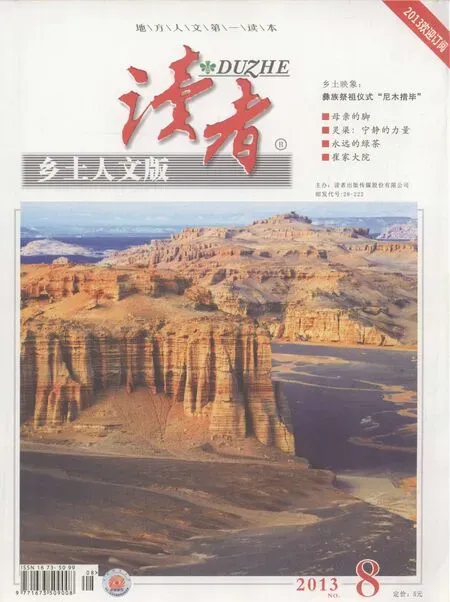我討厭我身上的汗味
2013-04-25 07:05:35周海亮邵曉昱
讀者(鄉土人文版)
2013年8期
文/周海亮 圖/邵曉昱
我討厭我身上的汗味
文/周海亮 圖/邵曉昱

我知道我身上有一股很重的汗味。我還知道,那氣味很難聞。
現在是黃昏,我擠上一輛12路公共汽車,從東城去西城。我喜歡12路公共汽車,它是小城所有公共汽車中線路最長的一趟車。每天我都要往返東城和西城,清晨與黃昏,12路公共汽車伴我穿越小城。有時我甚至嫌這段行程太短。我喜歡站在車上,打量這座城市的街景。
我討厭一些作家把我們描述得很可憐,偏偏現在的作家大多喜歡這樣寫。在晚上,在睡覺之前,我喜歡翻翻雜志。我翻雜志絕非有什么作家夢,純粹是因為無聊。我常常被雜志里的那些農民工的故事所感動,我對他們心懷憐憫。但我與他們不一樣,我不想讓別人憐憫,并且我真的沒有讓他們憐憫的理由。事實上,除了偶爾的傷感、恐懼、孤寂與無所適從,我過得挺快樂。
我對生活的要求很低。只要有一瓶白酒、兩包咸菜、一根火腿腸,我的夜晚就是快樂的。我一邊喝酒一邊打量街景:我喜歡坐著輪椅的老人、挺著啤酒肚的男人、挎著坤包的女人、踩著滑板的孩子;我喜歡路燈投下的光影、汽車濺起的污水、男人打出的酒嗝、樹葉“沙沙”作響的聲音;我喜歡馬纓花的香味、流浪狗的氣味、汽車尾氣的味道、女人隨風飄過的香水味。城市里,一切都是美好的。我喜歡這個小城。
可是我身上有一股很重的汗味,這讓我非常難堪。
清晨,我用冷水將身體沖洗了一遍又一遍。從西城去東城的公共汽車上,我非常自信。……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