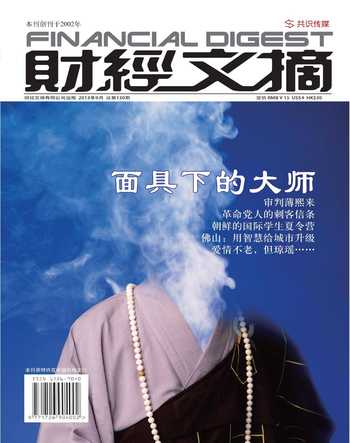俄羅斯:激進改革的失敗樣板?
張杰



1991年8月19日,蘇共保守派發動政變,企圖剝奪時任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權力。政變沒能挽救每況愈下的蘇聯,它的失敗反而加速了蘇聯的滅亡。政變五天后,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并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這個曾經稱雄世界的超級大國很快土崩瓦解。
腐朽政權轟然傾覆,莫斯科一片歡騰。然而,結束蘇共一黨專制,帶領俄羅斯進行“民主化”的葉利欽卻未能實現建設一個強大俄國的夢想。俄羅斯政局持續多年動蕩,經濟一度陷入崩潰的邊緣,至今未能恢復蘇聯的“往日雄風”。一些人將原因歸結為以“休克療法”為代名詞的激進改革,并主觀地認為蘇聯解體使俄羅斯陷入了萬劫不復之地。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筆者以為,俄羅斯在1990年代的“慘狀”不應歸咎于當時的激進改革,而且時至今日,俄羅斯的轉型也不可謂之失敗。
蘇聯已經難以挽救
蘇聯的懷念者普遍將戈爾巴喬夫定義為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罪魁,但事實上,待到戈氏上臺時,積弊已久的蘇聯已經難以挽救了。
蘇聯長期推行的是一種數量型趕超戰略,與這種戰略相適應的是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蘇聯問題專家、中央黨校教授左鳳榮總結,蘇聯模式的經濟特點是:以國家政治利益為目的的經濟發展政策,全部經濟生活無所不包的單純的計劃經濟體制,由政府集中管理經濟和進行資源配置的行政命令型體制,以實現軍備趕超為核心的經濟非均衡和粗放式發展的道路,由國家壟斷、與世界市場相隔絕的對外貿易。
這種依靠政治動員、缺乏動力機制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難以為繼的,事實也生動地詮釋了這一點:在整個蘇聯時期,其經濟由高速到低速再到負增長,并非偶然的波動,而是趨向性遞減,平均每隔5年大體縮減1.5個百分點。
1980年代初期,蘇聯的經濟增長乏力已經顯而易見,1980年到1985年其GNP增長率只能維持在2%左右。到19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負增長也成了自然而然之事,并不違背其經濟運行的正常軌跡。而這正是蘇聯深刻內在矛盾的集中體現。
戈爾巴喬夫自1985年上臺后,為了提振經濟實施了一系列漸進改革,但是并沒有放棄對計劃經濟的眷戀,只是希望在計劃的框架內發揮市場的力量,亦即實行所謂“計劃的市場經濟”。
戈氏的漸進改革收效甚微,蘇聯的經濟更加惡化了。面對經濟衰退的殘酷現實,精英階層開始鼓吹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化。但直到1990年,蘇聯領導層才開始考慮向市場經濟過渡,但為時已晚。
1990年至1991年,蘇聯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GNP在1990年下降了2.4%,1991年則下降了13%左右,固定資產投資在1990年急劇下降了21%,政府預算赤字持續上升,通貨膨脹亦失去了控制。戈爾巴喬的改革已經無力回天了。
激進改革獲得人民的普遍支持
1989年,蘇聯社會科學院曾經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代表工人的占4%,認為蘇共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占11%,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85%。
蘇共已經失去民心,蘇聯人民對漸進改革的耐心也被消磨殆盡,要求激進改革的聲音日益高漲,而這種狀況隨著每況愈下的經濟形勢愈演愈烈。
1991年“八一九事件”之后,葉利欽終于掌權,他批評戈氏的漸進改革,指出蘇聯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補補,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越來越嚴重,結果斷送了蘇聯的前程。俄羅斯要避免重蹈覆轍,應該大刀闊斧,進行深刻變革。
轉軌已經勢在必行。在年輕的經濟學家蓋達爾的協助下,葉利欽積極提出一系列被稱作“休克療法”的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放開物價;大規模私有化;出臺財政、貨幣“雙緊縮”政策,大量削減政府支出,取消稅收優惠,同時控制政府貨幣發行量。
葉利欽深信,要將俄羅斯從危機引向“文明之路”,必須要有決定性的“改革突破”,而且要行動迅速。只有這樣,才能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走上西方的發展道路,建立西方式的經濟與政治制度。
葉利欽的一些支持者也許對“休克療法”如何才能有效運行抱有懷疑,但它卻受到了西方經濟學家和權威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高度評價。因而,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拋開了原有的一切疑慮,以876票對16票這種一邊倒的票數通過了葉利欽的經濟計劃,同時投票贊成他享有執行經濟改革的立法權。
后世有民族主義者抱怨,西方勢力將“休克療法”強加給俄羅斯,但實際上在當時人民對葉利欽的激進改革措施是普遍接受的,私有化也幾乎是眾望所歸。1992年初的俄國所要面對的是蘇聯留下的不折不扣的“爛攤子”,經濟連年滑坡,又突然面臨經互會“大家庭”經濟空間與蘇聯統一經濟空間雙重解體的沖擊,經濟失衡已到了無論什么“主義”者都無法容忍的地步。
經濟衰退不應歸咎于“休克療法”
在實施“休克療法”后,早期存在的一些諸如基本消費品短缺、食物配給和囤積居奇等尖銳的經濟問題很快得到緩解,但接下來的劇本并沒有照此展開。俄羅斯經歷了長達四年嚴重的經濟衰退,直到1995年底仍沒有結束。
四年間,俄羅斯經濟衰退達到了40%。休克療法也沒有控制好通貨膨脹,到1995年底,消費品價格與1991年底相比上漲了1411倍,與1990年底相比上漲了3668倍。此外,人民的實際收入也出現下降,到1995年初,俄羅斯工人的平均實際收入下降了一半以上,很多人節衣縮食來維持生活。
實事求是,俄羅斯實行“休克療法”效果并不好,但并不意味著“慘狀”應該歸咎于這一系列激進改革。
俄羅斯的經濟危機始于蘇聯時代后期,經濟轉軌并非禍根,新班子接手的是徹徹底底的“爛攤子”。比如,蘇聯的全部外債都由俄羅斯承擔。蓋達爾在其《帝國的消亡》一書中記載蘇聯經濟的大潰敗,蘇聯外債從1981年的150億盧布增加到1991年的322億盧布,僅1991年連本帶息就需要支付約100億盧布,中央財政離破產、中止支付外債僅有數周時間。
此外,俄羅斯經濟困難的原因是實施了“休克療法”,還是“休克療法”不徹底、半途而廢,目前依然有頗大的爭議。
在“休克療法”引起痛苦的情況下,議會力量很快成為葉利欽的反對派。1992年7月,俄議會推翻了政府的緊縮預算,大幅放松銀根。這時休克療法僅持續半年。在議會的壓力下放棄財政貨幣緊縮的結果是靠大印鈔票來彌補赤字、增加國企補貼,這種飲鴆止渴的政策反而使經濟更加困難。在葉利欽與議會的拉鋸戰中,任何療法都不能貫徹到底,其療效不佳也就不足為奇了。
需要指出的是,貫徹“休克療法”更為徹底的波蘭、捷克等東歐國家與波羅的海三國經濟轉軌都比俄羅斯成功,而沒搞“休克療法”的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經濟狀況卻不比俄羅斯好。然而,不管激進還是漸進,轉軌初期的經濟滑坡則是蘇聯東歐各國無一例外的現象,就連有西德大力扶助的前東德也不例外。這說明,“休克療法”與經濟衰退的相關性并不明顯。
恢復的信心
如今的俄羅斯經濟,還有種種問題,但經過了1990年代的衰退和低迷后,從1999年開始復蘇,俄羅斯通貨膨脹率逐年下降,經濟穩定增長,一掃最初十年的頹勢。這期間,俄羅斯GDP年均增長6.9%,遠遠超過世界平均4.7%的增長速度。
現在,俄羅斯不再有短缺之苦,醫療幾乎免費,中小學上學免費還免費提供午餐,60歲以上無論工人農民都享受養老保險衣食無憂,實行個人12%、企業25%單一無累進稅制,政府機構大量精簡,國家財政1/4用于教育、醫療、養老和社會救濟。2006年,俄羅斯提前還清了欠巴黎俱樂部的220億美元的債務。世界銀行近期公布的各國“經濟成績”,2012年度俄羅斯人均國民收入高達12700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俄羅斯人“終于松了一口氣”,重拾信心的他們對民主的認同感也越來越高。“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就是沒有良心;試圖恢復過去的蘇聯,就是沒有頭腦。”普京的這句話廣為流傳。
回顧俄羅斯的轉型歷程,雖然不能說實施了“休克療法”才有經濟復蘇,但至少說明,那種認為激進改革會讓社會陷入萬劫不復之地的看法是不正確的。
學者金雁指出,越是強力控制的大帝國,一旦解體就越難建立正常秩序。“帝國后遺癥”的結局多數都不外乎兩種:一是持續的混亂導致社會情緒極端化,呼喚出“亂世鐵腕”;二是失去政治高壓的掩蓋,社會裂痕暴露,發展為內戰。葉利欽雖是“病夫治國”,但他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在漫長的過渡期中俄國既沒有由混亂發生內戰,也沒有導致人們因厭亂而走向極端。
在政治上,葉利欽沒能建立完善的民主程序與有效的權力制衡,但畢竟已經有了公認的議會與總統選舉,有了強大而合法的反對派,有了基本的政治自由與公民政治權利。在經濟上,俄國并未建成有效的激勵機制與規范競爭的市場體系,但市場經濟的基干還是建立了起來,為其在新世紀的騰飛打下了制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