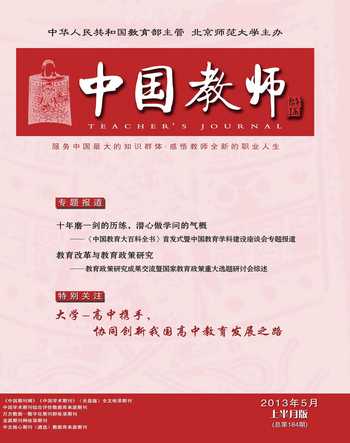做課如作文
謝金霞
做課,精心教學也;作文,文章寫作也。
一堂課怎么做,無定法可依。因為什么樣的課算是好課,無標準定則。葉瀾教授認為“扎實的、充實的、豐實的、平實的、真實的”“五實課”是好課;崔允漷教授則說“教得有效、學得愉快、考得滿意”的“三得課”是好課……竊以為,循規蹈矩的,肯定不是好課。
一篇文章如何寫,無套路可循。因為什么樣的文章算是好文章,無通用準則。《文心雕龍》說“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是為好文;清末最大文派“桐城派”說“清真雅正”是為好文……竊以為,中規中矩的,肯定不是好文。
做課與作文,正所謂“教無定法,文無定則”。
教無定法,使做課區別于車間流程。一個課題讓不同人做,往往神通各顯,差別懸殊;一堂課讓不同人來評,“一百個人會有一百種說法”。
文無定則,使作文區別于產品制造。一個文題讓不同人寫,常常內容有別,風格迥異;一篇文章讓不同人來品,“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
做課與作文,似風馬牛不相及,但二者細究之下,卻有相通之處:做課如作文,其皆有“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文、言之有情”之特質。
一、言之有物
一篇好文須言之“有物”。文章言之有物,乃指作者有感而發,而非無病呻吟。通俗言之,即你寫出的東西,表達的意思,要站得住腳,經得起推敲。大凡好文,或富含哲理,或寓情明志,或抒發實感,或褒貶時弊,雖不求有濟世普化之用,卻必有存在之意義。如此文章方可為“立言”之作,寫之,才有合理的價值。
一堂好課須教之“有物”。課之“有物”乃指課堂教學有“內容”。通俗言之,即“教什么”。有君憤然,“哪有教學無內容之課”?君言差矣!昔者國學大師陳寅恪授課有“三不講”之說(書上有的不講,別人講過的不講,自己講過的不講。)衡之大師,聯之現實,雖不苛求,卻存警醒。君不見當下課堂或所教內容本是錯的,卻以非為是,如此教之有害;或所教內容雖是對的,卻是無用之物,如此教之無益;或所教內容雖是對且有用的,卻是學生自學能會的,如此教之無獲。一堂課,真正該教的,應是對而有用且自學不會之內容,如此,方為此處所謂課堂“教之有物”。
另外,一堂課該有多少“物”,達成怎樣目標,不但教師自己要清楚明了,還要讓學生心中有數。教師須以學情為底線,“物”情為衡量,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不同的對象確定不同教學之內容,不同階段給予不同目標之定位。若教之任務不明確,學之內容很含混,學生則會聽之費勁,想之茫然,食之無味,棄之不甘。
二、言之有序
好文章,必有其內在邏輯。文章怎么切入,怎么展開,怎么承接,怎么收束。層次段落,過渡銜接,詳略繁簡,皆須通盤考慮。可以說,文章結構合理,可以盤活各個章節,使詞句文段,聯成整體。反之,文段章節就會各自孤立,一盤散沙。
好課堂,必是一有機整體。開頭如何導入,內容如何安排,環節如何過渡,中間如何串接,臨了如何收束,這些亦為章法。可以說,課堂節奏合理,環節相為呼應,教學就會融會貫通,暢通無阻。反之,教學無序,環節失調,就如亂石拼湊而怪嶙,就如呼吸不暢而憋悶。
文章之“序”在于起伏。“文似看山不喜平”,其意為好文章如觀賞山景,以峰回路轉、高低遠近為佳。“文須錯綜見意,曲折生姿”,說的就是文“序”。好文之“序”,行文布局跌宕起伏,曲徑通幽,如此引人入勝,讀之興趣盎然。
課堂之“序”在于靈動。好的課堂絕非平鋪直敘,而是內容疏密有間,氛圍動靜結合,節奏張弛有度。這一切皆緣于教師設問、懸念、鋪墊手法之運用,才使得課堂呈現輕重、急緩、張弛之變化。課堂變化多姿,高潮迭起,既是教師有意為之,也是課堂“序”之趨勢使然。我們說,如此靈動課堂,學生學習積極性焉能不高?
三、言之有文
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劉勰說:“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其實,文章即“文”章,即“雕縟”之章,也就是文采修飾之章。好文章,或言語活潑,或句式靈活,或意蘊豐富,或意境深遠。無論哪種,都是一種美的存在。
課堂亦須文采。課堂乃語言交流之場所,課堂之文采體現于課堂之言語。夸美紐斯講:“教師的嘴,就是一個源泉,從那里可以發出知識的溪流。”蘇霍姆林斯基說:“教師的語言修養,在極大程度上決定著學生在課堂上腦力勞動的效率。”確如所言,課堂語言是一門藝術的學術,好的課堂語言,猶如火種,能點燃學生心中興趣火焰;猶如石塊,能激起學生心海興趣之浪。
或許有人認為,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是為課堂之文采。其實不然!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說的就是關鍵時刻,擇機點撥。也有人認為,字斟句酌、言簡意賅,是為課堂文采。此言差矣!一些貌似“插科打諢”之語,放之適時,如味精入菜,可成為渲染情調之手段,精巧過渡之橋梁。
其實,課堂之文采,何必拘泥一格?課堂之上不啰唆,不贅余,不夸張,不做作;或輕或重,或快或慢,收發自如,讓學生思想之弦,始終隨你語言指揮棒而跳動。歡快時,如泉水叮咚,輕松流暢;激昂時,似疾風驟雨,呼嘯而過;悲壯時,凝重低沉,惋惜之情油然可見。這,才是真正課堂之文采,有這等文采,定能燃起學生求知欲望,引發學生情感共鳴。
四、言之有情
葉圣陶曾言:“如有所感興,則必須本于內心的郁積,發于情趣的自然。”確如先生所言,文章是作者認識感悟的文字表現,更是一種真情實感的流露。
大凡好文章,皆情入字里行間。文章寫得情真意切,讀之方覺情真感實。否則,雖是辭藻華麗,文采飛揚,卻如剪彩為花,刻紙為葉,盡管精致,卻無生命活力。
好課堂亦如此。課堂是人的課堂,是情感的課堂。課堂上傳承的不僅是知識,更是情感文化的濡染。一句名言,一首詩歌,一篇散文,哪個沒有人情世故于其中?
誠然,課堂教學,博大精深。每位教師就其人生閱歷、氣質稟賦而言,是鮮有“拷貝”版的,這正如世上絕無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如有的擅長書法,能畫出栩栩如生的簡筆畫;有的口才極佳,絕不亞于激情飛揚的演說家;有的感情豐富,能即興流露出喜怒哀樂等等。但無論哪般“絕技”,其背后都是對學生、對學科、對自己的情感投入。沒有激情迸發,所有技巧枉然;沒有情懷相系,一切皆為做作。
所以,課堂情感不是表層的張揚,不是膚淺的鋪陳;不是華而不實的渲染,不是冗余累贅的堆砌;不是聲嘶力竭的吶喊,也不是矯揉造作的表演。課堂情感是一種真實的、由衷的、發自內心的、感人至深的愛。
陶行知先生說過:“以激情感動激情,以理想鼓舞理想,以生命點燃生命。”教師不必是詩人,但他應具有詩人的氣質;教師不必是作家,但他應擁有作家之情懷。上課,即如作文,教師就得用自身的氣質情懷,領著學生創寫出屬于自己的人生華章。
(作者單位:浙江省溫州市繡山中學)
(責任編輯:馬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