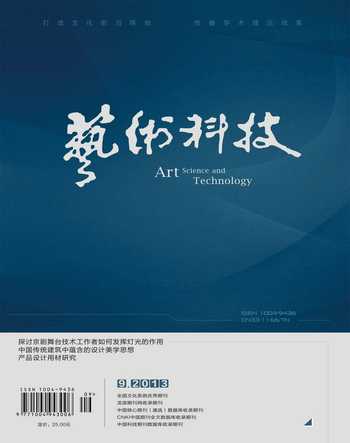禪宗與中國水墨畫興起的關系研究
摘要:以唐中期的“安史之亂”為界,唐文明由盛轉衰,中國封建文明由盛轉衰,中國色彩畫淡出畫壇主流而轉入民間發展。在佛教禪宗思想的影響下,出現于漢朝的中國水墨畫逐漸興起,占據中國畫壇主流位置,經唐中后期、宋、元、明、清延綿發展。
關鍵詞:禪宗;中國水墨畫;王維
“水墨”與“色彩”在中國古代繪畫舞臺上主次要角色的互換,使中國畫史在唐宋前后所上演的情節,發生了一次劇烈的變化:在此前,其劇情的展開是圍繞“色彩”這個主角而進行的,諸如“積色體”、“敷色體|”、“晉畫”、“丹青”、“吳裝”等都是這部劇情中的一個個情節;在此后,“水墨”扮演起了繪畫發展的主角,圍繞它所展開的劇情則由“文人”、“院體”、“流派”等情節構成。而色彩與水墨作為劇情主、配角位置互換的事件,是中國古典繪畫語言發展史上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幕。
中國水墨畫的基本體式在漢代時已經具備了,并與色彩畫并行發展,在唐代中后期興起,成熟于五代,并且在在宋元以后,成為了中國繪畫史上的主流繪畫形態。遲至在漢代以后,水墨畫就與色彩畫并行發展了。唐宋時的仕宦文人畫家們不過是撿起了漢畫中的水墨資源而已。中唐之前中國傳統繪畫是以色彩畫為主流的。唐中后期,水墨畫逐漸興起,并且持續發展到宋、元、明、清占據中國畫畫壇的主角地位。
佛教傳入中國始于漢代。禪宗,則始于南北朝。“禪”即梵語“禪那”,音譯而來,漢語意為“思維修”、“靜慮”、“定慧均”等,即“禪定”的通稱。
那么,何謂“禪”?禪即是人的“心”所達到的“無我”境界,因此,禪以“心”為宗。達到這種境界,可以使人“言語道斷,絕思靜慮”,使人斷一切妄念而入圣境。而慧能開創的禪宗是以“心即佛”為主要內容的心性學說,主張“頓悟”,以“定慧”為本。那么中國水墨畫的興起與禪宗學說有什么關系呢?
從東漢至六朝的500年間,是佛教大規模發展的時期。佛教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進入藝術審美的思想體系,直接影響了繪畫藝術的發展。這種影響充分表現在畫家將“禪”的意識,運用到中國畫的一點一線上。這一時期的繪畫名家如顧愷之、張僧鷂、陸探微、宗少文等人都相當虔誠的篤信佛法,喜歡結交高僧,經常為佛寺繪畫,其思想深受佛教的影響。
唐代太宗、高宗至武后數十年間,天下升平,國力強盛。佛教進入繁榮時期,舉國尚佛,雖婦孺也不甘落后。武則天因仰慕禪宗五祖的弟子神秀(北宗創始人)禪師之名,派遣使臣禮請入都傳法,并且帶著中宗、睿宗親至郊外跪迎,封神秀為國師,在皇城內建寺供養,朝野景仰。每到說法時,會聚數萬聽眾,人們都以能聽到禪師說法為榮。神秀圓寂后,都邑傾城為之送殯,唐代的尚佛之風可見一斑。這股洶涌澎湃的禪學洪流,也直接沖擊了畫壇。
不知是不是一種巧合,在唐玄宗天寶十四年,發生了使大唐文明由盛轉衰的大動亂——“安史之亂”,極大地影響了吳道子、王維、鄭遷等一些畫家的仕途境遇和人生心境。《舊唐書·王維傳》中記載潑墨山水的創始人王維:心境灰暗的他“每退朝之后,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而其“晚年長齋,不衣彩紋”。“室中只有茶鐺、藥臼、經案、繩床”。
王維號摩詰,山西太原人,世家禮佛,開元進士。進入宦界后,閑暇時常常去禪寺拜僧論道。先后聽神秀(606~706)、普寂(651~739)、義福(658~736)等諸禪師講法,按照佛法要旨,修持禪法,后來預知大限安坐而終。
王維對禪學的體悟,直接體現在他的藝術創作上,他的文章詩歌,澹遠空靈,深邃的禪機流露于字里行間,且能將詩意禪機入畫,又能以畫表禪。因此創作了不問四時“雪里芭蕉”式的寫意之作。王維在山水畫方面的成就最為顯著,其畫風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水墨渲染的畫法;二是空寂的意境。他一改過去畫山水的鉤研之法為潑墨渲染,使山水畫由此耳目一新。并著有《山水訣》畫論一篇,其中有句名言:“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深刻地體現出禪學思想。蘇東坡在《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贊王維說:“昧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其畫中的詩,詩中的畫,不是別的,而是禪的境界,禪的感悟。“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妙悟不在多言,絕妙的一句話,無形中道出了禪宗和中國水墨畫的最大特點。
可以說,王維等人筆下的水墨山水與他們的仕途失意肯定是有關系的。他們不論是禪誦佛事,還是倦于涉世,其“不衣彩紋”,素樸以居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樣的。而這種生活方式其實也蘊含著他們的審美理念:摒絕鏤金錯彩的華美與色相,而崇尚清幽、玄淡。因而,“玄(黑)色”成為與他們的審美最為契合的一種顏色。
之后的張彥遠、王墨繼承了王維的創作心法,并加以發揚光大,張彥遠所著《歷代名畫記》中有句名言“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被歷代奉為繪畫創作的心法。強調人對現實生活的平常體驗和對環境的心靈感悟,主張師心自用。南朝宗炳就提出了“應目會心”理論。“應目”是指觀察物象,“會心”則是畫家感應于物象后所產生的思想感情,亦即物我兩化,情景交融,最后達到“萬趣融其神思”。
那么,中國色彩畫淡出,水墨畫的興起,如果全歸于王維、張璪等人因仕途失意后對禪學的體悟,是不能完全使人信服的。因為仕途失意并不是他們獨有的經歷,而禪宗在南北朝就已產生了。那么為什么水墨畫為何興起于他們所在的唐代?是這些文人、畫家、仕宦們的自覺選擇嗎?
我想不是的。以中唐的“安史之亂”為界,唐文明由盛轉衰,中國封建文明由盛轉衰,整個中國的“精神氣候”已經發生了變化:在之前,中國文化是一種昂揚、激越、健朗之氣候;色彩的熱烈、堂皇、富麗、高華等無疑體現著這種精神氣候。在之后,中國精神氣候日益走向孱弱、低沉、內省、柔糜。審美理念與藝術形式也不能不順從、適應于這種大的精神氣候。而水墨的清幽、玄虛、簡淡,素樸等則肯定與這種精神氣候最為契合。
“禪”的境界是達到破執。“禪”崇尚的美,其中有“色空”之美,中道之美,破執破俗之美,自然之美、含蓄之美、返璞歸真之美。這種禪意的審美理想與水墨畫所呈現的美十分接近。而且水墨畫在形式、方法、工具等很多問題上都與禪意相契相合。
至此,禪宗思想為中國畫的發展注入了生機和活力,中國畫也為禪宗的發揚提供了難得的“道場”。中國畫開始追求以墨代色,以簡化繁,大樸自然而氣韻靈動的禪的意境。在對立的事物中處理上,中國畫也如參禪一樣,從來不是偏執一邊,而是去尋求一種超越。在對待形式上,中國畫主張“得意忘形”。忘形,不同于變形。它既非有形,又非無形;它既是有形,又是無形。它包含了兩者。忘形不是去排斥形,而是去關注本性。只有在見到了本性時,形才可能被忘掉。有形、無形都是對形的執著。忘形才能不為形所累,才是對形的超越。
總之,禪與中國畫水墨畫所表達的都是一種意境。我想從某種意義上說,禪不是導致中國水墨畫興起的直接原因,而是導致其興起的“催化劑”!
參考文獻:
[1] 牛克誠.色彩的中國繪畫[M].湖南美術出版社,2002.
[2] 王文娟.中國畫色彩的美學探源[M].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3] 范瑞華.中國畫向何處去[M].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
[4] 張桐楀.影響中國繪畫進程的100位畫家[M].南海出版社,2004.
作者簡介:傅麗云(1979—),女,山西太原人,蘇州大學藝術學院10級MFA在職研究生,山西藝術職業學院教師,助教,研究方向:中國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