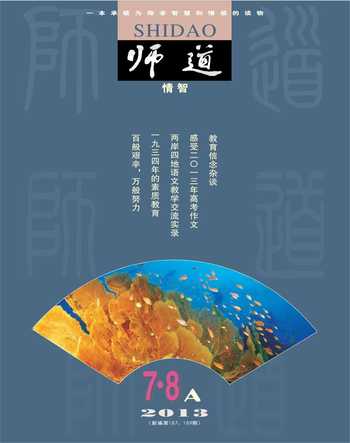同步閱讀,讓學生打下文化底蘊
游前程 徐仕林
《新課程標準》提出:語文教學應立足于促進學生的發展,為他們的終身學習、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礎。
閱讀教學在語文教學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目前實際的教學中,閱讀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課堂上師生沉浸于肢解課文,缺少整體性閱讀,缺少對課文的整體把握;學生課余時間主要用于作業,把閱讀等同于做閱讀作業題,去迎合標準答案,很少有時間從事課外閱讀,尤其是整本書籍的閱讀。現在學生的課外閱讀量少得驚人,以致一些文學研究生都沒完整地讀過四大名著,令老輩的文學教授大跌眼鏡。
缺少課外閱讀的惡果很嚴重。在某初中試卷中問:《駱駝祥子》一書中祥子的妻子是——,有學生填“女人”,有學生填“窮人”,有學生填“太太”,更有學生填“駱駝”,讓人哭笑不得。能填對“虎妞”的,真是鳳毛麟角。
涉及到古詩文的閱讀題,由于記誦不牢,不少學生學得似是而非,把名句移花接木把作者張冠李戴的并不鮮見,結果弄成的笑話也不少。如此文學常識的差錯,實在不應該。
所有這一切,都提醒我們,現行的閱讀教學,必須反思與改革。
其實,古代的語文學習以記誦為主,推行的是“書讀百遍,其義自見”。“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通過大量的識記背誦,形成語感,從而形成閱讀能力、欣賞能力與寫作能力。根本不會像我們現在這樣將一篇文章、一首詩詞講解得肢離破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學古文,把功夫放在幾個虛詞實詞上,放在對作者寫作意圖的推測上,而忽視了對全文意境的領悟,藝術的欣賞,精華的吟嘆,真可謂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由于閱讀教學的缺失,學生學了十幾年語文,口不能言,筆不能寫,對傳統文化知之甚少,對語文學習缺乏興趣,可以說,語文教學在某種程度上是失敗的。
現行的閱讀教學必須回到原點,返璞歸真。個人認為,首先要保證學生的課內同步閱讀。比如說課文中講到的內容,課外必須作外延的伸展,讓學生了解到緊密相關的方面。比如說,學《桂林山水》,可以給學生找一些名家寫桂林山水的佳作或片段, 供學生欣賞、學習。
比如學朱自清的《春》,可以讓學生讀背一些有關春天的詩句,如王安石的“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杜甫的“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賀知章的“二月春風似剪刀”,孟浩然的“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張致和的“斜風細雨不須歸”, 杜牧的“清明時節雨紛紛”均與文中的意境很相似;如果說朱自清的春比較溫柔比較細膩比較女性化,缺少陽剛,那么朱熹的“萬紫千紅總是春”, 杜甫的“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白居易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都很豪放,能激發起學生昂揚奮發的斗志。
相信這樣的課內同步閱讀,占時不多,聯系緊密,必能得到學生的喜愛。
其次,立足學生的生活實際,指導好學生課外閱讀。畢竟,我們讓學生讀書,不見得要把他們培養成文學家,而是讓他們具備人生應有的基本知識與素養,打下文化底蘊。底蘊深厚,則后發優勢足,發展潛力大。底蘊薄,則行不遠,力不從心矣。
可以說,現在的課外閱讀,尤其是經典名著,不少是大部頭的,學生平時課業多,難以有大段的時間來看。所以,平時,學生以精短的千字左右的時文閱讀為主,如選看《少年文摘》《意林》《讀者》《青年文摘》。而時間較充裕的暑假和寒假,可以讀書為主,千萬不要讓各種羅羅索索的假期作業占滿了他們的時間。小學生宜讀有趣有益的詩詞與童話類,如《千家詩》《宋詞選注》《朝花夕拾》《致小讀者》《鄭淵潔童話》《吹牛大王歷險記》《格林童話》《木偶奇遇記》《西游記》《格列佛游記》《騎鵝旅行記》《伊索寓言》等等;中學生宜讀一些開闊視野的書籍,如探險類的《80天環游地球》《海底二萬里》《 魯賓遜漂流記》等,白話小說類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官場現形記》等,如優美散文《張曉鳳散文選》《冰心散文選》等,推理小說的《福爾摩斯探案集》;修身養性的歷史哲學類書,如《培根論人生》《世界上最美的哲學課》《上下五千年》等,可分為必讀與選讀。必讀保證學生最基本的閱讀量,選讀可照顧學生的個性愛好。個人認為一些與學生閱讀興趣、生存年代較隔膜的名著,應允許學生選讀,不宜強求。而有些學生喜好看漫畫,只要沒有不宜的內容,也用不著反對。
古人說,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可見精神享受比物質享受更重要。也有人說,一日不讀書則面目可憎。讀書之人,三日不見,須刮目相看。“腹有詩書氣自華”。也有人說,閱讀是讀書之始,也是自我教育之始。語文教學,要重視同步閱讀,給孩子打開一方知識的寶庫,讓孩子從此愛上學習,愛上讀書,打下深厚的文化底蘊,終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