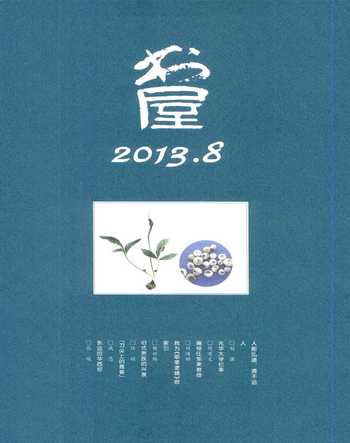國學大師黃侃的傳奇人生
柳作林
讀葉賢恩先生著《黃侃傳》、潘重規先生著《黃季剛師與蘇曼殊的文字因緣》、司馬朝軍等著《黃侃年譜》等書,深為國學大師黃侃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治學精神及個人獨特氣質所感動,情不自禁,乃作此篇,以窺豹先生傳奇人生。
一
黃侃,湖北蘄春人,1886年4月3日(農歷二月廿九日)生于四川省成都金玉街三道會館。他自幼穎異,聰明過人,三歲發蒙私塾。五歲,隨父黃云鵠(翔云)去武侯祠,祠堂壁懸楹聯甚多,黃侃咸默記之〔1〕。七歲時,父親黃云鵠受聘江寧尊經書院(現今南京市),黃侃隨母留家,經常奉母指令給父親寫信,告知其家境。令人意外的是,有一次黃侃在寫完信后,即興附詩一首:“父作鹽梅令,家存淡泊風。調和天下計,杼軸任其空。”(其父黃云鵠曾任四川鹽茶道,又曾任蜀地它職,前后歷二十年,清風峻節,守法愛民,蜀人稱為“黃青天”)〔2〕。父親見信后,既驚嘆不已,又倍感慚愧,并和詩一首:“昔曾司煮海,今歸食無鹽;慚愧七齡子,哦詩奉父廉。”〔3〕當時黃云鵠的朋友山西布政使王鼎丞(湖北宜昌人)正客居江寧,無意中見到這首七歲孩子的詩作,大為驚嘆,當即將自己的愛女許配給了他。黃侃十歲時,已經能暢通經史。一日,黃侃在蘄州一家名慶大祥號書店看《資治通鑒》,一邊閱讀,小腦袋一邊搖擺,似有所得的樣子,引起了老板張仁福的關注,張老板走到黃侃身邊輕聲問道:“你是不是預購這套書呢。”
“想購,我現在沒有錢,打算來這里兩三次,刻在腦子里牢靠些。”黃侃回答說。
“你這小伢兒,好大的口氣!你今天在這里看了多少本?只要你能把今天讀到的部分跟我背誦出來,我把這套書贈送給你。”
“今天我只看六本。”
“好,我不要你背誦六本,只要你在這六本之內,我點到哪幾段,你背誦得來,我就把書贈送給你。”
“當真?”
“君子無戲言!”
結果張老板點哪一段,黃侃就背哪一段,而且滾瓜爛熟。張老板深深被折服、連聲贊道:“神童!神童!我贈書給你!我贈書給你!”并在書的扉頁上寫下了“贈給一位神童”六個大字,從此“神童”在蘄春傳遍開來。
二
1903年,十八歲的黃侃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武昌崇文普通中學堂,為第一屆學生,與宋教仁、董用威(董必武)、查光佛、鄭江灝、歐陽瑞華、陳錕、田梓琴等革命志士同學〔4〕。學習期間,他深受受宋教仁、董必武等人民主革命思潮的陶染,開始接受反對滿清專制統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并以推翻清政府、拯救民族、拯救人民為己任。
在崇文學堂期間讀書期間,經同學宋教仁的介紹,黃侃與兩湖書院肆業的湖南善化(今長沙)人黃興〔5〕訂交,結為莫逆,他倆經常在一起宣傳反清、反對君主專制的革命思想,議論時政,指斥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黃侃多次當面調侃、諷刺學監李貢三是一個不學無術的官僚,于是觸怒了這位學堂權要。不久,學校張貼公告,宣布開除了黃侃的學籍。1904年,黃侃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去拜見湖廣總督張之洞,張總督認為黃侃聰明超群,是當世不可多得的人才,便用官費資助其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深造〔6〕。
1906年1月31日,黃侃在日留學期間巧遇宋教仁〔7〕(宋也因進行革命活動,被開除學籍,亡命于日本),在宋教仁的引薦下,黃侃會見了辛亥志士田梓琴、曹亞伯等,相一起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張之洞聞訊黃侃在日參加從事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于是取消了對黃侃留學的資助。從此,黃侃開始了革命者的流亡生涯。
在日期間,黃侃師從余杭章太炎(炳麟)〔8〕學習音韻和說文,同時與章、劉(劉師培)籌商革命,為同盟會的《民報》撰稿。1907年,章太炎在日本東京受孫中山先生之命,擔任《民報》主編。一日,見到黃侃的一篇文章,大加贊賞,立即寫信約見,許為奇才,約其為《民報》投稿。據統計,從1905年11月《民報》創刊到1910年2月1日終刊,黃侃以“運甓”、“不佞”、“信州”等筆名發表了《專一之驅滿主義》、《哀貧民》、《釋俠》、《論立憲黨人與中國公民道德前途之關系》、《哀太平天國》、《劉烈士道一像贊》和《討滿洲檄》〔9〕等一系列文章,其中《討滿洲檄》一文是以軍政府名義,發布在《民報》臨時增刊《天討》上,是辛亥革命時期的一篇重要文獻。文章氣勢磅礴,情感強烈,論說透辟,筆鋒犀利,深刻揭露了清王朝十四大罪狀,支持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從政治和為人道德結合的角度,強烈批判封建地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各種壓迫和剝削,充分表明了革命的浩然正氣。
1910年,由于同盟會的隊伍不斷壯大,國內各地革命力量蓬勃興起,武漢地區最為熾烈。于是,湖北革命黨人邀請黃侃回國共謀舉義大事。當時湖北最為活躍的有“共進社”和“文學社”兩大革命團體。1911年秋,黃侃返鄂參與了這兩個團體并策劃發動革命,他還先后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的會黨中吸收會員,發展組織。又受《大江報》社長詹大悲之約,以“奇談”署名,為《大江報》撰寫時評《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10〕。文中說:
中國情勢,事事皆現死機,處處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為。然猶上下醉夢,不知死期之將至。長日如年,昏沉虛度,軟痛一朵,人人病夫。此時非有極大之震動,極烈之革命,喚醒四萬萬人之沉夢,亡國奴之官銜,行見人人歡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為事理所必無,次之則為無規則之大亂,予人民以深痛巨創,使至于絕地,而頓易其亡國之觀念,是亦無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亂者,實今日救中國之妙藥也。嗚呼!愛國之士乎?救國之健兒乎!和平已無可望矣!國危如是,男兒死耳,好自為之,毋令黃祖呼佞而已。〔11〕
這篇反清戰斗檄文發表后,尤如一枚炸彈爆炸,立刻震動了大江南北,革命人士受到了極大地鼓舞,增加了他們的強烈斗志;而清朝政府上下則驚恐萬狀,感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立即查封了《大江報》,并逮捕了社長詹大悲、總編輯何海鳴。
《大江報》被封,輿論界大嘩。時湖廣總督瑞澂,第八鎮統制張彪等人見破獲人士如此之多,大為震動,生怕士兵“大亂”,當即下令對新軍嚴密監視,禁止官兵隨便出入,欲調巡防營(舊軍)來省城加強防衛,形勢極為緊張。10月10日晚,第八鎮工程營士兵首先發難,轟轟烈烈的武昌首義爆發了。
由此可見,黃侃的《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這篇時評,可謂是武昌起義的導火索,為辛亥革命爆發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其功不可沒。
三
“報親恩,惜身命,為兒女,作所依”〔12〕,這是黃侃治家孝道的一貫思想,堅持以孝道教育家人,教育后代。自1907年師從章太炎先生以來,一直以執弟子禮數始終甚謹〔13〕,逢年過節,或久別重逢,依例都要躬行叩拜之禮,尤其是對先生的革命精神和治學精神極為敬仰。1914年2月,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被袁世凱幽禁在北京東城錢糧胡同。黃侃來到京,探知先生的下落后,冒著殺頭的危險,“日夕相依同宿,復致書教育總長論救,致書教育總長湯化龍,詞甚哀切,又作《申理章太炎建議案》一文,辭甚哀切,其義篤師交,罔顧生死,有古烈士之風”〔14〕。直到袁世凱死后,章太炎才被釋放出來。黃侃之所為,使身陷困境中的章太炎深為感動,遂將其得意之作《新方言》相贈,并題詞其上以為回報。在學術上,黃侃重視師承,他視章太炎為樸學泰斗,仰之彌高,常以“刻苦為人,殷勤傳學”以自警。他身體虛弱,仍致力學術而不倦,“惟以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但又不為師說所囿,而要在繼承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新的探索。所治文字、聲韻、訓詁之學,遠紹漢唐,近承乾嘉,多有創見;在音韻學方面,對古音作出了切合當時言語實際的分類。晚年黃侃主要從事訓詁學之研究。其重要著述有《音略》、《說文略說》、《爾雅略說》、《集韻聲類表》、《文心雕龍札記》、《日知錄校記》、《黃侃論學雜著》等數十種〔15〕。
黃侃學問大,素性狂傲,但治家敬孝是他的一貫思想,堅持用孝道來教育家人和后代。1898年,他父親云鵠因患惡性瘧疾過世后,每逢父親的生日和忌日,他無論在何地都要率家人設筵祭奠,以示哀悼。1908年,黃侃留日期間,得知生母周太孺人病重,立即離日回家,為母親四處奔波,求醫問診,侍奉備至。11月,生母病情進一步惡化而不幸逝世。黃侃親自處理生母后事。返日后又請好友蘇曼殊(元瑛,時亦在東京,同住《民報》社內))“繪《夢謁母墳圖》”〔16〕。黃侃面對該圖,思及自己眼前境遇,有國難投,有家難歸,悲感相集,遂揮筆寫成《夢謁母墳圖》題記一文,文末用《詩經》中“豈不懷歸,畏此罪罟”來表達他對家國之痛,充滿了愛國主義的激情,隨后又請章太炎先生為畫幅題跋。章太炎揮毫寫了《書黃侃夢謁母墳圖記后》,表現了他倆之間超出一般師弟、師友的深厚情誼〔17〕。
1921年10月,黃侃應聘到武昌中華大學(即現今的華中師范大學前身)、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即現今的武漢大學前身)任教,這期間為了讓養母田太夫人晚年不寂寞,能有個周到的照料,便把田夫人寄養到黃安其次女家。黃侃還非常內疚地在日記中寫到:“謹榆之奉,不克隨時,盡侃之年,不足以銷此恨矣。”〔18〕黃侃對于自己遠離養親,未能盡到侍奉之責,以致有累深感不安,懇切自責,充分體現了他孝敬養母之情。
四
由于黃侃清高孤傲,他與章太炎、劉師培被學界稱為“三瘋子”。五四運動時期,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驍將,積極提倡白話文運動,黃侃和章太炎看不慣胡適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并竭力反對。胡適知道黃侃的這種“瘋”性格,每次只好忍氣吞聲,謙讓過之。他這種我行我素、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一直到1919年秋,從北京大學調離到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任教時,遇上了首任校長石蘅青(石瑛),才算是遇到了真正的克星。
石瑛,字蘅青,湖北陽新縣燕廈(今通山縣新莊坪)人,英國冶金留學博士,為人秉性剛直,廉潔奉公,兩袖清風,被譽為“民國第一清官”;他工作作風嚴謹、正派,從不徇私情。尤其在工作上,石瑛不管是誰,不管官階有多高,都不準在自己任上徇私情,所以又被稱之為“湖北三怪”。石瑛在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任校長期間,他不僅嚴格督促學生的功課,對老師也同樣是雷厲風行,講求的是踏實、認真和廉潔,且不定期的進行考察,極力反對老師疏懶、浮夸、狂妄,全校師生都非常害怕這位“怪”校長,就連“瘋”狂傲慢的黃侃,對石瑛校長也是敬畏三分。黃侃時不時的自我解嘲道:“碰著石蘅青,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19〕有一次黃侃因未給學生上課,被石校長逮了個正著,石瑛嚴肅地規勸黃侃說:“季剛,你讀了一肚子好書,為什么不好好用以濟世呢?還發什么狂呢?”〔20〕黃侃只有稱道:“是。”曾有人問黃侃:“為何轉了性?”黃侃毫不隱諱地說:“打不過人家,有什么辦法呢?”可見黃侃雖表面狂傲,但對他敬重的人,還是很謙虛的。
五
黃侃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國學大師。他出口成章,過目不忘,詩詞歌賦無不精通,生平寫作的詩、詞、文章很多。1985年武漢大學黃侃詩文遺稿整理小組編輯的《黃侃詩文集》,其中收錄詩有一千五百五十二首,詞四百一十八首,文和賦一百五十八篇。細讀黃侃的詩文集,不難發現,與同時代舊體詩文的其他作家詩文相比,黃侃的都屬于上乘,在近代文學史上應占一席之地。
在文字學方面,黃侃在恩師章太炎的語言文字學學科觀念的基礎上,進一步闡釋了“夫所謂學者,有系統條理,而可以因簡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雖字不能遍識,義不能遍曉,亦得謂之學。不得其理與法,雖字書羅胸,亦不得名學”〔21〕。對此,黃侃將語言研究中的形、音、義通觀闡述得更為明確,為我國傳統語言學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在訓詁學方面,他把訓詁學視作研究國學的基石:“學問文章宜由章句訓詁起。”并提出的一系列富有創見性的主張以及他卓越的訓詁實踐,其著述經后人整理的十七種《黃侃論學雜著》、《文字聲韻訓詁筆記》、《說文箋識四種》、《爾雅音訓》、《量守廬群書箋識》等〔22〕。這些書中既對文獻材料的精辟考辨,又有系統、條例的歸納,為《爾雅》學的建立構筑了有血有肉的框架,標志傳統雅學向現代雅學的不斷飛躍,從而開創了訓詁學研究的新紀元;在音韻學方面,黃侃將其作為訓詁學的初階與工具來進行探討,對古韻對轉、旁轉、旁對轉做了一次重大突破,在漢語音韻史上無異于豎起了一座劃時代的里程碑;在經學、哲學、文學、史學等方面,黃侃均有很深的造詣,成為一代國學大師。
作為國學大師,黃侃的嚴謹治學、刻苦求研精神也是值得后人稱道的。他曾說過:“學問須從困苦中來,徒恃智慧無益也。”“學問成熟,自然要著書。我打算五十以后就從事著作。”〔23〕1935年農歷二月十九日,黃侃先生四十九歲生日,恩師章太炎贈上一壽聯云:“韋編三絕今知命,黃絹初裁好著書。”〔24〕其本意是催他寫作,寄望于已年近半百的得意弟子黃侃寫出“絕妙好辭”。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章太炎苦心而作的對聯無意間嵌著“黃”、“絕”、“命”三字。黃侃展開壽聯,一眼就看出暗藏的玄機,因此很不高興,以為“命該絕矣”。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內心都是忐忑不安。
1935年10月6日,黃侃因飲酒過多,胃血管破裂,吐血不止,經醫生搶救無效,于10月8日(農歷九月十一日)英年早逝,年僅四十九歲。他是海內外公認的國學大師,其著作及精神風范是中華民族的一筆寶貴財富和學習的典范。
注釋:
〔1〕〔2〕〔3〕〔5〕〔7〕〔9〕〔13〕〔15〕〔16〕〔17〕〔19〕〔20〕〔22〕葉賢恩:《黃侃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3、33、41、58、66、246、240、210、232、231、235、252頁。
〔4〕潘重規:《黃季剛師與蘇曼殊的文字因緣》所言,張暉:《量守廬學記續編》,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70頁。
〔6〕蘄春縣檔案館藏:XZ—12—234。
〔8〕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黃侃劉師培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頁。
〔10〕〔14〕〔23〕〔24〕司馬朝軍、王文暉:《黃侃年譜》,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1、60、61頁。
〔11〕黃侃: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校訂《黃季剛詩文鈔》,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頁''
〔12〕〔18〕蘄春縣檔案館藏:XZ—12—231,《黃侃日記手稿》,1921年12月。
〔21〕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