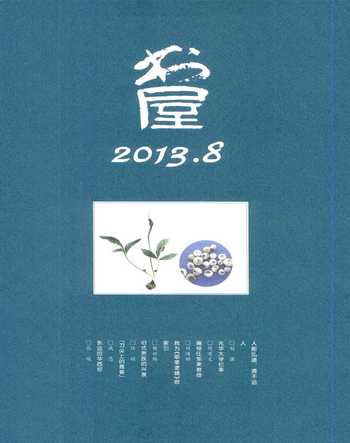而今誰識書生
陸達生前的同事黃君看到拙文《天鵝之死》后,輾轉聯系上我,共話往事,嘆息不已。夜深人靜,我倚在床上心情久久不能平復下來。不僅是陸達,幾十年間多少不堪回首的往事在心里翻騰,情不自禁,寫下一首絕句:“雖是初逢似舊雨,遙憐故友話凄涼。此生只剩一支筆,劍氣簫聲總斷腸。”
文明使這個世界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得井井有條,但人生不能選擇,這種不能選擇常常使我憤懣。所以,我筆下流淌的,雖是悲哀凄涼,卻不是絕望。“世事滄桑不自傷,拼將血淚寫文章。憑欄誰識書生面,一笑拈花四野茫。”這就是那天夜里我寫下前一首詩后,欲罷不能,又寫下的一首“縱筆”詩。
黃君是通過張君和我見面的。張君長于書畫和金石,給我和我學書法的孫女所治之印甚佳,我送他一首絕句:“慘淡情懷方寸間,丹青更是起云煙。才華卻為衣食累,空鎖關河六十年。”他送我一幅太湖石圖,我又戲題三絕句,其一曰:“此石嶙峋出自然,千年凝氣萬年還。我心匪石血如火,我腰如石豈一彎。”題畫詩直抒胸臆,格律稍粗。
實際上,四十余年來,我只寫了寥寥三十余首舊體詩,因為“文革”初受人牽累,我寫的一百余首舊體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過了一段艱難日子,那以后許多年再也沒有寫過舊體詩。
但我始終認為,有些感情上的東西只能用舊體詩這種體裁才可以表現出來,也就是說,只有舊體詩才能承載感情的奔瀉。“只有雷門堪擊鼓,人笑人嘲都是譜”。記得“文革”中期黨團組織恢復生活,剛脫囹圄的友人羅君又要交代自己的“思想錯誤”,甚是煩心與反感,跟我談起,一下子觸動了我,情不自禁地說出兩句詩:“舊劫不隨人事老,時時翻出作新愁。”而今羅君早已作古,年復一年,我時時想起這兩句詩來,不為別的,僅僅是那時的感情還在心里激蕩。
這種激蕩的感情常常在心里燃燒起來。老報人陸老米壽之慶,秀才人情,我奉上兩首詩,其一曰:“南山松柏郁青青,鐵干虬枝拂白云。國事艱難人事老,中宵猶自聽雞鳴。”不僅是祝壽,也把燃燒的感情傾注在詩中。
忘年至交翁月卿先生是清末封疆翁同爵的嫡親孫女,她的叔祖父翁同龢更是清季重臣。月卿先生家學淵源,成就書法名家,以近九十之高齡自撰自書《葆真集》出版,之前亦有數種書法集和散文集《西街憶舊》面世,我曾寫詩相賀:“風雨西街憶舊游,小樓磨硯幾春秋。葆真結集星垂野,璀璨銀河筆底收。”“九十書家孰與儔?更兼筆下寫春秋。每瞻雙璧親和力,風暖長江月滿樓。”
寫詩確實是心靈的撞擊,那一瞬間撞擊出來的火花就是詩。有時面對驚天動地萬眾歡騰的場面就是寫不出一句詩,就因為沒有那個撞擊。有時卻因一點小事一首小詩旳觸動,性靈相通,激發出寫詩的欲望。老友徐山皕先生出身名門,是明朝開國元勛徐達后裔,滿腹經綸,錦心繡口,勤于書信往返,誦讀如賞水墨丹青,我曾委婉寫詩相贈:“每讀華章感慨深,牽人情趣一煙輕。低回可惜先生筆,不寫民間疾苦聲。”
故友張老寫下一首品新茶的鷓鴣天詞:“谷雨春尖碧嫩香,一瓢江水煮瓊漿。分茶漫憶放翁句,品茗猶懷陸羽鄉。凝郁馥,溢芬芳。壺觴代酒細評量。而今但得晨昏飲,可以清心滌俗腸。”這首詞的后兩句一下子觸動了我,感而和之:“漫道新茶似酒香,洗心明目勝瓊漿。燈紅人擁邯鄲路,月白舟搖陸羽鄉。晤故友,對幽芳。行藏用舍自思量。雨前沏得桃溪水,解我無端千結腸。”
聞一多先生的侄女聞立詢女士看到我這首詞,嘆道:無端是有端。真是這樣。那段時間我在機關郁悶極了,到了無法工作下去的地步,最后找到市里老領導幫我溝通,在無任何優惠條件的前提下,提前六年退休。這首詞既是寫的品新茶,更是寫的我郁結的心情。這里的“故友”指茶,黃庭堅《品令》詞把茶寫為“故人萬里,歸來對影”。“雨前”也是指茶,谷雨前的新茶。雨前茶用桃花源的溪水沏出,就是我那時心情的寫照。
世交殷永秀女士與夫君童耐冰先生結廬大別山麓,林泉自娛,我每年都要去小住數日,竹籬花徑,清泉烹茶,心靈都得到洗滌。某年初秋我造訪時寫了一首絕句:“近樹參差遠樹迷,小樓半隱萬山低。塘邊扁豆新如筍,滿天煙雨子規啼。”那個子規真叫多,成百上千的在清晨的山嵐煙雨中啼叫飛翔,畫面美極了,也擾人清夢。
深冬時節永秀女士來信邀我去看梅花,我依前韻作答:“近事朦朧遠事迷,清霜千里入云低。殷勤告訴梅初放,夜闌魂夢杜鵑啼。”兩年后的冬天我去了,朔風冷雨,世界是一片肅殺的衰敗景象,而小園卻盛開著各種梅花,爭紅斗艷,幽香銷魂,令人神清氣爽,我張口就得兩句:“窮冬富有新生意,耐冷梅花斗雪開。”特別是一樹紅梅花怒放在窗前,我寫下幾句新詩:“窗前/開一樹紅梅花/像一團火/把心里的冰雪燒化/把它撒到天上/化一片絢麗的云霞”
四個畫家朋友合作,將我一首七絕詩意畫在一幅四尺徽宣上:“姹紫嫣紅映白頭,無猜鷗鷺掠沙洲。春濃須謝三分雨,云淡飄然一葉舟。”這張畫掛在我家客廳,為人贊賞。
而我與佛門也甚有淵源。武昌蛇山上的龍華寺是明代成化年間辟出的一方凈土,歷經五百四十年世間風雨,今年春夏間應住持之請,我為龍華寺作了兩副對聯:“龍象護莊嚴看花雨繽紛法流永匯;華章誦妙諦聽梵音清遠禪悅長存。”把“龍華”二字嵌在聯首,住持合十稱謝。另一副是:“寺近長江江流不息風帆動;廟枕蛇山山深靜穆釋門空。”從龍華寺地理位置聯想到佛門廣大,慈航垂佑,江流有聲,慧境空靈。
在世間風雨中,盡管理性思考吞噬著我的靈魂,我又常常為友情所感動。黑龍江省的譚敦寰和馬合省李琦夫婦,雙城的張濟,他們都稱我七叔,還有吉林省的陳效方兄,我為他們寫過一首七律:“書生事業倍關情,華發蹉跎歲又更。萬里莽原悲驥老,中宵風雨聽雞鳴。幾回魂夢松江岸,依舊煙云武漢城。幸得良朋如滿月,天涯何處不同明。”
和他們的交往緣自先大兄雷雯。先大兄落籍哈爾濱,取“心遠”二字為書齋名,雖是從陶詩“心遠地自偏”中得來,也確實暗喻地理偏遠。他的部份詩作取名“銀河集”與“煙雨集”,喻其詩短篇多,我曾有詩相寄:“群書萬卷蘊幽懷,浩氣文章跌宕來。風月一樽饒酒興,乾坤獨攬盡詩才。銀河璀璨垂穹宇,煙雨蒼茫響春雷。寥廓云天人遠望,心遠先生幾時回?”
南京大學陳遠煥先生為人真誠熱情,古風猶存。去年我去南京,遠煥兄始終相陪,令人感動。那天他陪我游石頭城“鬼臉”時,突然烏云潮涌,雨驟風狂,遠煥兄未帶雨具,渾身濕透,還搶著給我照相留念。我曾寫下這樣幾句,因自覺不佳,就沒有告訴他。“云黑雷沉鬼臉遮,舊京王氣忽還家。秦淮夜夜燈如火,白下年年歌滿車。蟲臂蟲肝追時尚,民膏民脂壘繁華。相思紅豆隨人老,伴我真情到天涯。”
姜弘兄書桌上有他一張滿面笑容的照片,且他與夫人每年去深圳過冬,去年行前,我送他一首詩,詩題是《題姜弘先生玉照兼祝南行平安》:“白發飄然笑可聞,不堪荊棘說前塵。曾信革命千般假,幸得人生兩頭真。時有文章驚四海,更兼睿智掣長鯨。公今南下迎春去,應逐新雷第一聲。”
姜弘兄和我是五十年的兄弟,肝膽相照。他雙目幾近失明,還為這個小冊子寫來序言,令我十分感動。當我提筆給這個冊子寫后記時,讀著姜弘兄寫的序言,“而今誰識書生”這句悲涼的詞句油然涌上心頭,順著筆,把這些年來寫的一些舊體詩串聯起來,以為后記。
這本小冊子在臺灣的出版,得力于南京現代史學家周正章先生的推薦和臺灣秀威出版公司總編輯蔡登山先生的青睞。我和正章先生在北京紀念胡風學術研討會上朝夕相處,回漢后寫下一首絕句寄贈給他:“借得胡家始識荊,文章驚世息紛爭。寒風凜冽京城路,踏破殘冬萬木青。”這里,僅向周正章先生、蔡登山先生和編輯劉璞先生以及為本書的出版耗費心力的諸位先生致以衷心地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