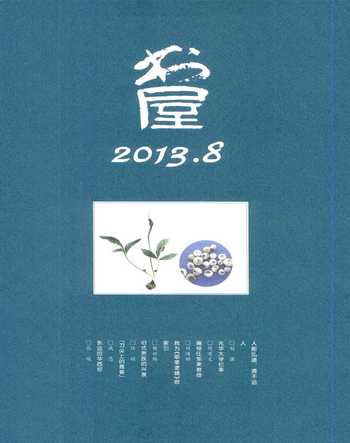“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張寶明
公元前479年,也就是魯哀公十六年,孔子辭世……鮑鵬山在《孔子傳》行將收筆時將其傳主比喻為“千秋木鐸”,并以夫子“自道”的口吻對“無道也久”的社會發出預言:“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論語·八侑》)言簡意賅,在中國這塊廣袤無垠的羅盤上,夫子畢其一生、不舍晝夜,為我們華夏歷史文化勘定出了美輪美奐的思想磁場。從此,一代又一代后學朝圣的故事一直在路上。如果說一部西方文明史是對柏拉圖注解的歷史,那么作為東方文明史東道的我們也不能不是對孔子注解的歷史。中外古今,元典從來都是一個民族或國家不可逾越的祭碑。無論我們走多遠,我們都會時時回眸凝望:畢竟,我們在回答要到哪里去之前必先回答“我們從哪里來”。當下,傳承與創新的命題一直困擾著我們,究竟該傳承什么?失去那余音裊裊的“木鐸”,我們不但無法確證自己是誰,而且也難以找到回家的路。
沿著鮑鵬山的筆墨,孔子重新向我們走來。盡管滄桑、坎坷、顛簸甚至流離之路曾經讓我們在千年風雨中慘淡曲折,但是真正能夠讓我們回歸正途、直趨燈塔的還是孔子那振“道”發“義”的“木鐸”。在技術、專業、信息滿天飛舞的今天,也只有“木鐸”才能點燃岌岌復岌岌之人文薪火的火種:走上“道”,再出發。在沒有想好路怎走之前,這時的“道”比“路”更重要。在這個意義上,傳承和復興的地位絕對不亞于創新和開拓。因為一旦失“道”于人,人再將“路”走歪,代價將沉重而慘痛。這,歷史一次又一次地給出了殘酷的證明。好在我們唇槍舌戰,為“大學精神”爭來爭去之時,鮑鵬山攜著孔子來了。閱讀《孔子傳》,它至少省卻了我們在浩如煙海之經典中打撈“大學何大之有”的定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禮記·大學》)幾千年前的孔子早就想到了,而且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之大學三項功能之前重點加上了以“道”為中心的“文化”傳承。鮑鵬山跟著夫子的“木鐸”振動出了幾圈暈輪:“大學學習的目的,是要弘揚一個人偉大高尚的德行。”“大學”是指一種學問。這種學問的目的,簡言之就是“學大”,學著讓人大起來:
簡單地說,大學就是大人之學,就是君子之學。它不是培養人的專業技能,甚至也不是灌輸一些靜態知識,它立足于培養人的價值觀和價值判斷力,讓人學會對世界上紛紜復雜的事物做判斷,同時培養人的高貴品格和氣質,養成人的大眼光、大境界、大胸襟、大志向;不是為了就業,而是為了成人;不是為了一己謀生,而是要為天下人謀生,謀天下太平,爭人類福祉!可見,“大學”的內涵,至少不是我們今天講的對于技術的學習,而是提高德行,是養成人格,然后改造社會,這是大學的最根本含義。
毋庸諱言,在經典和注解之間,難免產生張力。這種張力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存在,這可以說時時有、事事有、人人有。張力,如果不是常識性的錯誤,那就是“必要的張力”。問題是我們的注解如何在回歸的前提下緩解、化解甚至消解這一緊張。乍讀這本書,如果不與其“天時地利人和”,那就不只是張力的問題,至少部分的大學校長就會把它當成胡言亂語甚至瘋人瘋語來一陣拳打腳踢。我理解的鮑先生“木鐸”聲中的“不是”判斷并不是不需要,而是要先聲奪人,一再強調“道”的獨一無二地位。筆者以為,在還原經典卻無法無縫對接的情形下,我們至少可以不是“只為了”。比如大學不是不需要“培養人的專業技能”,也不是不考慮就業,但那并不是唯一。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們要銘記的是:價值比知識更重要,品質比技能更重要,“成人”比專業更重要,一言以蔽之,前面有一“道”風景線無法逾越。
孔子有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論語》)縱觀孔子的一生,橫豎都將探究宇宙人生的大道作為自己一意孤行的使命,始終將提高自己的人格境界作為臻于至善的人生目標。他既沒有迷官(場)喪志,也沒有玩(器)物失志。“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道出了其出“道”早,將一生奉獻給學問、真理的少年大志,“志于學”即是“志于道”的開始。在一個現在大多數少男少女爭相“賣萌”的時代,這樣的立志打破了“道之不傳久矣”的局面。從其對弟子子夏關于“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的諄諄教誨中,我們便能領略其擔當道義、心系天下、志存高遠的公共知識分子情懷。在齊、魯、衛、陳、楚諸國并立的年代,他沒有流于某一國,也沒有滯留于某一地,更沒有投于某一人,他的道一以貫之,無論何時何地,都以情懷布“道”,“天下為公”的大同信念在牢牢存儲在了孔老夫子隨身攜帶的移動硬盤里,物化在振聾發聵的“木鐸”里。
在夫子那里,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與生俱來,如同充盈著暖意和愛意的太陽,盡管云層可能不時遮擋住其光輝,但其光彩照人的放射卻不舍晝夜。道義的擔當從來如此:不但心中有道,還要樂于布道。誰都知道,心中有道是第一步,行走在布道的路上是第二步,可這第三部也是最難的一步則是如何在泥濘荒蠻、荊棘塞途的崎嶇險徑中一直走下去。更何況,他不只是流螢相伴,他要經常要在沿途的歧路中回答那些對自己膜拜有加的弟子們的質詢。如果是一位厭世、避世的隱者也就罷了,弟子們恰恰跟的是避地、避國、避人卻不避世的大道擔當者!風正勁,夜正冷,路在何方?老夫子周邊的小夫子的接踵而來追問也是充滿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和現實關懷:老師,“君子亦有窮乎?”“君子亦有窮乎?”這里的“窮”,不僅僅局限于金錢上的窮困,更多指的是人生挫折、事業坎坷與政治上的窮途末路。這句話翻譯成白話:老師啊,您不是常說我們這些沿著崎嶇陡峭山路擔當大道、尋求真理的人會達到輝煌頂點嗎?為什么我們在世間還會如此困厄而一籌莫展呢?
平時我們看到的性格直率、心中充滿陽光的學生子路這次提問非同凡響。可以說是一次最有問題意識的發言,真正代表了孔老先生得意門生的水平。因為子路之問問出了一個千年秘密,也是中國幾千年哲學史上、倫理學史上的一個大命題:一個人既然按照至高的道德準則去行事,就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為什么回答總是否定的?是啊,弟子們可以問這問那,甚至問一些鬼神之類的看似刁鉆的問題,那些提問并不難回答,但“君子亦有窮乎”這問題恰恰戳到古往今來知識分子的囧處。我不好推斷孔老師當時有沒有有辱尊嚴的情緒反應。要知道,今天攤上這樣的直逼人心的富有挑戰性問題,老師們大抵是要一句的:“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乎?”你小子是不是覺得跟導師跟錯了,從現在開始,你我不是師生,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歷史有據,夫子淡定,再淡定,最后還是淡定!當子路一肚子帶著怨氣去質問老師時,老師卻一副氣清神定的姿態:“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孔子回答的簡單明了、意味深長。其含蓄的底蘊被幾千年后懷抱原典的鮑子悟道并一語道破:“君子本來就應該是常常走投無路的。”不,準確地說,鮑鵬山不是一語道破,這里還有更為精彩的闡釋與言說:
道德并不能保證道德之人人生順遂。希望通過實行道德來保障自己順遂,更不是人的最高境界。
如果你認為做個君子處處都能夠夠行得通,到處都能受歡迎,那我告訴你,錯了。恰恰相反,君子正因為他講道德、講原則,他追求進取卻又有所不為,所以他常常是被制肘的,時時是被雍阻的,往往是行不通的。”
在這兩段對孔子悲觀而又崇高的注解中,讓人至少讓筆者悲喜交加。在前一段,我不禁想到“五四”時期批孔先驅陳獨秀的話:“道德不是用來責人的,而是用來律己的。”這些的確是對道德極其透徹的理解。而后一段話,我想起了新儒家馮友蘭的一句話,中國哲學就是“接著說”和“如何說”的問題。對鮑鵬山而言,他顯然接住了這樣一個大命題,而且將孔子當時欲言又止、想說而又沒有說完的話發揮得淋漓盡致。當年的孔子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的呢還是要把這個話題故意甩給諸如像鮑鵬山這樣的夫子?毋庸諱言,我本人同意鮑鵬山的“半醉”:“君子以成人為最高追求,小人往往不擇手段地去追求成功。君子當然也追求成功,但是,君子在追求成功的時候不以人格的喪失作為代價,在成功和成人之間必須做出選擇的時候,他一定選擇首先保有人格尊嚴。而小人正相反。”這話我還有另一半:亂世和寧世截然兩端。一心尋求公平、正義和大同理想的孔子啊,不正是想通過他和弟子們努力讓“亂世狗”成為過去嗎?他老人家清楚:未來的安康社會,“寧世人”必將以道德準則、法律規范行事,那時的世界才真正變成了我們一再期盼的美好人間。這一點,也是作者在《自由與道德》一節中點破的那樣:“真正的道德人格一定是自由的人格;真正的道德人生是自由的人生;真正的道德社會一定是自由的社會。孔子,以其一生的修行,告訴了我們道德與自由的這種關系。到達這種境界的人是寬松的、從容的、愉悅的、自由的,又是合乎道德的、體面的。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自由和道德的結合。”及此,也許,子路及其同學的問題不言自明矣!
“君子固窮!”孔子的淡定回答,不止說他老人家已經在回答之前習慣性地捋好了思路,而是說他對道義擔當、尋真求理過程中人在囧途的凄涼、慘淡乃至迷茫有著充分的心理準備。滿載一車的星輝,義無反顧地走在尋求希望之光的旅途上,漸行漸遠,因為他心中有夢。這個夢不是魯國夢,也不是齊國夢,也不是衛國夢,而是行大道的中國夢、世界夢、天下夢。仰望天空,那“夢”在孔子的心中是星星,是月亮,更是太陽,這個夢不會因為一時一地的稍不如意而掉頭回傳,也不會在大禍臨頭也時“斯濫”!這樣說,從孔子一路風塵后的彼時彼景中可以證實。在“仁者擔當”一節,鮑鵬山這樣描述孔老師及其弟子在陳、蔡兩國之間陷入孤境、窮困潦倒的尷尬情形:兩國大夫們圍追堵截,將一批匡世濟民、理想遠大、仁慈博愛、德行高尚之有擔當、有追求、有信仰的布經傳道“君子”隊員團團圍住,一心傳(大)道、布(圣)經的師徒一行陷入了千年之迫、萬年至窘之中。我想子路此時的一肚子的怨氣很有代表性,號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的圣人被弄得灰頭土臉,竟然落魄到斯文掃地的這步田地,何至于此啊!正是在這個關節上,孔子撫琴吟唱:“君子固窮!”這可能是自古及今無人能比的“中國好聲音”。如果此道不是一以貫之,這一“聲”就難以讓人信服,更難以讓叫“好”經久不衰、延綿千年。
“志于學”,樂以忘憂;“志于道”,不知老之將至。將“學”與“道”統一起來并作為畢生的追求,孔子用一生的堅守履行了自己的諾言。這個統一不但改變了中國文化史,而且改變了包括政治史的整個社會系統。學統、道統、政統,在孔子“志于學”的影響下開始分離,出現了一批帶有公共知識分子性質的士大夫,這比西方早了幾千年。學術獨立是第一步,這一步開啟了一個獨立的職業,不再依附于政治;“君子不器”是第二步,這一步又有進一步的分離,它將以學術為職業的“稻粱謀”士人與道義擔當的士大夫區別開來,開啟了人文知識分子的先河。學問與道德、知識含量的多少與人文關懷的高低從來沒有必然的關聯。一個化學家或物理學家可能只埋頭生產化學武器或核武器,而且追求的目標是殺傷力越大愈好,這樣,他可是一個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專家,與孔子所說的為誰的“道”是兩碼事情;民國時期的王闿運可以是一代學問宗師,但他為袁世凱稱帝寫的頌歌則是金錢作祟。這里的知識、學問與人文、道德構成巨大反差。回眸歷史,我們有怎么能不平添幾分對夫子的敬仰?
先人已逝,逝者如斯。孔子臨終前唱出的最后一首歌還在這里:“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死了,子孫還在,絕學不絕。我想,無論是對過去的“先人”還是對當下的“來者”,借用《孔子傳》的精神:理解比崇拜更重要,同情比仰慕更需要,因為古往今來的圣者都曾活在“當下”過,寂寞圣哲之間的對話從來都是穿越時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