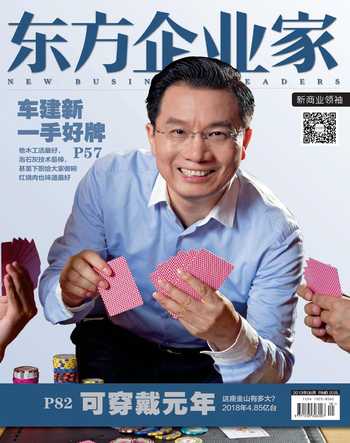白宮“好基友”:基辛格&羅斯福
時黛
尼克松喜歡說自己行動大膽而出其不意,總是強調自己和基辛格有多么不同。“這是個不可能的組合,”他回憶說,“威提爾小鎮雜貨商的兒子和希特勒德國來的難民,政治家和學者。”
但讓二人聯合在一起的“黑暗的”紐帶不是他們外表的差異,而是內在的相似性。當他們各取所需獲得自己長久向往的權力后,發現彼此都是有深深的不安全感。兩人都是實力政治的實踐者,結合了冰冷的現實主義和以權力為核心的政治信條,用基辛格寫俾斯麥的話說就是:“不受道德顧慮的牽絆。”兩人都相信:“外交政策必須建立在對力量的評估基礎上,不能感情用事。”
在一次和戈爾達·梅厄的談話中,尼克松把《圣經》里的為人準則干脆扭曲成了赤裸裸的權力游戲,“我在處理國際事務上的規則就是,‘別人怎么對你,你就怎么對他。”這時基辛格插嘴說:“而且是110%地這么干。”對基辛格和尼克松而言,在事后補救過失以及繞開國務院行事方面,道義上的考慮并不非常重要。
基辛格說俾斯麥“不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他總善于操縱敵對勢力間的怨恨,以此對各方加以約束”。無獨有偶,尼克松和他都是駕馭和利用怨恨敵對情緒的高手。兩人都多疑、詭秘,都把人往最壞處想,喜歡設套讓敵手之間“狗咬狗”;都是毀謗中傷的行家,在挑撥離間和對付共同的敵人方面有共同話語。就像基辛格說俾斯麥“從不接受反對者的任何好意”,尼克松和他都認為那些挑戰其權威的人背后有著不可告人的骯臟目的。
“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有某種程度的多疑癥,”長期擔任基辛格貼身助手的勞倫斯·伊戈爾博格(Lawrence Eagleburger)有著敏銳的洞察力,“這讓他們彼此懷疑對方,但也使他們能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在外交政策管理上他們有一套玩弄陰謀詭計的路子。”除此之外,兩人都是孤家寡人,而且喜歡這種感覺,這就使他們更熱衷于偷偷摸摸行事。他們不愿和他人分享信息或功勞,和下屬或同僚打交道時總是顧左右而言他,閃爍其詞;都喜歡給對手出其不意來個“驚喜”,從越南談判到軍控談判再到中國問題,全部暗箱操作,不跟國務院商量,然后再戲劇性地公開結果。
基辛格善變的性格讓兩個人這些共同點更加突出,他們彼此強化著各自的偏見。在一起的時間遠遠超出了正常的范疇之外,很快,基辛格和尼克松結成了對抗整個政府官僚體系和一個“敵對”世界的陰謀家聯盟。
當然,真正把兩個人聯結在一起的是他們對外交事務的口味、熱愛和感覺。兩人在一起大部時間都像是在開研討會,天馬行空地把世界大勢瀏覽一遍,討論他們將要訪問的地方。在基辛格的輔佐下,尼克松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訪問莫斯科和北京的總統,而且是在同一年。基辛格說過,要想把外交摸透,必須不停地把所有關聯的因素放在一起加以考慮,甚至早上刮胡子的時候也要想。尼克松做到了,雖然胡子和政策都弄得不怎么樣,但他的確是不多的幾個連刮胡子時也在考慮外交政策的人之一。
盡管有如此這般的共性,基辛格和尼克松在個性上仍有顯著差異:基辛格對周圍世界的一舉一動十分敏感,對自身在其中的作用尤其在意。尼克松不然。
這一區別表現在很多方面。基辛格對任何人的批評都覺得寢食難安,尼克松則裝聽不見、掩耳盜鈴,沉浸在自己的白日夢里;基辛格拼命改造他的敵手、非要把不同意見扳過來,尼克松琢磨的是如何打壓反對派;基辛格喜歡個人交流,尼克松怕得要死;猶太難民生氣時會朝所有有份的人大發雷霆,尼克松遇有不快則退避三舍,思忖著如何報復。面臨挑戰時,基辛格喜歡著迷般地仔細研究對手,尼克松則躲得老遠;基辛格能抓住各種細節,尼克松則信馬由韁,連問題最主要的方面也把握不好;基辛格思路清晰,總能直擊問題要害,尼克松跟著直覺走,總在互相沖突的幾個選項之間一連數小時猶疑不決。
關于尼克松和基辛格,最有說服力的比較來自國務院老牌官員、卡耐基基金會主席托馬斯·胡夫斯1973年的一篇演講:
兩人辦事永遠都是偷偷摸摸的,但基辛格做得更招人喜歡;
都憎恨官僚體系,但尼克松選擇了逃避;
都喜歡夸夸其談,但基辛格說得讓人信服;
都強烈反對意識形態,但尼克松會在反與不反間搖擺不定;
都是不可救藥的權術操縱者,但尼克松透明度更高;
都要求別人無條件擁護,唯獨基辛格更能博得批評者的好感;
疑心都很重,不過基辛格更加合群;
都不尊重憲法第一修正案,基辛格卻總能讓媒體著迷。
在第一任期(1969~1972)的尼克松每年2月都在白宮二層為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女兒埃麗絲·羅斯福·朗沃茨(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舉行生日宴會。埃麗絲是喬治城社交界和華盛頓政治權勢組織的元老級人物,雖然尼克松很討厭這兩個圈子,但又不得不討好。宴會通常只有六個人:尼克松夫婦、朗沃茨夫人、基辛格和專欄作家約瑟夫·阿爾索普夫婦。阿爾索普夫人說:“尼克松一般會讓亨利盡情表演,他在一旁和大家一塊聽著,臉上洋溢著得意的神情,就好像亨利是他珍藏的獎品。”不管談什么話題,尼克松都會湊到客人身旁說:“朗沃茨夫人,我想您一定想知道亨利有什么看法。”
這就是尼克松對基辛格最初的態度:引以為傲,還夾雜著幾分敬畏。就像一個被冷落的孩子,手里忽然攥著一件讓周圍人重視他的寶貝東西時,便有一種憤憤不平而又揚眉吐氣的興奮勁。擁有基辛格讓他最感快意的事情是,他挖了洛克菲勒的墻腳,尼克松一直忌妒他。霍德曼曾說:“尼克松總對洛克菲勒手下的人垂涎三尺、視若賢才,原因不外乎是他們的老板是個想買什么就能買什么的主兒。”尼克松沒有肯尼迪炫目的身世和光環能吸引大批文人,也沒法像財大氣粗的洛克菲勒把出色的頭腦都買至帳下,但如今憑借他的總統寶座,還是能把洛克菲勒王冠上的鉆石撬到自己手里。“他對此頗引以為樂。”演講稿撰寫人威廉·薩菲爾說。
尼克松渴望奉承,基辛格極愿提供,各取所需,二人之間的關系很快復雜密切起來。基辛格很快成為尼克松的第一寵臣,不離左右。和一個如此復雜多面而內心沖突的總統過從甚密,親近也就意味著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