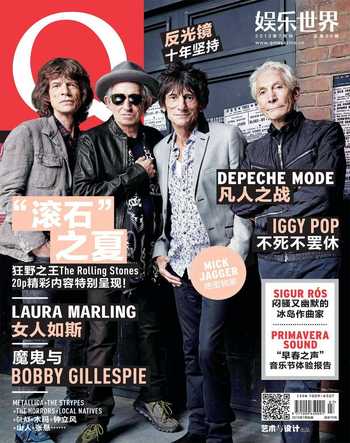山人樂隊: “土”卻不俗的中式雷鬼
lulu
起山人樂隊,還是挺有故事的。清楚地記得幾年前在地壇舉辦的民謠音樂節,當時下起了大雨,現場所有設備全部撤走,演出的地方搭起了雨棚,所有人圍在一起,純粹來了一場“不插電”。 山人樂隊是當天最后一個演出,雨沒有要停的趨勢,大家卻丟掉雨傘在雨里和小不點光著腳跳起舞唱起歌。那是記憶中印象特別深刻的一場演出,也因為這次音樂節,讓很多人聽到了來自云南大山里的最美最不一樣的聲音。
今年5月,山人樂隊正式推出了自己的第2張專輯《聽山》,距離第1張專輯發布的時間,已經相隔4年之久。單從專輯的封面就看得出來,“山人”洋氣了不少。
從剛開始錄制這張新專輯,到最后出成品,其實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對這張專輯而言,我覺得我們有一點‘回歸的感覺,‘往回收,回到原點這樣的狀態。”主唱子寒跟Q談起新專輯制作過程中的感受,“這次我們更多的是把自己本身的聲音展現出來,對‘社會和生活這方面的內容投入得少了一些。不像第1張專輯那樣,唱得更多的是對生活的認識和感受,而且也會有一些很浮躁的東西在里面。而這張,我們更希望它起到一個‘指向的作用,指引大家去關注,是這樣一個概念。”
如果你認真地聽過他們的第1張專輯,你會發現他們用幽默和機敏調侃著生活,是走出大山后,離城市不那么遙遠的聲音。但4年后的這張專輯,卻更加充滿了“民族”的味道,比如其中的“左腳調”、“佤歌”等。“我們想通過這張新專輯讓更多的人了解‘民族的東西,因為那種東西可能過一陣就沒了,最后變成文物,或是真的就消失了。很快,可能幾年以后就沒了。我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對民族音樂做些“保留”。也希望更年輕的音樂人們也會來做這樣的事,讓這些民族的東西更具生命力。”
即興,在“山人”的音樂里無處不在。“音樂永遠沒有固定的東西。你要想加東西,可以加一萬種。當然,在一首歌定型之前,大家會討論出一個大概的方向。所有的音樂人在做出一張專輯之后,都會有推翻自己的地方,都有遺憾。音樂是沒有盡頭的,是此時此刻,過了就過了。”音樂如人:歡樂,隨性,有特點。隨時的一點情緒,踩著舞步唱出來,讓人不知不覺聽“進去”了,音調一轉,又連忙被拉進了另一個世界。
“我們算錄音錄得比較少的,最理想的錄音狀態應該是演出現場那種‘不刻意的感覺。但現在錄音棚還是有局限性,時間上會有限制,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我們很快就會錄我們的下一張專輯,會結合視頻一起錄,挑一個適合的野外環境進行錄音,在那種很隨意的狀態下,很自然。”
因為新專輯的制作工作是請外國人來做的,品質上來說要好一點。“他們的技術會更專業一些。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他們畢竟是老外,不像我們云南人對自己的東西那么了解。就像讓一個老外去聽京劇,是一樣的道理。另外,由于語言溝通上的障礙,整個錄音時間多了一倍。”
僅闖出了大山,還走向了世界。近幾年“山人”頻頻走出中國進行演出。“差別真的很大!”他們這么評價國內和國外的音樂節。說起剛參加完的“日本橋之下世界音樂祭”,他們感觸太多:“他們非常重視自己傳統的東西,會更多地推廣自己的文化,這是最大的區別。國內的音樂節大部分還是推廣歐美、日韓以及中國港臺地區的音樂,整個音樂節的風格也和國外比較著名的音樂節沒什么區別。這次日本的音樂祭上只有我們一支中國樂隊,而且我們的音樂對于他們來說是非常新鮮的,所以反響很不錯。”說著,樂隊幾個人都面帶自豪地笑了,“有一件事給我們的印象特別深刻,就是我們在西班牙演出的時候,當我們要上場的時候,舞臺旁邊的保安表現得很不屑的樣子,但當我們演完之后,他立刻上臺幫我們收東西(笑),他覺得我們和其他中國的樂隊不一樣,我們的音樂很特別很好聽。中國音樂走出國門進行交流的,大部分還是京劇,或是中央歌舞團什么的。其實很多老外根本不喜歡那些東西。”鼓手小歐接著解釋:“國內外在音樂上的交流方式可能不太一樣。比如在國外演出的時候,外國人更多地是會去關注音樂本身,用什么樣的旋律,和什么節奏融合在一起,當曲子一響起時,他們就會跟著跳舞;也就是說,他們更在乎的是這段音樂有沒有意思。而在國內,大家首先會看這個樂隊有沒有名,而且他們更關注你唱的詞是什么,聽你唱的這段和他們的生活經歷是不是能產生共鳴。”
中國目前的很多音樂還是拷貝國外的東西,什么時髦就做什么,缺少了太多自己的東西。拿最簡單的來說,現在在年輕人眼里,最流行過的節日還都是那些西方的節日。其實很多時候中國人還是覺得自己是土的。音樂上,也一樣。
可以說,“山人”一直都是把民族音樂保存得非常好,卻又在不斷地創造著新東西。他們在運用民族特色樂器的同時,也會在自己的音樂中加入雷鬼、ska等元素,保持著這種平衡。“其實國外的一些音樂元素在云南很多少數民族音樂里都有,比如雷鬼和ska,只是國外比我們更早地運用了這些元素。”艾勇認真地跟Q說,“比如這次我回云南,叫了一幫朋友演出,很多當地的朋友在現場跳起民族舞,和雷鬼的節奏完全融入在一起了,我都驚了!舞步的感覺都一樣。包括這次我們去騰沖,有個喇叭隊演奏的都是民族樂器,有管樂有鼓,那個節奏完全就是ska的節奏。這些都是寶貴的財富,也是我們想挖掘和發展的。但不能直接拷貝,還是要所謂的‘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修修剪剪之后呈現給大家。”所以說,民族音樂有很多值得我們去關注和保護的,而每個人的眼睛都是往前往遠看的,但當你停下腳步,回頭看看自己民族的東西,那些你以為只在大山里才有的音樂里,有雷鬼,有ska,有hip-hop,也有blues,有的是驚喜。全世界的音樂其實都是相通的。
對于“中西結合”,山人有著自己的想法:“這是必然的趨勢。世界各地的音樂交流越來越多,會產生許多的‘化學反應,可能就會產生新的東西,這是一件特別好的事。‘變通才會越來越有生命力。但這種融合也要和當下的社會生活有關系,這樣即使突破了大眾的審美習慣,人們也會樂于去感受。假如‘山人把云南的民族音樂原封不動地搬過來,拍子很復雜,很多人都會聽不慣。”這讓人突然就想到了前一陣的北山世界音樂節,薩克斯和二胡的結合、搖滾遇到咸水歌,這樣的“中西合璧”雖然乍一聽有點無法接受,但仔細聽來,還是會有不一樣的新奇東西迸發出來,是音樂的魅力所在。
“山人”的音樂離不開舞蹈。如果你看過他們的現場,你一定會明白那種“不跳舞就不會唱歌”了的感覺。他們說,有些曲子之所以要跳舞是因為如果不跳起來,就一定會亂了節奏,因為那些節拍非常復雜。而云南那邊的舞蹈每個動作都是有生活的影子,所以只有跳著舞才會更有感覺。
經過了城市的“熏陶”,在“山人”的身上還是能直接感受到大山里的氣息。“生長環境決定性格”是他們給出的答案。“我們從小就在民族地區長大,在大山里,骨子里的東西改不掉的。”而他們惹人喜歡的地方,也正是那些最簡單、最質樸的東西。
新專輯推出之后,“山人”又忙著做起下一張EP,云南ska,打算今年晚些時候發。然后,就是找一些朋友在野外支起設備,錄個視頻,以最自然的姿態,把他們想做的事兒趁早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