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沉默的大多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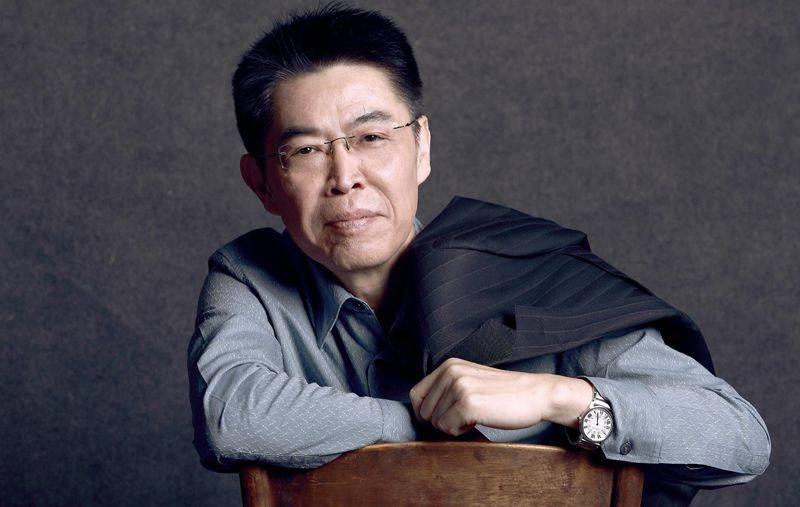

印象
你找到那片凈土,整個環境的物理性就不存在了
任何一個小慨率事件如果稍微錯位,都不可能成為現在的你。一次看似尋常的結緣,回頭望望,其實都意味深長。
如果沒有發生這件事,張昭的人生可能有另外一番不同的書寫。
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是一個正在恢復自信和商業活力的中國,她忙亂、騷動和熱烈。同時對于很多人來說,充滿了吸引力。赴美留學的張昭,毅然在香港回歸祖國的1997年,回到了祖國。這一年,全球最熱映的電影是美國好萊塢拍攝的《泰坦尼克號》。35的他,意氣風發。(在此之前的七年,他在美國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后轉入電影系,獲得電影制作碩士學位。)
回到國內的張昭,收到不少片方邀約。其中有一個電視劇比較特殊,不僅全程需要在美國取景拍攝,而且當他們找到張昭的時候,電視劇已經開機了。也就是說,張昭要做的工作只是,接替上一任導演完成接下來的拍攝。這是一名在當時幾乎家喻戶曉的大導演,因病入院故拍攝終止。張昭去總政醫院看他,謙卑請教工作,發現他無心戀戰,令張昭深感意外的是,他為何在盛名之下活得如此痛苦?為何臺前的風光帶來的卻是如此巨大的壓力?他得了抑郁癥。
從醫院走出來以后,北京的天空下起了雨,地面有些滑,躲躲閃閃之下,一輛出租車停在了張昭身邊,正準備上車,拉動車門,反復幾次怎么也拉不開。見狀,司機從車里鉆出來,圍著出租車繞了一圈,把門打開后,又冒著雨小跑了回去。“就這個場景,我心里一動,聯想到那位導演,我問自己:你愿意活得像他那樣嗎?還是像這位出租車司機,能為別人帶來點什么。我謝了他好幾遍,他開心得不得了。”人生有一些啟蒙點,跟年齡沒關系。那一刻的感受,張昭形容說,突然間曙光照到了你。
加之,這期間張昭拍的幾部影視作品,市場都不太成功。用張昭的話來說“中國電影當時沒有商業市場的概念”,由此,他決定轉型,從導演轉型當制片人,后來他又轉型做公司。“我總結自己的經歷就是,不斷的在撤退,退居到公共視野之外。其實你退了,往后退,你的事業越大,當然承擔的責任也越大。”在復旦大學學信息工程的時候,他當過電視主持人,做過舞臺劇演員,組織過學生運動。
而另外一方面,注重細節,思維習慣是以小見大的張昭認為,只有不斷地往后退,你的眼睛才能看到更多的人。這雙眼睛,曾幫他看到過中國民營傳媒企業的希望。
這就是傳媒界熟知的“一盤餃子”的故事。2003年冬天的一個早上,剛從美國出差回國的張昭,下了飛機就直奔當時還在紫竹橋辦公的光線傳媒。他與光線創始人、同為復旦校友的王長田一直談到中午12點。到了飯點時間,王長田從辦公室抽屜里拿出一大盒餃子,“這是我媽包的”。又從另一個抽屜里取出三種辣醬。“一下徹底把我打倒了,要想在中國做事,沒有睡草席的力量是不行的。”無論多少次提到這件事,張昭的眼睛里都有光芒。那個冬天一過,他就從上一家“體制內”加入了光線。
在中國的創業環境里,有很多的沙漠,比如政策的沙漠、人才的沙漠、資金的沙漠。王長田倡導“駱駝文化”,平時將脂肪存在駝峰里,如果遇到危機,可以消耗自己的儲備。它們置身于“被VC綁架的商業世界”之外,這種反周期生存的方法,在生意場上并不多見。張昭在光線八年,深受其團隊文化影響,以至于今天有樂視的同事會對他感嘆:“不愧是從光線出來的”。我們采訪的地點就在張昭的辦公室,與同一水平線上其他企業家、職業經理人寬敞考究的辦公室相比,他的辦公環境略顯簡陋,一張沙發接待來訪者,辦公桌上擺滿文件,背靠著一面白色書柜,每一格都有拉門,也不知陳放何物?看得出他是個謹慎的人。而整個辦公室,面積不足25平米,這是他自己的要求。隔壁是一間面積約60平米左右的會議室,他們曾建議張昭在這里辦公,被張昭斷然拒絕。“不管你今天市值多少,要永遠處于一個創業狀態。”而在商業社會里,艱苦樸素的風格,本身就是一種競爭力。
商業領域里還有句老話叫:渠道為王。學理工出身的張昭,相信公式的力量,萬變不離其宗。企業里的公式,就是商業模式。商業模式包含了四個內容,產品模式、用戶模式、營銷模式、盈利模式。他認為中國電影的產業之路,就是渠道。2006年,他成立光線影業的時候,就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不做大片,也不建院線,而是靠發行和營銷制勝。
當今天我們津津樂道于光線在電影《泰囧》和《致青春》上創造的票房奇跡時,也許很少人知道張昭曾是一手打造光線發行團隊的幕后功臣。“我還記得我面試第一個孩子的情景,他從外地過來。他們現在都跟我關系很好,當年我們是建了一所黃埔軍校,后來大家都從光線挖人。”張昭說起來的時候,臉上掛著滿足的表情。
張昭的做事風格是嚴格。在他的團隊的工作,你可能會有一些壓力。首先,這么多年來一直堅持管理的探索,他有一定的標準,“我的團隊文化是這樣,什么事你別敷衍了事,這樣走不遠。”其次,他事無巨細,一個海報都要管。“我到現在都沒有年齡感,我不是經常會想起自己是多少歲數的人,跟郭敬明合作,都是很平等的。”
還有一點,他豁得出去。這點更多的是表現在張昭的人生選擇上。2011年,光線上市之際,他從光線轉投樂視。許多人為他惋惜。雖然這背后的曲折、行業的發展等可能是另外一個商業故事,但單從他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這種隨時隨地都可以重振旗鼓的樂觀自信,非一般人。“我這一輩子就是一個不斷重新開始的人,從信息工程到哲學到電影,從科學走向哲學走到藝術,我一直是這個狀態。”
“你怎么會有那么多的勇氣?”我試著問。
張昭笑笑,然后回答我。“那天我們公司的一個老總跟我說,你現在是公司所有的高管當中,唯一一個無房無車無戶口的人。我現在還是個北漂,所以又怎么樣。其實就是說從來沒有擁有過什么,那為什么要怕失去呢?那你就永遠可以重新開始了。每次我都從一個一年級學生開始,很好。我一直是這樣覺得,其實生命的價值就在不斷地創造,這個確實是我的人生觀。”張昭的坦誠超過我的想象,這一段時間以來,他接受的采訪可能超過了之前的所有,我以為我會面對一個隨時都能信口開河的人。
又回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一個紐約的冬天,像所有中國留學生一樣,二十八九歲的張昭也靠打工賺取一部分生活費。有一次,在送外賣的過程中,自行車剎車壞了,他措不及防地撞到了電線杠上,褲子破了,眼鏡碎了,外賣也撒了,然后瘸著腿,推著自行車一步一步回到餐館,把當天掙的小費還給他們。他沒有抱怨,也不覺得狼狽,很麻木的回到家里,那是一間只夠放一張床的小屋。回到家的時候才發現腿上流了好多血,簡單清理完傷口,他打開一本教科書《電影導演I》,放在膝蓋上,書的第一頁什么內容也沒有,他盯著這張空白頁很久很久........
“對一個男孩子來講,成長特別重要,經過這些事情,讓你體會個人的渺小,人其實不能完全左右自己的命運,我從來不去想那些規定動作,到了幾歲該做什么,我是一個嚴重不走尋常路的人。當一個事情成為你生命的支撐點的時候,你沒有那么多的雜念,任何挫折對我來講不意味著什么,你跟我談什么房子、車子都沒意義。那個空白頁是一個很純粹的很忘我的狀態,這是我的幸福感。你找到那片凈土,整個環境的物理性就不存在了。”
這也是他多年人生的一個寫照。
對話#
我們共謀一個未來
一個職業經理人要藏起自己的個人夢想,要為產業服務。我很認同馬云說的一句話:中國現在需要的是,有職業經理人素質的企業家,或者有企業家視野的職業經理人,把這兩個結合起來,個人利益就在企業資本價值和產業回報。
林:前段媒體鋪天蓋地的宣傳,我想知道“二張”合作的細節,比如,你們怎么認識的?
張:其實挺簡單的,就是一個偶然的場合,一次朋友聚會。我對他接下來做什么感興趣,他對我離開光線也好奇,就聊起來了。講到培養新導演、互聯網國際化,這是我們共同關心的話題。
林:當時向他拋橄欖枝的公司和個人有很多。
張:有很多,但這個很正常吧。我覺得是巧合也不是巧合,巧合就是說,如果我沒去,他沒來的話,我們就聊不上。不是巧合是指,冥冥之中我們也應該合作,大家想法一致,都走在產業的這條路上,合作是早晚的事情。我們幾十天就談成了這個合作,其實最重要的是,大家是不是在一條道上走?
林:事實上,張藝謀電影的審美一直保持在那,很難改變。而樂視影業的定位是互聯網時代的電影公司,用大數據說話,迎合市場。這跟張藝謀的品位是有偏差的,我疑問的是,他能不能、愿不愿意拍像《泰囧》這樣的影片?
張:很好的問題,那我要問你的是,你覺得《泰囧2》還有這樣的票房嗎?
林:我覺得不會。
張:那好了,你按照這個思路去想。 我沒有讓他迎合,我跟他的合作,是奔著一個現在還沒有呈現出的一個未來去的,然后我們共享這個未來,不是為我們今天服務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很多人都用這樣的思維想:他來了,對我們現在有什么用?
林:所以張藝謀他也不用著急,現在就呈現一個什么東西給大家看?
張:你說他還需要嗎?他得過那么多獎。
林:說實話,這一兩年來,我覺得他“胸中塊壘酒難澆 ”,挺需要一個證明的。
張:產業這個事情,不是要去滿足大家的期待。你滿足了今天的期待值,就滿足不了未來的期待值。其實價值就在于別人今天看不見你,但是你看見了你為之去努力的東西,這也就是企業對于資本的價值。前天我跟萬達院線的葉寧聊起這個事情,他說:原來是這樣,我們沒想到。
林:什么令他沒想到?
張:其實就是一些戰略性的合作。我給你舉個例子,兩年前我跟你說《小時代》現在的營銷方式,你肯定不認,今天《小時代》做出來了,電影還能做出這樣的影響力來。我們跟張藝謀的合作也一樣,我腦子里想去做的事,我一步一步會做出來。大家別忘了張藝謀的品牌是創新,他之所以變成大師,不是因為他這么多年一直在創新嗎?
林:你怎么看“中國合伙人”,比如你跟王長田、你與賈躍亭、你和張藝謀?
張:這個可以很坦率,《中國合伙人》講的問題是這些人在生命的某一瞬間,相互依靠做一些事情,但實際上,我覺得這個是其次的。第一,還是資本責任和產業責任,你要搞清楚你對什么負責,你的商業模式是否滿足最大多數的人?變得更有資本價值,同時推動產業的發展。第二,是職業化,這個很重要的。第三,如果大家有一些共同的理想,這些理想必須是同時滿足前面兩個條件,你才能有價值。
一個職業經理人要藏起自己的個人夢想,要為產業服務。我很認同馬云說的一句話:中國現在需要的是,有職業經理人素質的企業家,或者有企業家視野的職業經理人,把這兩個結合起來,個人利益就在企業資本價值和產業回報。
林:身為光線的股東,你如何看待未來樂視與光線的競爭?
張:我首先是希望光線做得好,這個很重要。另外就是,我希望能夠告訴大家,任何一個公司都是厚積薄發的,真正扎實打下過基礎的企業,一定會有表現好的一天。我覺得光線具備這樣的品質,長田倡導的駱駝文化還是有他很大的空間。他們能做到今天,我一點都不吃驚,我心里清楚得很。第二,就像《小時代》和《不二神探》一樣,同臺競技又如何?我們都在一個舞臺,大家跳各自不同的舞,看誰跳得更精彩?這個行業發展很快,不過幾年,我們都變成了老公司,看誰走得更遠?新公司要起來,它要琢磨這個公司的商業模式,那個公司的發展模式,還挺有意思。
林:某種程度上說,每個公司的商業模式也可能將經歷一輪或幾輪洗牌?
張:理論上是的,其實現在任何一個產業的變化都是很快的,尤其是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使得其對所有傳統行業都產生很大的影響,而互聯網本身變化也很快,幾年前有些所謂獨領風騷的互聯網公司現在已經不見了。所以我說傳統行業的十年是互聯網的一年。這個時候像電影這樣的傳統產業談商業模式就很重要。樂視影業的商業模式就兩個著重要出發點,一個是互聯網,一個是國際化。
林:你和樂視影業的野心都不小。
張:中國已經誕生了全球最大的PC公司聯想,吉利已經并購沃爾沃,誕生了全球性的汽車公司,每個行業都有相似的可能,可能是因為現在的中國人確實是比較有理想,有野心。第二,中國有這么龐大的消費人群,中國文化產業的消費人口紅利才剛剛開始,所以依賴這么大的一個本土市場是有機會的,至于是不是要把國際化當作是一種目標,我覺得是看公司的發展。但是以哪種方式去國際化,其實是取決于創新,國際化是要創新的,你給世界的電影產業帶來什么樣新的商業模式,這個是走出去的核心,你要對整個的國際電影產業有貢獻才有價值,不管是從產品上還是從商業模式上,如果有貢獻那就應該分享,你出去其實是分享,對別人也有啟發,中國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電影市場,到了2020年說不定就變成第一大市場。你知不知道六大公司在美國的票房是多少,最大的不超過15個億,而且很多年沒漲了,以后也不會大漲。到了2020年中國市場的規模是多少,400億、500億,你占了市場份額10%是多少,40億、50億,差不多就10億美金,你占20%就是100個億人民幣,近二十個億美金,國際并購的機會理論上是成立的。所以不要妄自菲薄,我覺得依托中國市場的中國電影公司通過并購實現國際化是有這個基礎的,但是要不要變成一個國際化電影公司,其實是取決于你的貢獻,你沒貢獻別國際化,你有貢獻了那你就應該拿出去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