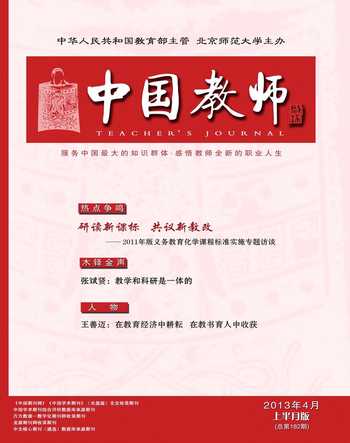王善邁:在教育經濟中耕耘 在教書育人中收獲
曹夕多
王善邁,中國著名教育經濟學家,中國教育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現任北京師范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和學術委員、北京師范大學首都教育經濟研究院院長,同時擔任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教育經濟學會理事長等職務。
一、北師大情緣
王善邁教授1955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學校教育專業,1958年畢業留校任教至今。從1958年起,王善邁教授分別任教于北京師范大學宣傳部、政治教育系、馬列主義教研室、經濟學系(該系于1996年組建為北京師范大學經濟學院,于2004年更名為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在北師大工作和生活的50多個春秋,王善邁教授同北師大結下了深厚的情緣。
問:從求學到工作的50多年,您在北師大經歷著不同的人生階段,您對于哪一個階段最為留戀?
答:我在北師大度過了青年時期的學生時代,參與了50至70年代的歷次政治運動與生產勞動。改革開放以來,專心從事教學與學術研究。現在回想起來,每一個階段都很寶貴。從教學研究來說,收獲最大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學術研究階段,但讓我最為留戀的還是青年時期的學習階段。
問:在北師大度過的學生時代,讓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答:學生時代非常短暫,但卻為我的一生打下了良好基礎。那個時候大學一、二年級進行通識教育,人文社會科學專業普遍開設中國和世界通史、中外文學史等基礎課程,三年級以后才進行專業教育。通識教育使我有了較寬廣的基礎學科知識。我至今記得心理學的彭飛教授,他是一個學術嚴謹、哲理性很強的人。中國文學史、外國文學史分別由鄧魁英、穆木天教授任教,我通過上這兩門課程閱讀了大量中外文學名著。邏輯學由朱啟賢、馬特教授任教,他們是中國當時最著名的邏輯學家。
那時的生活雖艱苦但卻很有規律。我每天都要跑上3 000米,還要參加學校田徑隊、排球隊。我曾擔任北師大男排校隊的隊長,并帶領校隊獲得北京市高校排球賽的冠軍。這些鍛煉奠定了我良好的體質基礎,并且使我每一天的學習都精力旺盛。
那個年代的一大特色就是政治運動與生產勞動較多。上學期間,我曾參加“肅反”運動和“整風反右”運動,并參與過十三陵水庫和密云水庫的修建勞動。剛剛留校工作的時候,我曾赴河南信陽地區遂平縣調查人民公社。1964年,我在北師大參加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后又赴山西省武鄉縣參加“四清”運動。我經歷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其間參加了農業生產、電機生產,在農村和工廠的工作和生活累計有3年多。這些社會實踐活動雖然占用了許多學習和研究時間,但卻讓我提高了政治覺悟、積累了社會經驗、熟悉了工農業生產知識并鍛煉了堅強的意志,這些都是我人生的寶貴財富。
問:您經歷著自己的人生,也見證著北師大的改變。在您的眼中,北師大改變的是什么?不變的又是什么?
答:北師大最大的改變是從一所師范院校發展成為綜合性大學,現在正向世界高水平大學邁進。不變的或者說傳承下來的是師大特有的文化傳統,比如在思想政治上,有愛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在學術研究上,嚴謹踏實,不斷創新;在生活作風上,艱苦樸素,積極向上。
二、教育與經濟的交叉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經濟學是國家級和北京市重點學科,王善邁教授作為該學科的北師大學術帶頭人,帶領出一支結構合理的高水平研究團隊。幾十年來,王善邁教授承擔了數十項國家級課題和國際組織的研究項目,發表論文近百篇,出版學術著作十余部,多次獲得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獎勵,在教育經濟學領域累計培養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百余人。王善邁教授創辦了北京師范大學首都教育經濟研究院,多次為政府的教育發展和教育財政決策提供咨詢服務,并參與相關法律和政策的制定。
問:您怎樣選擇了教育經濟學這個學科研究方向?
答:從事教育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并非是我的自由選擇,而是出于國家和社會需要以及我的教育學和經濟學雙重專業背景。我本科學的是教育專業,工作后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進入人民大學舉辦的高校政治經濟學教師“資本論”研究生班,比較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恩格斯和西方早期的經濟學經典著作。1981年,時任教育系主任的黃濟教授要求我對教育系孫喜亭、靳希斌等教師編寫的《教育經濟學講座》進行修改和統稿。1983至1985年,我和北京大學厲以寧、陳良焜教授作為負責人,承擔了國家社科研究重大項目“教育經費在國民收入中的合理比例”研究,其成果在國家做教育決策時被采納。這兩件事促使我開始涉足教育經濟學研究。1984年,由北師大教育系和經濟系聯合申報,獲批了教育經濟學碩士學位授予權。1996年,由我主持申報并獲批了教育經濟學博士學位授予權。從此,我從業余逐步走向專業,開始了教育經濟學的研究。
問:幾十年來,在教育經濟領域,您對于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教育資源配置方式、教育體制改革、教育財政和教育財政制度、教育成本與效率、教育經濟學學科建設等內容都進行過深入研究。從2010年起,您作為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的首任委員之一,參與到國家教育體制改革的咨詢工作中來。請問在這兩年多的工作里,您是否對于教育經濟學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有新的認識與收獲?
答: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共分成10個工作小組,我擔任第九組“保障體制機制改革組”的副組長。在兩年多的工作里,通過對6個省和6所部屬師范大學教育體制改革試點項目的調查,我對教育投入保障有了兩點新的認識:第一,所有的教育體制改革項目都應以相應的教育資源投入為保障;第二,教育資源投入及其有效配置和管理必須以相應的制度來規范和保障。
問:從創建到發展,您親身經歷并見證了中國教育經濟學科的過去與現在,您怎樣看待該學科的未來?
答:教育經濟學是一門教育與經濟學交叉的、新興的、應用型學科。在教育領域中也有資源的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效益等諸多經濟問題。教育經濟學就是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回答稀缺的教育資源如何有效配置的問題。該學科對于一個國家的政府、學校、企業、家庭的教育決策與管理有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國基于時代和國情的需要,于20世紀80年代初從西方和蘇聯引進了該學科。經過3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教育經濟學在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隊伍建設與人才培養、決策與管理支持等諸方面獲得了長足發展。但它還是一個年輕的、不夠成熟的學科,對我國來講,亟須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我國已有了良好的基礎,展望未來,這一歷史使命定能實現。
三、為師的體悟與收獲
作為師者,王善邁教授奉獻了幾十年,也收獲了幾十年。王善邁教授對學生很嚴厲。在政治思想上,他要求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具有社會責任感;在學術上,他要求學生踏實積累、獨立思考、胸懷大志、有所作為。當王老師的學生,在學習和學術上不能有絲毫馬虎與懈怠,要實實在在地付出才能順利過關,這一點學生們都明白。
嚴厲的王善邁教授對于學生也很關愛,節假日有空,學生們會到王老師家聚餐、玩撲克牌;過年不回家,學生們會到王老師家守歲、吃餃子;生活上遇到困難,畢業了要找工作,工作后遇到煩惱,學生們都會到王老師家,尋找親人般的依靠。對于學生來說,王老師家就是他們在北京的家。
最讓學生感動的是王老師在癌癥和心臟病的手術和治療期間,心中最惦記和放不下的還是學生。給學生修改論文、與學生探討學術、關心學生的就業與生活,這一幕幕經常發生在醫院的病榻前。在學生的心中,王善邁教授用幾十年一點一滴的行動,詮釋著“師者”的內涵。
問:作為一名從教50多年的資深教師,您對于“師者”有怎樣的體會?“師者”的角色,讓您有怎樣的收獲?
答:作為高校教師,在教書上必須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并不斷探索。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教師必須具有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在育人上必須身體力行,力求為人師表。
常言說教學相長。學生代表著未來,他們富有的朝氣和青春活力深深地感染著我,促使我在教學與科研中與時俱進、不斷進取,在精神狀態上年輕化。我曾經患癌癥和心臟病,在住院手術治療和康復期間,學生們給予了我精心的照顧和無私的幫助,讓我永生不忘。我能戰勝病魔并健康工作,與學生們的無私奉獻是分不開的,可以說學生是我生命的動力。
問:在您50多年的師者生涯中,除了收獲,是否也有辛酸和艱難呢?是怎樣的力量一直支撐著您?
答:在數十年的工作中,我經歷了許多挫折和磨難,如1959年因對人民公社化持有不同意見而被指為“右傾思想”作檢查,“文革”中因莫須有的罪名被打成“反革命”遭受一年多的批判,因患癌癥和心臟病兩次大手術瀕臨死亡,等等。但這些絲毫沒有動搖我對事業的執著和生活的熱情,我想這背后支撐我的是一個共產黨員的信念和對教書育人這份事業的熱愛。
問:作為一位師長,您對于現在的學生和青年教師有怎樣的寄語?
答:我感到現在學校乃至整個社會比較浮躁,許多人自覺或不自覺地熱衷于爭名利、爭資源、爭權力,進行種種“包裝”,學術腐敗屢禁不止。我衷心希望學生和青年教師能抵御各種誘惑,潛心學習和研究并持之以恒,用辛勤勞動為中華民族的振興、為祖國的繁榮昌盛效力。我愿與我的學生共勉之。
(本文由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通訊編輯部供稿)
(作者單位: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北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孔榮 柯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