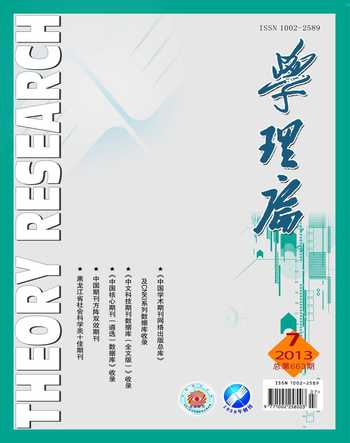論儒學與專制沒有必然的聯系
閻秀芝
摘 要:儒學與專制的關系一直是學界論爭的熱點,對于這一問題,我們的觀點是儒學與專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儒學之所以被誤認為和專制有必然關聯是在它成為官方哲學后被術化的結果,從它的精神實質方面看儒學是反專制的,即使在它成為官方哲學后仍然對封建專制起到了限制作用。
關鍵詞:儒學;專制;精神實質;反專制
中圖分類號:B2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1-0061-02
對儒學與封建專制的關系,學界一直存在爭論,經過詳細考察與梳理,我們認為儒學與專制不存在必然聯系,為論證這一觀點,我們從三個方面進行闡述:第一,從儒學的產生看,儒學不是為政治服務,更不是為專制服務;第二,儒學后來確有被專制利用的部分,但儒學的被利用是術化的結果,不表明儒學的本質如此;第三,儒學成為官方哲學后,仍對封建專制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一、從思想與社會的關系看,儒學與專制沒有必然的聯系
孔子創立的儒學產生于春秋末期,這是一個“禮崩樂壞”,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出現嚴重變動的社會:周天子的權威出現動搖與衰落,王道喪失;周禮所規定的倫常秩序紊亂,人們的正常生活喪失了依托。孔子對這種局面深感痛惜,他立志依據周禮,以繼承夏商周三代文化為己任,恢復正常的人倫秩序。可見孔子創立儒學的著眼點是人類正常社會的建立,即人怎樣才能過上正常有序的社會生活,其基本途徑是恢復周禮,重構倫常秩序,故有“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說。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儒學反映了西周的社會性質,西周的社會性質決定了儒學的實質和發展取向。這恰是從思想與社會的關系做出的基本論斷。
關于西周的社會性質問題前人已有明確的界定,且已形成共識。如楊向奎先生說:“西周是‘宗法封建制,西周大宗是最高統治者;小宗是自由平民、士,他們是國人的主要成分;而野人則是受奴役的殷人”[1]。許倬云對西周社會則做了如下描述“周君和各種不同等級的大夫們組成了諸侯國中的權力集團。他們統稱為貴族,……次于權力集團的階層是士”[2]8,“真正的生產者只是那些庶人和親自耕種土地的士……庶人有義務在土地上勞動來養活那些上層階級的人”[2]10。從兩人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西周社會是一個由大宗共同統治的宗法共和制社會。其中士、自由平民、殷商沒落貴族為國人,下層的士、庶人和受奴役的殷人為生產者。西周社會既然是大宗共同執政的宗法共和制,必然不會形成周天子的專制統治,相反在周王朝發展的后期,由于分封的諸侯國勢力的膨脹,周天子的權力被削弱,逐漸喪失了統治權,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此外,國人在政治上也有一定地位和權勢,如周厲王時期的“國人暴動”就是很好的明證。社會存在決定思想狀況,西周既然不是專制社會,立志要繼承周禮的儒學就不可能和專制有必然的關聯。
孔子思想產生之初,其關注最多的是“周禮”,以及如何利用“周禮”重建良好的社會秩序,孔子早期即以“知禮”聞名于世。但他在推行“禮”,希望以“禮”改變社會現狀的進程中,處處碰壁。這就迫使他進一步思考“禮”之不行的根源,并發出了“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的感慨。這一時期,孔子認識到“禮”作為外在規范,要想推行無礙,還要靠“仁”的內在自覺來保障,即“仁”是“禮”的內在根本,“禮”是“仁”的外在體現。但這時孔子思想的重點剛從“禮”轉向“仁”不久,仍非常重視“禮”,故有“克己復禮為仁”之說。孔子思想發展到中期,已不再以克己為仁,因此原憲問孔子“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貢問仁時,孔子答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到了晚期,孔子明確指出“仁者愛人”。可見,孔子的思想由重“禮”,到“忠恕之道”的提出,再到“仁者愛人”思想的成熟完善,“仁”成為其學說的主體,在“五常”中以“仁”統攝其他。其后的儒家繼承了孔子“仁”的思想,落實在政治上,發展為“仁政”、“德治”等思想,強調統治者要重民、愛民,對百姓要“富之”、“教之”,反對以武力壓迫百姓,體現了反專制的精神。
儒學和專制沒有必然的聯系,而且從實質上講,它是反專制的。而儒學之所以被認為與專制有必然的聯系,和它后來被專制統治利用有關。
二、從儒學的精神實質看,儒學和專制沒有必然的聯系
儒學被誤認為與專制有必然的聯系,為專制統治提供理論基礎,和儒學后來被專制統治利用相關,而儒學被利用是儒學被術化的結果,不表明儒學的本質是專制的。儒學被術化源于西漢,董仲舒為了求得儒學的生存權,有意無意地改變了原始儒學的一些精神實質,做出了一些有利于專制統治的思想變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三綱”思想。董仲舒把“三綱”引入“五常”,以“三綱”來統攝“五常”,強調上對下、強對弱的控制,強化專制思想,并把這種專制思想歸結為“天意”,以此說明專制思想的合法化。董仲舒的變革,使儒學在與別派的斗爭中脫穎而出,得到統治者的重視,成為官方哲學。但儒學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它偏離了原始儒學的人文思想,使儒學和專制發生了一定的聯系。
這種術化背離了原始儒學的精神實質,不能以此標明儒學的本來面目,我們要判斷儒學和專制是否存在必然聯系,就要從儒學的精神實質而不是從其被術化的狀態去著手。
儒學是積極入世之學,與社會發生著廣泛的聯系,有的學者因此把儒學分為政統的儒學、道統的儒學和學統的儒學。學統的儒學以文化傳承、弘揚人文精神為己任,本身是反專制的;道統的儒學以“道”的價值理想作為士人的價值追求,從道不從勢,反對偏離“道”對權勢、利益的屈從,顯然是反專制的;儒學落實為政治理念、為政統的儒學。有人從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統治下,儒學和政治的結合出發,認為儒學必然是專制的。這種觀點有兩個誤區:一是儒學落實為政治理念形成為民本思想而非專制思想;二是專制的形成是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所致,并非儒學導致或強化了專制。
其一,儒學在政治上為民本思想,主要體現為它的重民思想和德治理念。儒家繼承了先古“民為邦本”的思想,認為“本固”才能“邦寧”,因此人君要重視百姓。如孔子認為對待百姓要做到“使民如承大祭”。孟子提出了“民貴君輕”的著名思想。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按照孟子的說法,民眾最為重要,民心所向,才能成社稷,為君主。荀子也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而君之所以能治民,要君自身正,而后正人,“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在治理國家的問題上,儒家強調德治思想,要求對民眾進行道德教化,以倫理規范引導百姓,重視百姓的意愿,實行“以德服人”的“王道”, 反對以暴力和強制對待百姓。孔子要求當權者治理國家要遵守恭、敬、惠、義等道德原則,即“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又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這都體現了儒家以德統政的“仁政”思想。
其二,從專制的形成看,儒家不應對專制負責。我國有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傳統,在這漫長的時期中,儒學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有人把儒學和專制聯系在一起,認為儒學導致或強化了專制。眾所周知,專制產生的根本原因是社會制約機制的缺乏,這在今天已成為共識。如果硬要說儒家要對專制負責,只能歸結為儒學沒有發展出一套強有力的社會制約機制,只是從道德的層面對當政者進行規勸,僅僅緩和了專制而不能解決專制,最終卻被強有力的專制政治壓制。如果要追尋一種思想為專制負責的話,即是法家思想。法家要求把權力集中于君主一人,臣子要無條件地服從君主,君對臣民百姓有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由此產生的結果是,“任何社會勢力,一旦直接使專制政治的專制者及其周圍的權貴感到威脅時,將立即受到政治上的毀滅性的打擊。沒有任何社會勢力,可以與專制的政治勢力,做合理的、正面的抗衡乃至抗爭”[3],必然導致君主獨裁專制統治。
三、儒學作為官方哲學仍對封建專制發揮著抑制作用
儒學成為官方哲學后,遭到了專制的利用、扭曲和壓制,但它沒有成為專制的附庸,而是態度鮮明地主張限制王權,甚至對君主專制進行強烈的批判。現以事實說明之。
其一,《二程集》中程頤的《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對宋神宗直接提出尖銳批評:
人君因億兆以為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恒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于天,一事之不合于理。如此,王道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為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為自得,銳于作為,快于自任,貪惑至于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后悔[4]。
程頤的批評直指宋神宗,認為宋神宗在推行“熙寧新法”的過程中,沒有做到“盡其至誠惻恒之心,視之如傷”,而是“以天下徇其私欲”,結果就是“適足以致負敗”。因此,程頤要求宋神宗“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作為施政原則,防止君主個人意志的膨脹。
其二,黃宗羲對君主專制的強烈批判。如果說程頤的批評尚屬體制內的規勸,黃宗羲則直接對君主專制本身提出質疑。他對君主專制下的君、臣、法都進行了尖銳的抨擊。
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黃宗羲認為,君王的職責在于為天下人興公利除公害,君與民的關系應是“天下為主,君為客”,君王履行此職責,必須“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
為臣之義應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然而后世人臣同樣偏離此義,他們視天下和人民為君主的私物,他們所思所憂者,是如何維護君主的專制統治,成為君主的爪牙和幫兇。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為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黃宗羲從君、臣、法對封建君主專制展開了全面而猛烈的批判,其理論前提即孟子“民貴君輕”思想的展開。它在批判君主專制的同時還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社會的理想方案,主張依據“天下為主,君為客”的原則,限制君權,學校議政。王夫之也主張限制君權,反對絕對專權。無論是黃宗羲還是王夫之,都把百姓作為天下的根本,強調限制君權,體現了儒家一以貫之的“民本”思想和反專制的精神實質。
參考文獻:
[1]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82.
[2]許倬云.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流動[M].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3]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1卷[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91.
[4]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