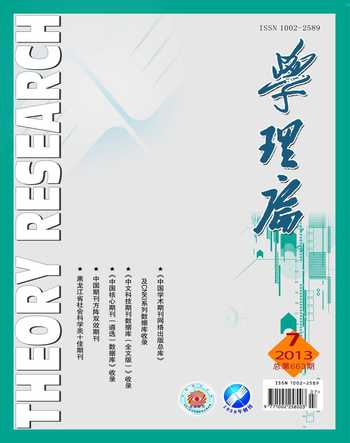試論議會組成人員的人身特別保護權
張蕓
摘 要:議員是現代社會代議制民主政體的基礎,各國憲法對議員職務權利都予以了充分保障,人身特別保護制度的設立更是展示了各國憲法理念的共性與差別。對議員的人身保護可謂由來已久,由于對其內容、本質的解讀的不同,針對此所產生的有關“特權”的爭議也頗受關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設立在此問題上汲取了各國立法的精華并結合具體國情有所發展。試圖從議員人身特別保護制度產生的原因入手,對我國人大代表人身特別保護制度的運行狀況進行簡要探索。
關鍵詞:議員;人身特別保護制度;特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1-0127-04
近期,南方周末上的一篇報道引起了筆者的關注。溫州市人大代表、宣達集團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葉際宣被指控涉嫌行賄非國家工作人員,警方擬對其采取強制拘留措施。但由于葉際宣所擁有的“特殊身份”,若要限制其人身自由,必須事先經過溫州市人大主席團或常委會通過。因此廣西玉林市公安局委托溫州市公安局向溫州市人大常委會提請了一份許可報告,但最終未獲通過。這一事件再次將人大代表的“特別保護權”推上了風口浪尖,一時引發了人們的激烈爭論,也引起了筆者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深入研究和討論議員的人身特別保護權這一問題,對于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證權力機關組成人員依法行使職權具有重要意義。
一、議員①人身特別保護制度的法律淵源與產生原因
對議員的人身特別保護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紀初期的英國議會制度。實際上在15世紀早期,英國的下議院就將對議員的特別保護運用到了民事訴訟當中,但由于受到王權的制約,適用范圍相當有限。如1397年,一位下議院議員因提出減少王室經費的議案,而被國王以叛逆罪而科刑[1]201。直到1737年議會特權法通過才使得議員的特別保護真正成為現實。美國借鑒了英國的這一制度,在1787年憲法第1條第6款規定:“兩院議員除犯叛國罪、重罪以及擾亂治安罪外,在出席各該院會議及往返各該院途中,有不受逮捕之特權。”德國1850年普魯士憲法中也規定:“任何議會議員在會議期間未經議會授權,不得因犯罪行為被搜查或者被逮捕,但在犯罪時當場或者因此行為在次日被逮捕的不在此限。”我國現行憲法也肯定了西方對議員的人身特別保護制度。現行《憲法》第74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非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主席團許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非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可見,對議會組成人員賦予特定的人身保護權,是各國的普遍做法。
議員作為人民的代表,手中握有憲法賦予的神圣而不可剝奪的民主權利,代表民意、上傳下達,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石。而為了保障民主制度的順利實現,保障議員能夠更好地行使職權,各國憲法對議員無論從生活方面還是司法方面都予以了特殊保護。人身保護制度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它與代議制民主的產生與發展是密不可分的。議員是代議機關的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針對其人身所做出的任何決定更應當審慎。設立議員人身保護制度還能有效維護議會等代議機關的權威,對于樹立代議機關至上的社會價值觀有重要意義。應當注意的是,東西方國家設立議員或代表的人身保護制度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西方設立該項制度或者賦予議員人身特別保護權的目的還包括防止因政治性政黨逮捕事件影響議會制民主制的運行的目的。而在我國,更多的則會考慮如何合法、有效地保障代表的權利以實現人民當家做主。追本溯源,筆者認為,議員的人身保護制度是議員言行免責制度的延伸與發展。由于議員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其言行不應受國家權力機關或社會媒體的影響,即使在司法層面上也應當享有一定程度的言行免責權,以保障其更好地代表民意、傳達民意。然而,在代議制發展過程中,不乏當權者限制議員人身自由的案例,因此,對于議員人身權利的特殊保護就顯得尤為必要。
二、議員人身特別保護制度的本質與內涵
由議員人身特別保護制度引申出來的是議員的人身特別保護權。人身特別保護權最初是由于反對王權的迫害而產生的,人們希望通過這種豁免權利為議員提供持續的保護,以應對君主對議會權力的各種形式的干涉與侵犯。由于議員是憑借自己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及其職權而享有法律規定的保護性權利或豁免權,不免使人們聯想到可能對民主原則構成威脅的另一種權利,即特權。那么,到底什么是特權?議員所享有的人身特別保護權的本質是不是特權呢?
洛克在《政府論》中寫道:“所謂特權,不外是授予君主的一種權力,在某些場合,由于發生了不能預見的不穩定的情況,以致確定的和不可變更的法律不能運用自如時,君主有權為公眾謀福利罷了。”[2]98根據洛克的觀點,“為公眾謀福利”的特權是正當的,它實現的前提是君主是賢明的,但問題是,一旦出現昏庸的君主,可以任意行使這種特權以謀求或增進不同于公眾福利的利益[2]517,“特權”就變得尤為可怕,因為此種特權是一種“法外之權”,或者超越法律的權利,如果人民不對其加以限制,讓他們憑借自己的智慧正當地使用它,即要為人民的福利而使用它[2]515,就可能使其處于一種非法的狀態。由于人性的不可知性,權力一旦逃脫法律的控制是極其危險的,因此,此種意義下特權——法外之權,必然不能作為議員所享有的人身特別保護權的本質或內涵來理解。
有學者認為,把特權理解為“法外之權”是不正確的,而真正的特權,應當是超越一般權力之上,由某一類人所專有,并為法律所保護的權利[3]95。例如中國封建時期“八議”、“官當”、“上請”等制度,這項制度賦予統治階層的某些有地位或者德高望重者享有免受法律追訴或者減免刑罰的權利,目的是維護統治者的權威。當特權以法律的形式進行了規范,并且享有特權的人理性地遵守和服從法律,就不必然地與違法相聯系。這就與我們所說的議員人身特別保護權的法律設置有了相似之處,但仔細分析,仍不十分契合。
從表面上看,議員所享有的這種“特殊保護”已經超越了普通公民的“一般保護”,有“特權”之嫌,但從實質上來講,議員的人身特別保護屬于一種訴訟程序上的刑事追訴障礙,并不代表議員可以享有免除懲罰或者擁有規避法律的特權,一旦失去代表資格,那么與其相連的人身特別保護權也將消失。對議員人身進行特別保護的目的也不是使某一部分人群特殊化以提升其社會地位,因此也不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相違背。
(一)人身特別保護的主體
從本質上說,對議員的人身特別保護權被認為是專屬于議會的權利,但是其反射給議員,并主要由議員來行使和實現[4]。從各國憲法的規定來看,人身特別保護權主要適用于議員,以及其他為了使議會工作不受到干擾而給予保護的尚未任職或者已經辭職的人員。如1961年委內瑞拉共和國憲法第143第1款規定:“參議員和眾議員,從宣布當選的日期起,直到他們的任期屆滿,或者他們辭職后20天為止,應當給予豁免權,不得被逮捕、拘留、禁閉或者受刑事審判,搜查其人身或住宅,也不得在履行他們的職務中加以中止。”[5]這就意味著,如果代表脫離了議會工作,其人身受到限制不會對議會事務及人民利益造成損害的話,那么就不能再繼續享有人身特別保護。所以,享有特別保護的主體應當是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在代議機關任職的議員或者代表。另外,根據德國《魏瑪憲法》第37條規定:“聯邦國會及各邦議會議員,在開會期間,非得其所屬國會或議會之許可,不得以犯法行為而受審問或被逮捕。唯現行犯當場拘捕或于犯事之翌日被捕者,不在此限。”這一規定說明,享有人身特別保護權的議員不僅限于國會議員,其他各邦議員也因其代表身份而享有此特權[6]。這一點在許多國家的憲法中都有所體現。
(二)人身特別保護的期限
各國立法對于議員人身特別保護的期限的規定不盡相同。有的國家規定議員在任期內享有人身特別保護權利,即無論在開會期間還是閉會期間,議員均享有人身特別保護的權利,除希臘、古巴、西班牙①等國家外,我國也是做出此規定的典型國家之一。就我國來看,除憲法第74條予以規定以外,1982年12月10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第44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非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許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非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如果因為是現行犯被拘留,執行拘留的公安機關應當立即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相對于1982年憲法有關代表人身特別保護的有關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對這一權利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并且提出了對于現行犯應在對其采取控制人身自由的行動后立即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的“報告制度”。此后,在1995年2月28日第三次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35條也做出了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許可,在大會閉會期間,非經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如果因為是現行犯被拘留,執行拘留的公安機關應當立即向該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常務委員會報告。”這一規定不但具體說明了享有人身特別保護權的是縣級以上人大代表,而且將地方各級人大代表享有人身特別保護權與全國人大代表規定一致,體現了人身特別保護制度的普遍性。
而在有些國家,對于議員的人身特別保護制度僅局限于議會會議期間內。如日本憲法第51條規定的:“兩議院議員在國會開會期間不受逮捕。開會期前被逮捕的議員,如其所屬議院提出要求,必須在開會期間予以釋放。”
做出類似此規定的代表國家還有美國、韓國、比利時、菲律賓①等。筆者認為,相對于任期內的保護,該種保護制度的設立范圍較窄,雖能有效防止議員在任期內濫用法律賦予其的保護性權利,但對議員的人身的保護力度明顯減弱,在某些情形下將產生不利于議員有效行使權力的情形,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人身特別保護的內容
各國對于人身特別保護制度的內容保持了較高的相似性,其中最主要的是議員的人身自由。希臘、法國、德國、韓國、古巴、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菲律賓、西班牙②等國也都做出了關于限制議員人身自由權利的一般禁止性規定。英國作為議員人身保護制度的創始國,則對此做出相對保守的規定,其對于議員人身所給予的特殊保障,只限于不得因民事案件而逮捕議員。如議員有犯罪行為,則仍可被捕,只是逮捕機關在逮捕后,必須立即通知議院。英國的這一做法為許多國家在對議員人身特別保護制度做出規定時提供了典范。我國對于人大代表的特別保護權也進行了相關規定,它包含以下幾層意思:(1)人大代表的人身特別保護權只限于刑事案件,不包括民事案件的傳訊和審判。(2)經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常務委員會的許可,司法機關不能對人大代表實行逮捕和審判,體現了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常務委員會的“許可制度”。(3)人大代表如果確屬犯罪且是現行犯,在不拘留就有可能危害社會的情況下,公安機關可以先拘留,但必須立即向大會主席團或常務委員會報告,請求許可,體現了司法機關向大會主席團或常務委員會報告請求許可的“報告制度”等。③
此外,議員的人身特別保護制度的內容通常還涉及諸多程序性問題。我國的“許可制度”以及“報告制度”就是此類內容的典型代表。對于議員人身權利的特別程序性保障可謂由來已久。早在1626年4月18日,英國上議院就通過決議,規定上議院的議員在開會期間,除犯叛亂罪、重罪及妨害治安罪外,非經上議院的決定,或有上議院的命令,不得予以拘押或限制其自由[7]。1875年法國《關于政權間關系的法案》第14條規定:國會議員在會期中,非經議院許可不得因重罪或輕罪受追訴。可見,在對議員人身自由限制的程序性規定中,大多國家都加入了與我國相似的許可程序,體現了各國議員人身特別保護制度內容中的特殊程序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各國在對議員人身特別保護制度的內容進行設定時針對的并不是議員本身,而是著眼于議會制,是議會特權在議員身上的反射權利,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制發展的必然要求。對議員人身保護制度的內容的設定也不僅僅著眼于此項權利本身,其設定對于議員其他權利的實現和職權行使的保障也大有助益。
(四)人身特別保護的例外情形
法律賦予議員人身特別保護并不意味著不加限制地保護,法律同樣規定了許多例外情形。如大多數國家做出了現行犯例外的立法例,這主要是出于保護被害人利益的考慮;除此之外,對于危害國家安全等社會危害性極大的犯罪行為也被排除于特別保護之外,體現了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
除此之外,許多國家還設置了批準程序,即除非得到代議制機關的許可,不得對議員或代表享有的人身特別保護權利予以限制或剝奪。以我國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規定了對于現行犯應在對其采取控制人身自由的行動后立即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的“報告制度”[8]。為了確保公正審判,個別國家還對議員的審判級別進行了意外規定,如白俄羅斯共和國憲法第102條第3款規定,最高法院審議眾議院議員或共和國院議員的刑事案件。西班牙、挪威④等國亦有類似規定。
三、對我國人大代表人身特別保護制度運行狀況的探索
孫中山曾說過:“政治良否,視人與法。”法律制度的健全與否不僅與人民息息相關,更與政治密不可分。作為實踐性很強的人身特別保護制度,如何在不違背立法者原意的前提下進一步完善這一制度,值得我們討論。
第一,關于“許可權”。對于這一點,首先我們應該明確享有“許可權”的主體。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在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由大會主席團做出許可,而在閉會期間則是人大常委會。但由于人民代表大會一般一年舉行一次,而人大常委會每兩個月舉行一次,在其他時間司法機關往往很難找到合適對象以啟動這一程序。所以在實踐中,“許可權”通常被下放給人大常委會主任會或者是其他辦事機構,與法律規定不相符合。其次,對于“許可”的程序,依法律規定,除現行犯以外,凡對代表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性措施,都必須事先向人大主席團或常委會申請。但在實踐中,一些司法機關為了提高辦事效率,往往先采取強制措施,事后才向人大及常委會提請許可。這樣一來,事前的“許可”變成了事后的“報告”,對人大代表的合法權益造成了嚴重侵犯。就這一點來看,我們應嚴格“許可”程序,在堅持現有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制定更為細致的調整人身特別保護權許可制度的相關法律,或者出臺相關法律解釋,在遇到程序問題時有法可依。
第二,關于代表的職業化。戈爾曾在其著述《社會思想》中說:“議會雖自認代表全民的種種,實際上,并未代表全民中一民的任何種切。……欲避免現在議會制度之虛偽,只有一途:即按職業團體規定代表方法,一業一個代表機關。換言之,真正民主政治,不求之于有萬能的一個議會,而求之于各業并立的代表機關。”從戈爾的這一思想可以看出,他認為只有將代表職業化,才能充分代表民意、行使代表權利,并且有助于消除權力腐敗等等議會政治弊端。其實在許多國家,如意大利、波蘭、日本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職業代表制。所以筆者認為,采用職業代表制在我國是可行的。我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在國家政治及人民生活中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如果僅讓人大代表在工作之余考察民意、尋找問題或者僅在人大會議期間對代表提出的問題進行討論表決,那么必定仍有許多問題無法被及時發現、及時解決。另外,代表職業化可以避免代表以代表身份為庇佑,從事一些例如貪污腐敗的犯罪活動,從一定程度上切斷其違法犯罪的途徑。
第三,關于縣級以上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常務委員會提請機關的申請的審查。當司法機關就決定逮捕縣級以上人大代表而向縣級以上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常務委員會提出申請時,主席團或常委會就該申請應對其進行程序性審查還是連同“事實、理由、證據”等實體內容進行一并審查,實踐中存在不同的做法。由于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職能的局限性,無法對案件事實等進行直接審查,因此可能導致許可審查的隨意性。且“許可”作為一種程序上的強制措施,并不必對案件的實體內容進行過多的審查。筆者認為,對于實體內容的審查應屬于有權對公民采取限制、剝奪人身自由的法定司法機關的職能,若主席團或者常務委員會再對司法機關提出的申請進行實體內容的審查,不免有越俎代庖之嫌,而且可能出現不同機關對同一事實行為進行雙重審查的危險性,甚至在審查時出現濫用“不許可”權的情況,妨礙司法。新修訂的《代表法》中,對此情形做出明確規定:“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或者常務委員會受理有關機關依照本條規定提請許可的申請,應當審查是否存在對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進行法律追究,或者對代表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等其他執行職務行為打擊報復的情形,并據此做出決定。”[9]明確了除做程序審查外,還要對“是否存在對代表打擊報復的情形”這一特定內容進行審查,并以此做出是否許可的決定。這一修改明確、完善了我國人大代表人身保護的許可程序,既有利于監督、保證代表依法行使權力,又保障了司法的獨立性,提高了司法效率與公信力。
第四,關于法律上的救濟途徑。當司法機關做對本級人大或常委會不予許可的決定存在異議以及人大代表對于做出的許可決定存在異議時,能否要求復議,向哪個機關要求復議以及復議的程序為何都沒有進行明確的規定。實踐中,往往將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決定作為最終決定,這樣難免人大權力的逾越,并且對于司法機關或者人大代表來說,有一定的不公平性。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人大自身存在腐敗,那么人大的這種“許可決定權”更加容易滋生腐敗。針對這個問題,最主要的解決方法就是建立相應的救濟途徑。首先,對于司法機關對人大主席團及人大常委會做出的不予許可的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人大主席團或者人大常委會請求復議,對于復議結果仍不服的,可以提交上一級司法機關,請求上級司法機關提請上級人大常委會撤銷不予許可的決定。其次,對于人大代表對于人大主席團及人大常委會做出的許可決定不服的,人大代表有權請求人大主席團及人大常委會進行復議,如果對復議結果仍不服的,可以請求上級人大常委會撤銷這一決定。對于前述內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44條有明確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不適當的決議。”因此,建立這種救濟途徑是有法可依的,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
綜上所述,議員的人身特別保護權是一項維護代議機關權威、保障議員履行職責的一項重要權利。但是鑒于實踐中的疏漏,我們仍然需要對其不斷探索與完善。
參考文獻:
[1]蔡定劍.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洛克.政府論(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3]朱興文.權利沖突論[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
[4]易衛中.德國議會議員不受逮捕權研究[J].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5).
[5]徐建波,等.縣級人大不許可逮捕涉嫌犯罪的代表如何處理[J].人民檢察,2005,(7).
[6]李莉.對人大代表不受逮捕權的內容分解與立法建議[J].漳州師范學院學報,2010,(3).
[7]莫江平.人民代表三論——紀念《代表法》頒布10周年[J].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4).
[8]滕修福,等.析“人大許可權”的立法設計和相關問題[J].人大研究,2010,(1).
[9]滕修福,等.代表法修正:進一步調整和規范代表行為[J].人大研究,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