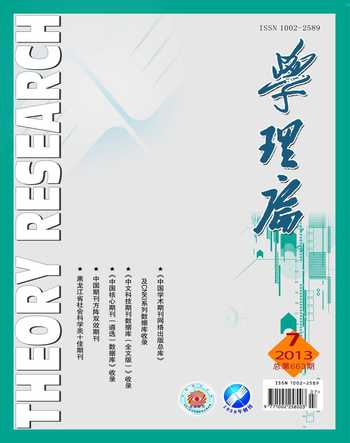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之客觀方面構成要件研究
江凌燕
摘 要:作為毒品犯罪的主要源頭,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必須得到有效控制。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在客觀方面構成要件上存在諸多爭議,法律又未對其進行明確的規定,給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本罪造成了困難。擬對本罪所包含的三種行為進行分析以對本罪之客觀方面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
關鍵詞: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客觀方面構成要件;非法種植;經公安機關處理;抗拒鏟除
中圖分類號:D924.3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1-0136-03
作為毒品犯罪的主要源頭,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必須得到有效控制。然而,法律在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之客觀構成要件方面缺乏明確的規定,給如何認定本罪造成了諸多困難,因此有必要對其客觀方面進行研究,以利于司法實踐的開展。
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的客觀方面是指違反國家的有關規定,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數量較大,或者經公安機關處理后又種植,或者抗拒鏟除毒品原植物的行為。因此本罪包括了三種行為: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數量較大的行為,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經公安機關處理后又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的行為,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抗拒鏟除的行為。本文擬對本罪所包含的三種行為進行分析以對本罪之客觀方面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
一、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數量較大的行為
這一行為界定的關鍵在于對“非法”、“種植”和“數量較大”的認識。
(一)非法
根據醫療、教學、科研的需要,衛生行政主管部門依據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可以在指定的地方種植數量有限的毒品原植物,以生產麻醉藥品。因此種植毒品原植物存在合法與非法之分。上述經許可而進行的種植就是合法的,否則就是非法的。因此非法包括了以下幾種情況:第一,未經主管部門許可而種植的;第二,經許可種植,但數量超出法律規定或者許可的范圍;第三,經許可種植,有種植權,但在規定范圍以外的地方種植的。這三種非法的種植是構成本罪的前提。
(二)種植
對種植的界定涉及罪與非罪以及本罪之犯罪停止形態問題,是本罪認定的關鍵。但對于什么是種植,理論界有較多的爭議。有學者認為,種植就是播種、插栽、施肥、割收津液和種子的行為[1]。有的學者認為所謂種植,是指以收獲為目的的播種、培植(如灌溉、施肥、鋤草等),包括自己種植、培植和自己生長或他人播種由自己培植兩種情況[2]。還有的學者認為,行為人只要參與了其中一種,即可構成種植[3]。又有學者認為,只要是播下了種子,即使尚未實施管理和收割,就可以認定為實施了種植毒品原植物的行為[4]。還有學者認為,種植是指從播種到收獲的全過程,只要實施了此過程中的任一行為,即可認為實施了種植行為[5]。這些觀點從不同的角度界定了什么是種植,都明確了種植行為的農業特性,并將其中一種行為的實施即定性為種植。但這些觀點都較為簡單,不夠全面,對于準確把握本罪還是不夠的,因為它們都只是涉及了種植行為普通的農業特性,而未關注其能區別于他罪的本質特征。筆者認為,作為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的種植之把握,本質在于對收獲行為的界定。當然有的學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并且提出種植認定的關鍵除收獲外還有出苗前的行為。認為播下種尚未出苗就被查獲的,以犯本罪論定為未遂,以種植面積和正常條件下出苗成活率計算數量[6]。但筆者認為,將出苗前的行為單獨列出來實際上是將種植行為復雜化了。出苗前就定為本罪是可取的,因為種植是一種行為,此罪乃行為犯罪,只要行為人實施了任一種植行為就表現其犯罪行為已經著手,達到法定數量即構成本罪,不管其是否只是播種,播種以后有沒有出苗,有沒有收獲。否則就不入罪。至于在成立本罪的前提下,如何認定其犯罪停止形態以出苗為既遂標準就有待商榷。如果以出苗定為本罪既遂的標準的話,那么在出苗后的任何行為都不可能定為其他的犯罪停止形態。然而法律卻將收獲前自動鏟除的行為作為犯罪中止而免除處罰,這就產生了矛盾。而且,出苗完全是一種自然行為,以一種自然行為來劃定人的責任也是有失公平的。因此以出苗作為既遂的標準缺乏說服力。結合本罪的法律規定,筆者認為以收獲行為作為既遂標準最為恰當。首先,從農業活動的角度來看,種植無不是為了收獲,如果不是為了收獲,那么此種植行為就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也不符合本罪的立意宗旨。本罪的設立就是旨在控制毒品生產、販賣和吸食的源頭,使制造毒品無原料可用。如果種植不是為了收獲,這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就幾乎不存在了。不存在社會危害性或者社會危害性微小的行為當然就不能構成犯罪。只有當種植行為以收獲為目的,才能顯現出其種植毒品原植物后可能從收獲中生產出毒品,為毒品生產提供原料的社會危害性和本罪的立法本意。另外,按照常理推斷,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一般都是以收獲為目的的。因此,本罪應以收獲為既遂,其他一切種植行為,如果在未收獲之前被查獲,皆屬未遂,但都要以本罪定罪量刑。而準備種子尚未播種下去,由于種植行為還未實施,當屬預備。這樣一來,收獲前自動鏟除的行為自然可作為犯罪中止而免除處罰。而若將出苗行為單獨列出,則使本罪的犯罪停止形態難以分清,更難以認定。
收獲行為的重要性除了其作為本罪犯罪既遂認定標準的意義外,還包括對收獲行為本身屬性的認定。因為對罌粟進行收獲割漿的行為具有雙重屬性,既是農業活動的收尾,又可以直接生產出生鴉片成為制造毒品的開端,這使種植與制造易生競合。而對于收獲行為的定性,理論界存在兩種觀點。其一為:行為人種植罌粟后割漿收獲鴉片的,既觸犯了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又觸犯了制造毒品罪,按重罪吸收輕罪,定制造毒品罪;行為人僅實施了割漿行為,判直接以制造毒品罪論[7]。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收獲割漿僅是收獲,只有在生鴉片的基礎上進行加工、提煉才屬制造[8]。
筆者認為后一種觀點更為可取,但對收獲割漿行為也不能如此簡單定性。收獲割漿行為既是前農業種植行為的必然結果,又與加工、提煉等工業制造行為的行為密切聯系,因此不能將收獲割漿行為孤立視之,一概而論,而應當結合行為人收獲割漿的前后行為來定性。這里應分為四種不同的情況來處理:第一,收獲割漿僅僅是農業活動的必然結果,終結行為,具有強烈的自然屬性。如果行為人種植毒品原植物,從播種到收獲割漿就終結了,這只是一個完整的農業活動行為,應只以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論。第二,如果在種植、收獲割漿之后,行為人又對所收獲的毒品進行加工、提煉,則又構成制造毒品罪,應數罪并罰,而不能單獨定制造毒品罪。第三,如果行為人只是收獲割漿,而后又以其為原料提煉毒品,未參加前面的農業活動,則以制造毒品罪論,因為這時收獲割漿行為對于行為人本身來講并非農業活動的終結,而是制造毒品的開始,這時的加工提煉已經吸收了前面的收獲割漿行為。第四,如果行為人僅僅參與了收獲割漿的農業活動,未參加之前的農業活動,而后也未參加之后的加工、提煉,還是應以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定罪處罰。因為這里不存在后制造行為吸收前行為的問題,而僅僅是實施了種植這一系列農業行為之一。此時如果以制造毒品論就加重了行為人的責任。
因此,對于種植,筆者認為應該這樣界定:種植是指以收獲為目的的從播種到收獲而終結的任一農業活動。至于罌粟種植中具有雙重屬性的收獲割漿是否構成本罪種植毒品原植物罪之種植,需聯系行為人的前后行為進行界定。
對于種植還存在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對于以自己制造毒品為目的的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應如何定罪?
有的學者認為,應認定為制造毒品罪的未遂。因為此時種植毒品原植物已成為以制造毒品為目的的有機一環,如果以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認定會輕縱罪犯。有的學者則認為此種情況是預備行為,但也應獨立成罪,不能以制造毒品罪的預備論[4]。
筆者認為前一種觀點不妥。如果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因為是制造毒品的一環就應被目的行為吸收而不能獨立成罪,那么種植、制造、販賣也都可以構成一系列統一的活動,制造也可以是為了自己販賣做準備,那此時的制造是否也應該被販賣行為所吸收而不能獨立成罪呢?如果是這樣,法律完全沒有必要對毒品犯罪的各種形態予以分開規定,只需要一個籠統的“涉毒罪”就夠了。既然刑法將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獨立成罪,那么無論此種行為處于毒品犯罪的何種階段,其目的是什么,結果歸于何處,只要具備了本罪的法定要件,就應成立本罪。如果行為人既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又制造毒品的,當然應該對二行為進行數罪并罰。另外,對于那種在種植階段就被查獲的,要認定其行為的目的是為了自己制造毒品而定其制造毒品罪,在司法實踐中較難操作,因為除了行為人自己的供述外,往往很難找到其他的客觀證據予以證明。而且同樣的種植行為,僅僅因為其主觀目的不同,客觀上還未有行為表示,就進行不同的處理,顯然是有失公平的。
(三)數量較大
對于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的行為,只有達到數量較大才構成犯罪。因此法條關于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的數量規定應予以明確。但我國對本罪毒品原植物的數量僅有簡單的列舉性規定,包括刑法典對非法種植罌粟規定的起刑點:500株和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準有關問題的解釋》中對非法種植大麻起刑點的規定:5000株。至于其他毒品原植物,則僅僅用了“數量較大”予以籠統概括。雖然我國目前普遍種植的毒品原植物為罌粟和大麻,但也不能排除出現非法種植其他毒品原植物的可能性。如果實踐中遇到這種情況將會導致無法可依的尷尬。
在數量規定上還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對于既種植罌粟或者大麻,又種植其他毒品原植物,而種植罌粟或大麻又未達到500株或者5 000株的如何處理。并沒有明確的計算標準。
當然,法律明確規定500株罌粟、5 000株大麻為本罪的起刑點,是考慮到500株罌粟和5 000株大麻所含有的麻醉成分及其所加工、提煉出的一定數量的毒品所帶來的社會危害性。因此,對于其他毒品原植物的數量較大,也可根據其含有與500株罌粟或5 000株大麻所含相等的麻醉成分來確定其起刑點。對于同時種植多種毒品原植物的,也可以采用這種方式來解決。但是,500株罌粟和5 000株大麻到底含有多少麻醉成分,能夠加工、提煉多少克毒品,其他毒品原植物一株又含有多少麻醉成分,也應由國家進行明確的規定。否則,同樣缺乏統一適用的標準。
二、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經公安機關處理后又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的行為
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的客觀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第二種行為為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經公安機關處理后又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的行為。這一行為的重點在于“經公安機關處理”。
何為經公安機關處理,理論界也有多種看法。有的學者認為,是指經公安機關發現強制鏟除或者予以行政處罰后,仍不思悔改,又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即使種植數量不大,也應以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定罪處罰[9]。有的學者認為,是指經公安機關批評教育或治安處罰,行為人自行鏟除或被強制鏟除后,仍不思悔改,又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的,不論前后種植的是哪種毒品原植物及數量是否較大,都是犯罪行為。有的學者則認為是指經公安機關行政處罰而不思悔改,再次重犯,不受數量限制[3]。有的學者則認為是指治安處罰、強制鏟除等經過司法機關處理[8]。又有的學者認為是指治安處罰、強制鏟除,再次種植數量不受限也不累計[10]。又有的學者認為是指治安處罰、罰款、強制鏟除毒品原植物,不受數量的限制[11]。還有學者認為是指行政處罰、罰款,不受數量的限制[12]。
從以上的界定可以看出,爭論的焦點在于公安機關的處理到底包括了哪些處理。筆者認為,公安機關的處理應該是公安機關作為行政機關而做出的處理,包括行政處罰,即行政拘留和行政罰款,以及相當于行政處罰的強制鏟除,而不應包括公安機關作為刑罰執行機關而做的處理。因為公安機關作為刑罰執行機關進行處理,其決定并不在于公安機關,將其放在這里,不符合立法本意,其性質也不等同于公安機關做出的處理。而前次種植行為如果受到刑罰處罰,不管是否由公安機關執行,后次行為都應當單獨處理,未達到法定數量或情節的不入罪,達到的以新犯罪論,構成累犯的,以累犯論。如果將前次受到刑事處罰的行為也納入此處所講的經公安機關處理,又結合后次種植行為進行處罰,顯然違反了一事不再罰的原則。由此,經公安機關的處理,僅僅只是公安機關作為行政機關的處理,而不能任意擴大為司法機關的處理。當然,由公安機關做出決定,而由其他機關執行也應視為公安機關的處理。
對于本行為構罪是否有數量要求以及前后兩次行為是否進行累計這一問題,學者基本上達成了共識。本行為構成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沒有數量要求應該說是本罪的應有之義。將再次種植的行為設立為罪,重在強調行為人主觀上的惡性,怙惡不悛、屢教不改的人身危險性。若再規定數量要求就與立法本意相矛盾了。但在具體適用時,應考慮刑法第13條的規定,予以酌情處理。至于前后兩次行為是否進行累計,答案也是顯然的。前次行為既然已受處罰,行為人就已經為自己的行為承擔了責任。如果后又進行累計,也是違背一事不再罰原則的。
還有的學者提到了前后兩次行為的時間限制問題。認為前后兩次種植行為之間應有五年的時間間隔[6]。筆者認為并無充分的理由。因為只要行為人在受到公安機關處理后又進行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的行為,其主觀惡性就已顯露無遺,而不存在時間間隔的問題。
三、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抗拒鏟除的行為
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是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客觀方面的第三種表現。此行為實質上包含了兩個前后相續的行為,即先非法種植,而后又抗拒鏟除的行為。而且先種植的數量未達到“數量較大”的要求,否則,先前的種植行為就可以單獨構成本罪,而不需要后面的抗拒鏟除的行為。
這一行為認定的關鍵在于對“抗拒鏟除”的界定。對此,理論界也頗多爭議。有的學者認為,抗拒鏟除即在公安機關或毒品原植物種植的主管部門依法強制鏟除時,以暴力、威脅或以其他手段抗拒鏟除[2]。有的學者認為,所謂抗拒鏟除,是指以暴力、威脅的方法拒絕、阻礙公安機關強制鏟除毒品原植物的行為[11]。有的學者認為,所謂抗拒鏟除是指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的行為人,采用暴力、暴力相威脅,或者其他強制手段足以妨礙主管機關鏟除毒品的行為[11]。有的學者認為,抗拒鏟除應理解為正在對公安機關的強制鏟除而產生的[4]。還有學者則提出,抗拒包括了質和量兩個方面。質是指針對執行強制鏟除人員的阻撓行為,量則指足以阻撓的手段。而鏟除是指公安機關或者其他禁毒管理機關在鏟除,抗拒就發生在公安機關或者其他禁毒管理機關進行強制鏟除之時[6]。從以上對“抗拒鏟除”的界定可以看出,爭議的焦點主要在于,什么是抗拒,抗拒行為發生的時空范圍,是誰在鏟除以及抗拒是否受種植數量的限制。
筆者基本贊同后一種觀點。立法將此行為設立成罪的目的主要是針對行為人知錯不改的惡劣態度和主觀惡性,從而保證國家禁毒措施(在這里主要是指鏟除措施)能夠順利進行。因此,此處的抗拒行為應是指使鏟除措施無法順利進行的行為,而不論此行為是否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也不論是作為或是不作為。當然,在實踐中,抗拒主要表現為作為,尤其是表現為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為內容的作為。而鏟除不僅是公安機關在實施,其他禁毒管理機關也可實施,因此抗拒所針對的對象是任何實施抗拒鏟除的機關和人員。但筆者認為,抗拒行為發生的時空范圍不能僅僅局限于依法執行強制鏟除措施之時。因為在鏟除的其他階段,行為人也可實施阻礙鏟除順利進行的行為。只要這種行為已經使國家機關及其人員的鏟除工作無法順利進行,就應以抗拒鏟除處理,而不論其行為是否發生在鏟除的當時和現場。當然,這里的鏟除應當指強制鏟除或強令鏟除。否則,就不會發生具有對抗性質的抗拒行為了。
這里還存在一個需注意的問題,就是抗拒鏟除構成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與妨害公務罪和故意傷害罪的關系。由于抗拒鏟除的行為本身就是妨害公務的行為,而且抗拒行為在現實生活中又多表現為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這極可能造成工作人員的傷害和死亡。因而在此情況下,此三罪關系密切,極易發生競合和并罰的問題。因此,對于抗拒鏟除的定性也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果抗拒之行為人只是抗拒,本身未參與先前的種植行為,則不能定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而只能以妨害公務罪定罪處罰;若行為人已由于非法種植數量較大的毒品原植物或者再次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而構成本罪,抗拒鏟除則成為一種額外的行為。應對這種抗拒行為進行單獨處理。如果抗拒鏟除行為情節輕微,達不到構成妨害公務罪的法定要求,則作為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的加重情節進行處理。如果抗拒鏟除的行為已經達到了妨害公務罪的法定要求,則應當進行數罪并罰;如果在抗拒鏟除中傷人、殺人的,則成立想象競合犯,從一重處罰。
參考文獻:
[1]周道鸞,張軍.刑法罪名精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641.
[2]何秉松.刑法教科書[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4:781.
[3]婁云生.刑法新罪名集解[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4:255.
[4]桑紅華.毒品犯罪[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191.
[5]趙秉志,于志剛.毒品犯罪疑難問題司法對策[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299.
[6]于志剛.熱點犯罪法律疑難問題解析與證據調查[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364.
[7]趙秉志.毒品犯罪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1.
[8]王紹濤.試論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的構成與處罰[G]//懲治毒品犯罪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171.
[9]蘇文昭.略論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C].1990年中國法學會年會論文集.
[10]趙常青.中國毒品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113.
[11]劉加琛.新罪通論[M].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217.
[12]鄒淘,邵振翔.《關于禁毒的決定》、《關于懲治走私、制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的犯罪分子的決定》釋義[M].北京:群眾出版社,1991:31.
[12]楊聚章,沈福忠.刑法新增罪名研究[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