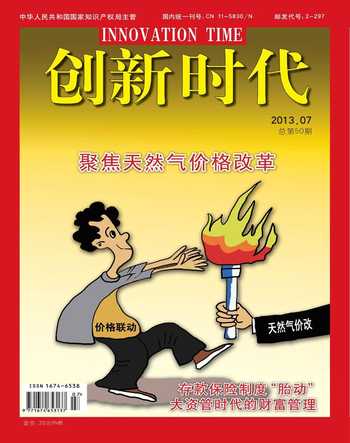從世界銀行歸來以后
江山
林毅夫似乎一直都是媒體追訪的熱點人物。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在經(jīng)濟學界的名望和地位,還因為他特殊的身份:從被蔣經(jīng)國接見的臺軍未來之星,到大陸的“官方智囊”,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經(jīng)歷,足以拍一部傳奇電影。
在今年的“兩會”上,作為全國政協(xié)常委的林毅夫再次表示,中國經(jīng)濟在未來20年仍然有潛力維持8%的增長。當外界質(zhì)疑他是否過于樂觀時,林毅夫表示:“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樂觀派,我是客觀派。但是大家都悲觀,客觀就變成樂觀了。”
舒爾茨的嫡傳弟子
林毅夫1979年游了3個小時渡過一灣海水投奔大陸的故事早已為人所熟知。當年他離臺后,幾經(jīng)輾轉(zhuǎn)來到北京,成為北大經(jīng)濟系的一名碩士研究生。1980年,剛剛獲得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的芝加哥大學榮譽教授舒爾茨訪問北大。林毅夫是當時為數(shù)不多的英語流利的學生,因此被派去做翻譯。舒爾茨對他十分賞識,1982年,在舒爾茨的力薦下,從北大碩士畢業(yè)的林毅夫前往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成為舒爾茨的嫡傳弟子。
林毅夫一直對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有著超乎尋常的關(guān)注。他認為,農(nóng)民問題是中國現(xiàn)代化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因此,他的博士論文也以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改革為題,被導師舒爾茨譽為“新制度經(jīng)濟學的經(jīng)典之作”。完成博士論文后,舒爾茨挽留林毅夫留在美國,他婉言謝絕。在他看來,1987 年的美國社會高度發(fā)達,幾乎沒有新的空間。中國正在從計劃經(jīng)濟轉(zhuǎn)向市場經(jīng)濟,大有可為。于是,他成為了新中國第一位取得外國博士學位后回國工作的社會科學家。
1995年,林毅夫在北京大學創(chuàng)立了中國經(jīng)濟研究中心,這是全國第一個專業(yè)的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研究機構(gòu)。在之后的10余年中,這里成為中國經(jīng)濟學研究的最前沿,不僅為海內(nèi)外培養(yǎng)了大量的經(jīng)濟學人才,也成為了中國政府決策部門重要的智庫之一,林毅夫本人也逐漸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經(jīng)濟學家之一。
強調(diào)發(fā)揮政府作用
在很多人看來,林毅夫是中國學者中與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距離最近的人。他最廣為人知的經(jīng)濟理論是“比較優(yōu)勢”,即充分利用中國勞動力多且相對便宜的優(yōu)勢,發(fā)展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chǎn)業(yè),以此帶來經(jīng)濟的長期快速增長。業(yè)內(nèi)人士認為,林毅夫的理論是對過去以發(fā)展重工業(yè)為代表的趕超戰(zhàn)略的轉(zhuǎn)型,也是他對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戰(zhàn)略的最主要貢獻。
在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方面,林毅夫一直致力于走漸進式的道路,認為這樣更適合中國的國情。尤其是在總結(jié)了東歐等國的經(jīng)驗之后,他反對“休克療法”。他雖是“芝加哥經(jīng)濟學派”的嫡傳弟子,卻沒有選擇該學派的“自由市場”理論,這一點尤其表現(xiàn)在對國企的改革上。按西方的理論,國有企業(yè)改革的核心在于所有制,因此,一些國內(nèi)經(jīng)濟學者推崇私有化改革方案。林毅夫認為,產(chǎn)權(quán)是否私有與企業(yè)自生能力并無必然關(guān)系,私有化不能解決問題,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市場是否透明有效。正因如此,林毅夫一直強調(diào)在市場的基礎(chǔ)上發(fā)揮政府作用,在他看來,對于發(fā)展中國家而言,政府干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出任世行副行長
盡管林毅夫的理論在國內(nèi)外經(jīng)濟學界受到過廣泛爭議,但他依然創(chuàng)下了中國經(jīng)濟學家的很多個“第一”。2007年,他在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發(fā)表演講。馬歇爾講座每年從全世界著名的經(jīng)濟學者中挑選出一位擔任主講人,林毅夫是走上這個世界頂級經(jīng)濟學講壇的第一位中國學者。在演講的結(jié)尾,他說:“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認為發(fā)展中國家的貧窮,并不是命運。”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jīng)濟學家兼主管發(fā)展經(jīng)濟學的資深副行長,成為來自發(fā)展中國家任此職務的第一人。
離開北京前往華盛頓時,林毅夫?qū)幼〉靥岢隽?個要求:15分鐘就能到達辦公室;環(huán)境幽靜,能享受自然;最后是“住得起”。不過,履職后他很快發(fā)現(xiàn),自己留在家中的時間少之又少,經(jīng)常馬不停蹄地從這個國家趕到另一個國家。在奔忙中,林毅夫看到,世界上仍有大約14億人餓著肚子入睡,還有超過六分之一的人口在貧困線上掙扎。因此,如何縮小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間的差距,成為他在世行思考最多的問題。
作為一個來自發(fā)展中國家的經(jīng)濟學家,一開始并沒有多少人認真對待他,因為對于很多信奉自由市場理論的人而言,林毅夫的主張聽上去像來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然而,林毅夫有著自己的堅持。“我從中國的經(jīng)驗中尋找答案。作為首席經(jīng)濟學家,我認為我是一位世界公民。我對所有國家都負有責任。”林毅夫跟蹤研究了中國從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體到世界制造業(yè)強國的超高速轉(zhuǎn)變過程,呼吁各國政府對自己主導下的經(jīng)濟發(fā)展進行更深層次審視。他認為,在經(jīng)濟發(fā)展的每個階段,市場都是實現(xiàn)資源有效配置的基礎(chǔ)機制,但經(jīng)濟發(fā)展需要經(jīng)歷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除了有效的市場機制,政府應該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的過程中發(fā)揮積極的作用。他的想法、做法逐漸得到了人們的認可,并在國際上享有盛譽。
2012年從世行卸任后,林毅夫回到了熟悉的北大校園。對于中國經(jīng)濟的未來,他始終抱有極大期望。在金融危機陰霾未散的大背景下,在中國經(jīng)濟面臨種種嚴峻考驗的重要關(guān)口,林毅夫的堅持或許是給中國經(jīng)濟的一顆定心丸,畢竟,以他個人經(jīng)歷而言,人生每一次重要的時刻,他的選擇都被時間證明是明智而有遠見的。
(作者為財經(jīng)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