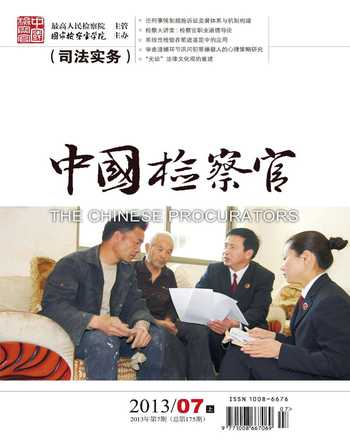對“見危不救”要否入罪的思考
劉仁文
對見危不救要否入罪的討論涉及法律與道德雙重關系。法律與道德的離合,不能一概而論。具體到見危不救要否入罪這個問題上,理論界一直存在爭議,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實際立法也大相徑庭。自20世紀初以來,西方“社會法學”的思潮影響日大,“社會本位”的價值觀在立法中得到體現,法律與道德呈合流之勢。在許多標榜“個人本位”、“權利本位”的西方國家,都有“見危不救罪”的規定。在我國,盡管沒有“見危不救罪”,對一般的無救助義務的人見危不救、見死不救的行為無法用《刑法》處理,只能用道德譴責,但近年來司法實踐中對某些有特定義務的人見死不救進行了定罪判刑處理。
事實上,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需要結合時代的具體情勢而定。法律對道德領域的干預度應依時而定。當道德的力量本身足以保證道德規范得以實施時,法律就應與道德保持必要的距離。但是,當道德的力量不足以使道德規范得到實施,而該規范對社會來說又至關重要時,就有必要采取法律干預的手段,以強化和鞏固該規范,以防止道德規范滑坡。即便要通過法律來加固道德,通過法律糾偏,并不是說就只有用刑法來懲治見危不救、見死不救這一條路徑,可以懲治與激勵雙管齊下,注意發揮法律的激勵作用。因此,我國在討論要否增設“見危不救罪”之前,首先要在激勵和保護見義勇為、樂于助人方面加強立法和執法,要防止見義勇為者“流血又流淚”的局面出現。
鑒于我國《刑法》結構與西方國家存在一個重大差別,即在刑法之外還有治安管理處罰、勞動教養以及其他帶有保安處分的措施,不宜簡單地移植西方國家《刑法》中的“見危不救罪”,而應通過完善《治安管理處罰法》等途徑來解決這一問題。對那些對本人或第三人無任何危險的見危不救行為,可將其納入《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調節范圍。而對那些有特定的救助義務者,則可以進一步明確《刑法》的相關條款,將其納入有關罪名的管轄范圍。
(摘自《法學雜志》,2013年第4期,第26-31頁。)(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1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