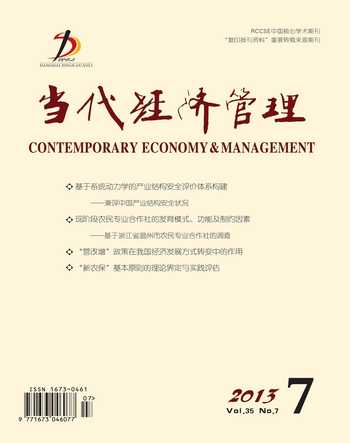中國生態工業園區的生態效益評價研究
王家庭 趙麗
[摘 要]選取全國26個由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轉變而來的生態工業園區,采用因子分析得出影響園區生態效益的經濟因子、能耗因子、水耗因子及管理因子四個主成份,并對其綜合得分進行排序。采用聚類分析將26個園區大體分為4類,生態效益水平依次下降,并對其原因進行分析,進而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詞]生態工業園區;生態效益;因子分析;聚類分析
[中圖分類號]F0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3)07-0041-06
一、引 言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在這種新的宏觀背景下,對我國生態工業園區的生態效益進行評價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以一種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模式增長,引發了自然資源的短缺以及嚴重的環境污染。工業作為一國經濟發展的基礎,必須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生態工業園區是繼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園的第三代工業園,是工業可持續發展模式。
生態工業園區(EIPs)是以清潔生產、循環經濟及工業生態學原理為基礎而建立的一種新型工業園區,它遵從循環經濟的減量(Reduce)、再用(Reuse)、循環(Recycle)3R原則,通過模擬自然系統中的“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的循環途徑,實現物質閉環循環和能量多級利用,最終達到物質、能量的最大利用[1]。
與傳統的工業園相比,生態工業園區在努力實現經濟效益的同時,更多地關注資源的高效利用并盡可能減少污染,使其生態效益最大化。
國外研究方面,Robert A.Frosch和Nichlas E.Gallopoullos(1989)[2]、Jouni Korhonen(2000)[3]、David Gibbs和Paudine Deutz(2007)[4]等,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工業生態系統特征,為生態工業園區的評價奠定了基礎。對于生態工業園區評價這一問題,國內學者也已作了不少研究。其中大部分學者均是以生態工業園區需具備的基本條件及評價目標等原則為基礎,從經濟、管理、環境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元炯亮(2003)[5];黃海風、張宏華、蔡文祥等(2005)[6];李強(2006)[7]。也有一些學者選取的方法及視角較為新穎,如黃鵾、陳森發、周振國等(2004)[8]采用頻度分析法和理論分析法,從園區發展水平、發展能力和發展協調度3個角度,構建了相對完整的生態工業園區指標體系,并指出生態工業園區評價指標體系應該完善信息采集、監測方法。
從總體上看,生態工業園區評價指標體系傾向于從經濟、管理、環境、生態4個方面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構建評價體系。但由于研究尚未步入成熟階段,以往研究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在評價指標的選取上表現出較多的重疊性,不能完全反應出評價的真實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作為主要研究方法,選取影響生態工業園區生態效益的主因子,并由此得到綜合因子得分從而進行排序;此外,通過聚類分析方法將各個園區以生態效益大小進行聚類。
因子分析是指從研究指標相關矩陣內部的依賴關系出發,把一些信息重疊、具有錯綜復雜關系的變量歸結為少數幾個不相關的綜合因子的一種多元統計分析方法。基本思想是:根據相關性大小把變量分組,使得同組內的變量之間相關性較高,但不同組的變量不相關或相關性較低,每組變量代表一個基本結構——即公共因子[9]。各綜合因子F的權重是根據其方差貢獻率大小而確定,方差越大,其所占權重越大;反之,方差越小,其所占權重越小。
因子分析步驟如下:①對數據樣本進行標準化處理;②計算樣本的相關矩陣R;③解特征方程R-λE=0,計算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取累積貢獻度不少于80%的前K個主成分代替原來的m個指標,計算因子載荷矩陣A;④對因子載荷矩陣A進行最大正交旋轉變換;⑤計算第j個公因子的得分Fj,并以其貢獻度為權重,對F1、F2、……、Fk進行加權計算,從而得到綜合因子得分F,并根據綜合因子得分對所評價內容進行排序。
聚類分析是一種將研究對象分為相對同質的群組的統計分析技術多元統計分析方法。聚類分析也叫分類分析或數值分類,它是應用最為廣泛的分類技術。通過聚類分析,可將性質相近的個體歸為一類,將性質差異較大的個體歸為不同類,從而使類內個體具有較高的同質性、類間個體具有較高的異質性。
系統聚類法是聚類分析中最常用最基本的分析方法。聚類分析在對數據變換處理的基礎上,根據表明樣本間關系密切程度的聚類統計量,運用一定的聚類方法進行聚類,如最短距離法,最長距離法,中間距離法、重心法、離差平方和法等,本文采用離差平方和(Ward)法進行聚類。
三、數據來源與變量說明
由于目前我國生態工業園區建設還未步入成熟階段,還未形成完整的生態工業園區年鑒,筆者所用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開發區年鑒2008。
根據以往學者的評價目標和指標體系構建原則,以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出臺的綜合類生態工業園區的考核指標體系為基礎,從經濟和環境兩個系統出發,構建了含經濟發展、循環利用、環境保護和綠色管理4個方面9項具體指標的生態環境效益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以此指導園區實現可持續發展。
從2007年53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中選取26個截至2011年12月通過驗收批準命名或批準建設的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選用其2007年工業增加值、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單位工業增加值新鮮水耗、單位生產總值化學需氧量(COD)排放量、單位生產總值SO2排放量、是否國家循環經濟示范區試點園區、全區是否通過ISO14000認證、期末通過ISO14000認證的規模以上企業數9個指標進行實證分析。
所選數據均直接摘自《中國開發區年鑒2008》,是由原始數據經處理后的數據,代表各項評價分類指標的得分。
具體指標的設置具有以下特征:
指標X1和X2用以衡量園區的宏觀經濟條件,以代表經濟發展的水平。
指標X3用以衡量整個生態工業園區的節能水平。該指標主要考核園區每單位工業增加值消耗能源資源(包括電力、燃氣、燃油、煤炭)的情況。
指標X4和X5用以衡量水資源的使用情況及水污染狀況。
指標X6用以衡量硫排放情況,主要考核大氣污染程度。
指標X7、X8、X9是衡量園區企業清潔生產實現程度、綠色制造推進程度以及園區管理水平的重要參考。該指標主要考核園區企業環境管理水平。
四、實證結果分析
筆者以SPSS軟件作為統計分析工具。在進行因子分析前,采用KMO檢驗和Bartlett球體檢驗來判斷觀測數據是否適合作因子分析。結果表明,變量的KMO值為0.649,Bartlett球體檢驗的卡方值為104.707,其P值為0,因此樣本數據適宜做因子分析。采用主成份分析法提取因子,前4個因子的特征值分別為3.681、2.076、0.909和0.821,其方差貢獻度分別為40.898%、23.063%、10.102%和9.118%,4者的累積貢獻度達到83.181%,信息損失為16.819%。
由表2可以看出:工業增加值(X1)、地方一般預算收入(X2)、是否國家循環經濟示范區試點園區(X7)3個變量在因子F1上的載荷值較高,反映了生態工業園區的外在宏觀經濟條件,我們將F1命名為經濟因子;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X3)、單位生產總值化學需氧量(COD)排放量(X5)、全區是否通過ISO14000認證(X8)3個變量在因子F2上的載荷值較高,反映了生態工業園區的能耗水平,我們將因子F2命名為能耗因子;單位工業增加值新鮮水耗(X4)、單位生產總值SO2排放量(X6)兩個變量在因子F3上的載荷值較高,反映了生態工業園區的水耗水平,我們將因子F3命名為水耗因子;期末通過ISO14000認證的規模以上企業數(X9)在因子F4上的載荷值較高,反映了生態工業園區的綠色管理水平,我們將因子F4命名為管理因子。這4個因子基本概括了生態工業園區生態效益的各方面,可用于科學、有效地評價26個生態工業園區的生態效益。
根據表3,因子F1、F2、F3和F4的得分表達式如下:
F1=0.238X1+0.281X2-0.112X3-0.2X4+0.143X5+0.226X6+0.590X7-0.229X8-0.063X9 (1)
F2=-0.057X1-0.035X2+0.465X3-0.052X4+0.523X5-0.2X6-0.091X7+0.37X8-0.114X9 (2)
F3=0.044X1-0.2X2-0.074X3+0.52X4-0.179X5+0.663X6+0.044X7-0.073X8-0.009X9 (3)
F4=0.226X1+0.12X2+0.004X3+0.285X4-0.402X5-0.258X6-0.318X7+0.287X8+0.629X9 (4)
然后,以主因子的方差貢獻度為權重,計算26個生態工業園區生態效益的因子得分,其計算公式為:F=0.40898F1+0.23063F2+0.10102F3+0.09118F4
(5)
最終得出26個生態工業園生態效益的因子得分及排序見表4。
從表5中的主因子綜合得分可以看出,天津(省略“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下同)、廣州、蘇州工業園區的生態效益居于領先地位,大連、漕河涇、煙臺緊隨其后,閔行、昆山、上海金橋略遜一籌,南京、武漢、南昌的生態效益處于中游,北京、長沙、杭州、福州、西安、合肥、南通的生態效益處于中下游水平,青島、溫州生態效益相對較弱,昆明、鄭州、蕭山、寧波、貴陽在26個生態工業園區中生態效益最差。
從經濟因子F1的得分來看:排名前5名的是天津、蘇州工業園區、上海漕河涇、廣州、煙臺,它們主要得益于所在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排名后5名的是南京、杭州、福州、蕭山、溫州,它們在經濟因子方面與其他城市相比相對較弱。
從能耗因子F2的得分來看:排名前5位的是南京、上海閔行、武漢、長沙、南昌,這反映出這5個生態工業園區的能耗較低,資源利用率高;排名后5位的是昆明、貴陽、鄭州、蕭山、寧波,這些生態工業園區能源耗費多,單位生產總值化學需氧量較高,資源利用水平較為低下。
從水耗因子F3的得分來看:排名前5位的是溫州、南京、天津、寧波、大連,這些生態工業園區的硫排放較低,環境保護較好;排名后5位的是蘇州工業園、上海漕涇河、煙臺、貴陽、青島,可能是由于工業的發展,它們的水耗較多,硫排放量較大,環境污染較為嚴重。
從管理因子F4的得分來看:排名前5位的是天津、廣州、蘇州工業園、大連、上海漕涇河,期末通過ISO14000認證的規模以上的企業數較多,綠色管理水平較強;排名后5位的是昆明、鄭州、蕭山、寧波、貴陽,這些生態工業園區的綠色管理水平嚴重不足。
通過因子分析,我們得到了26個生態工業園區的生態效益水平及排名。下面,筆者通過聚類分析揭示包含在因子中的、反映26個園區生態效益的個性與共性特征的信息。
我們以通過因子分析得到的4個因子(即經濟因子、能耗因子、水耗因子、管理因子)為變量,利用SPSS統計軟件,針對26個生態工業園區的生態效益水平,對26個生態工業園區進行聚類,采用系統聚類法分析。通過離差平方和法計算類與類之間的距離,使得同類生態工業園區間的離差平方和較小,而類與類之間離差平方和較大。
結果顯示,聚類結果和綜合因子得分排序結果的基本趨勢是一致的。然而,聚類分析是以樣本間的距離(離差平方和)作為分析依據的,將“距離”較近的對象劃為一類,而非通過分別計算各樣本的得分來做比較,這樣劃為同一類的對象具有更多的相似之處,因此聚類結果更為科學。
通過系統聚類法得到的分層結果見表5,由A類到D類呈現出生態效益依次減弱的趨勢。
為得到每類生態工業園區的類特征,取整體(26個園區)及各類(A類、B類、C類、D類)生態工業園區的因子均值,得到結果見表6。由表6可知,A類生態工業園區生態效益水平高主要是由其經濟因子決定的,這主要依托了其宏觀經濟條件的發展狀況。B類生態工業園區生態效益較高主要是由其管理因子決定的,即園區比較注重對于環境的綠色管理,因此園區的整體生態效益較高。C類生態工業園區在4類因子方面均沒有較為突出的優勢,整體生態效益水平一般。D類生態工業園區生態效益較差,我們從表6可以看出其水耗因子得分非常低,即在水資源利用方面存在較大的缺陷,而在其他方面又不具備明顯優勢,因此導致園區的整體生態效益水平很低。
五、結論及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結論:
①通過主成份分析法,提取出經濟因子、能耗因子、水耗因子以及管理因子,這4個因子基本概括了生態工業園區生態效益的各方面,可用于科學、有效地評價生態工業園區的生態效益。②通過聚類分析法,將26個生態工業園區大體分為4類,以蘇州工業園區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廣州開發區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為代表的A類園區生態效益總體最高;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寧波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蕭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生態效益較高;包括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南通經濟技術開發區、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在內的15個園區整體生態效益水平一般;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貴陽經濟技術開發區生態效益最差。③究其原因,A類園區主要依托了其宏觀經濟條件的發展;B類園區由于較為注重對于環境的綠色管理,其生態效益水平較高;C類園區在各方面均沒有較為突出的優勢,其生態效益水平一般;D類園區在水資源利用方面存在較大的缺陷,且在其他方面也并無優勢可言,故生態效益水平最低。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結合黨的“十八大”報告精神,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穩步實現生態工業建設和經濟建設的融合
切實做到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為生態工業園區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使其在宏觀經濟背景的依托下實現較大的生態效益。充分發揮政府資金導向作用,采取財政補貼、稅收優惠、貸款貼息等政策,吸引各類資金投資于生態工業,建立起多元化投資機制,將生態工業建設與經濟建設相融合,實現二者的共同提升。
2.轉變資源利用方式,構建生態文明社會
在工業生態學的指導下,使園區內形成一個模擬自然生態系統的封閉體系,令一個企業產生的廢料成為另一企業的原料,有步驟地回收和利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廢物和副產品,力圖實現水、能源等的最大效用。同時開展清潔生產工作,從源頭上控制污染,避免使用有毒有害原料及降低廢物排放量與毒性。
3.加強制度建設,嚴格落實對于園區的環境管理
按照環境管理標準的要求嚴格組織園區內的企業進行生產,對于污染較重且無法得到有效治理的項目,堅決不能批準其進入園區。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鼓勵企業開辟專門的實驗研究區域,在實踐中研究針對園區環境管理的新技術,并進一步加大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聯系,爭取引進更多研發中心入園。
4.樹立生態工業理念,鼓勵更多生態工業園區的建設
加強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增強全民節約、環保及生態意識,全方位貫徹生態工業理念,調動各方積極進行生態工業園區的建設,營造一個健康、文明的工業氛圍。
[參考文獻]
[1] Ewa Liwarska-Bizukojc, Marcin Bizukojc,Andrzej Marcinkowski, Andrzej Doniec.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an eco-industrial park based upon ecological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9(17):732-741.
[2] Robert A.Frosch,Nicholas E.Gallopoulos. Strategies for manufacturing[J].Scientific American,1989,261(3):144-152.
[3] JouniKorhonen. Four ecosystem principles for an industrial ecosystem[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1(3):253-259.
[4] David Gibbs, Pauline Deutz. Reflections on implementing industrial ecology through eco- industrial parks development[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7(15):1683-1695.
[5] 元炯亮.生態工業園區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循環經濟,2003(3):38-40.
[6] 黃海風,張宏華,蔡文祥,王春能.基于灰色聚類法的生態工業園區評價[J].浙江工業大學學報,2005(8):379-384.
[7] 李強,湯俊芳,鐘書華.生態工業園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J].科技與管理,2006(4):67-70.
[8] 黃鵾,陳森發,周振國,元霞.生態工業園區綜合評價研究[J].科研管理,2004(11):92-95.
[9] 高惠璇.應用多元統計分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An Evaluation of the Eco-industrial Parks Ecological Benefit in China
Wang Jiating ,Zhao Li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hoose twenty-six eco-industrial parks (EIPs) which were transformed from former national-leve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and use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o acquire four factors, including economic factor, energy consumption factor, water consumption factor and management factor, which influence the ecological benefit of the EIPs. Then we rank the comprehensive scores of the factors. Next we used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to sort the 26 EIPs to 4 classes whose ecological benefit level declines in turn and explored the reason. Finally we put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eco-industrial parks (EIPs);ecological benefit;factor analysis;cluster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