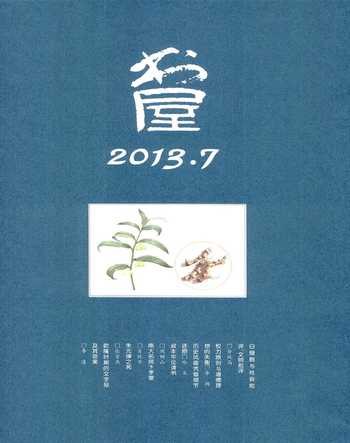也談“四庫全書”
李力
閻崇年在《百家講壇》講“清十二帝疑案”,總結了乾隆的八大歷史貢獻,將其主持編修《四庫全書》排在第一位。“四庫”是經、史、子、集的統稱,這部四千多名文人學者參與,歷時二十年才完成的浩大工程,其實有數目驚人的書籍遭到了焚毀、刪削、篡改、錯訛的厄運,而這一切都是蓄意為之。
一、焚毀。《四庫全書》收錄全文的圖書一共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種,成書七萬九千卷,近七點七億字。編修中明令禁焚的書籍就有三千多種,幾乎與全文收入的總數相當,這還不算因當時明令上繳違禁書籍在民間造成的恐怖氛圍,百姓偷偷焚毀的書籍,合計起來被毀掉的書籍恐怕不下萬部,這實在是一場文化大浩劫。
二、刪削。只舉幾例,據黃裳先生考證:乾隆四十一年詔令:書籍內如有只須刪改的字句,就不必因此而廢掉全書;乾隆四十四年,禁網已注意到地方志;乾隆四十五年,注意力伸到野史詩、演戲曲本、小說等俗文學領域。
三、篡改。魯迅先生曾說過:“清人篡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病后雜談之余》)。乾隆五十年,改《明末紀事本末》中“吳三桂擊走李自成”為“清軍擊走李自成”。不但與清代統治者利益密切相關的明人作品遭到大力剿滅,而且殃及兩宋。如岳飛的《滿江紅》名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被改為“壯志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因為“胡虜”、“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張孝祥的名作《六州歌頭?長淮望斷》是描寫北方被金人占領的孔子家鄉:“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這“膻腥”讓人聯想到胡人,當然犯忌,被改作“亦凋零”。陳亮的《水調歌頭?不見南師久》:“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一個半個恥臣戎”改作了“一個半個挽雕弓”。最荒唐可笑的是辛棄疾的《永遇樂?千古江山》:“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開國皇帝劉裕的小名,本來與犯忌的“胡”“戎”“夷”“虜”等并不相關,可是在專制淫威下,奴才們“覺悟太高”,再次證明了“狗總是跑在最前面的”。
四、錯訛。戊戍變法時支持新法的陜西進士李岳瑞,在其筆記《悔逸齋筆乘》中提到乾隆御制、四庫館臣校訂的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曩讀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惟《史》、《漢》、《國志》校勘無愧精審,《晉書》以次,則訛字不可枚舉。”是四庫館臣的疏忽嗎?不是。這是四庫館臣、內府官員、太監共同表演的取悅皇帝的“啞劇”——故意留下一些容易看出的錯誤,等待喜歡校書的乾隆看到后標出,再對館臣的“不學”降旨訓斥,從而“龍心大悅”,覺得自己的學問也在“皆海內一流,一時博雅之彥”的四庫館臣之上。“然上雖喜校書,不過偶爾批閱,初非逐字讎校,且久而益厭。每樣本進呈,并不開視,輒以朱筆大書校過無誤,照本發印。司事者雖明知其訛誤,亦不敢擅行改刊矣。”
從上述可以看出,毀、刪、改,包括留下的大量錯訛,都是蓄意而為。深究緣由,就不得不剖析乾隆編修《四庫全書》的真實意圖了。
眾所周知,所謂的“康雍乾盛世”本是中國歷史上“文字獄”最為酷烈的時期,而在乾隆編纂《四庫全書》的同時,更是“于斯為盛”。有人做過統計:整個乾隆年間六十二年,一共發動了一百多起文字獄,而在編纂《四庫全書》的二十年間就有四十八起,大約占到了一半!
乾隆老兒慣于“軟硬兩手”抓思想文化專制,編纂《四庫全書》是“軟”的一手,起正面誘導作用,藉此蒙蔽天下人的視線;羅織文字獄,動輒讓讀書人人頭搬家,則是“硬”的一手。“軟”的一手正是為“硬”的一手收證據、作準備、找借口。“兩手”可謂相輔相成、珠聯璧合。可見乾隆比“焚書坑儒”的秦始皇“聰明”,編書不過是手段,禁毀才是目的,他是“寓禁于編”。
明末大思想家黃宗羲在《原君》中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話如同流星,在夜空中劃出耀眼的光輝。為害天下,當然就會殃及書籍、禍及文化。編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便是一場浩劫文化、鉗制思想、馴養順民的悲慘歷史。魯迅說《四庫全書》編好后,不僅藏在內廷,而且“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里面,也曾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病后雜談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