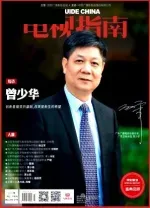言情小說的進化史
嚴格來說,言情小說其實是中國舊體小說的一種。然而,將言情小說發揚光大的推手卻是來自寶島臺灣的瓊瑤阿姨。若從純文學的角度而言,任何一個榜單都看不到她,可若從文化輻射和對女性的影響力而言,瓊瑤絕對是當之無愧的開山鼻祖。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還籠罩在計劃經濟的氛圍里,談個戀愛都要向上級打報告寫申請,瓊瑤小說的出現著實讓人們見識了“西洋鏡”,同時也讓剛剛走出文革的內地青年們知道了戀愛不光是只有互贈塑料皮筆記本、寫上“互相幫助共同進步”這樣一種形式,它還有“互相折磨”“共同折騰”等多種更有趣更變態的手段和方法。
在那個精神和物質都雙重貧瘠的年代,人都非常饑餓,餓書中華美的物質,餓書中轟轟烈烈抵死纏綿的愛情。就單拿名字來說,在60后和70后一片“小紅”“國慶”“杜鵑”“建國”之外,“婉君”“楚天”“濃若梅”“左雨農”“汪綠萍”“楚濂”“李夢竹”等如詩如畫的人名帶給人們無限美好的遐想。就連“瓊瑤”的名字也是取自《詩經》,而在我們這兒——《詩經》早在一片“打倒孔家店”和“批四舊”的運動中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一腳。
瓊瑤小說都有一定的模式,事實上任何言情小說都有既定的模式:他愛我我也愛他,但是我們倆有一個不自由;他不愛我我愛他,但是我們身體卻自作主張;他不愛我我不愛他,但是我愛上的卻不能帶回家……
其實,兩個人的愛意傳達,有時需要違背兩點之間直線最短的原則。越是迂回婉轉,越是礙著人多,便越是來勁得有趣。這有點像敵后作戰,在掃射中瞅空拋個媚眼,可比那大眼珠子直瞪瞪瞅著要抓心多了。戀愛中的大部分美好,來自于似與不似之間,金庸說戀愛的妙處,無非在“若即若離,患得患失”幾個字。篤定的愛,能給人勇氣,卻未必能讓人暈眩,拿得穩的感情,不如那有壓力的關系來得過癮。
瓊瑤筆下的所有人物皆是情感能量極大的人——不投入則已,一旦投入,必有驚天動地的波瀾。她特爾善于將人拖到一場醒不過來的夢里,舉手抬腳都覺得無力,還不如就依了。這種重口味,大劑量的言情小說特別適合饑饉年代的人們——苦太久的人是不害怕糖太甜的;因為時代的關系,喜歡瓊瑤的讀者不僅意味著人到中年,還意味著不可能有如愿以償的愛情,她們的花期太短暫了……閱讀瓊瑤,讓她們的心成了一塊不容易結疤的小小創口,這有利于自憐自惜,有利于制造一些小小的悲愴感,讓憂傷在小屋中漫起,一朵受傷的云在棱角分明的鏡子前緩緩升騰。
瓊瑤走紅之后,亦有許多追隨者,席絹、嚴沁、岑凱倫等,但基本都在復制瓊瑤的路線,無非是以最癡纏的愛情來試圖打劫觀眾最脆弱的情感。到了市場經濟時期,人們忽然意識到,那些言情小說的主人公為何從來不工作就能錦衣玉食?這顯然是不合邏輯的。在這一時期,“下海”成了熱門詞匯,亦有夸大其詞的“十億國人,九億商”的說法。于是乎,梁鳳儀和亦舒順勢而為,區別于瓊瑤的純言情,梁鳳儀的商戰財經小說和亦舒充滿警示格言體的小說成功占據言情市場的半壁江山。喜歡梁鳳儀和亦舒的讀者年輕稍微偏大,她們在更年輕的時候可能也是瓊瑤的讀者,但當她們終于可以名正言順談戀愛的時候,卻突然發現瓊瑤阿姨是騙人的;是現實和閱歷告訴她們,愛情沒那么脫俗,而嫁人更要擦亮眼睛。但是這類財經、勵志的言情小說也有庸俗的一面,比如男主角的皮相、財富、身份皆鶴立雞群,相當于藍籌股;女主角則在富貴鄉里保持著純真,以美為職業,以顛倒眾生為己任,身邊的男人無論老少,都像向日葵一樣伸長了脖子轉向她。說白了,梁亦的讀者雖然過了愛做夢的年紀,但始終對愛抱有僥幸的幻想。她們筆下的愛情都很緩慢,很柏拉圖——這不是要號召大家都去追求浸著黃連汁的劇情,只是,假想一下,如果在酒廊里兩句調情一杯薄酒劇能找地方寬衣解帶,估計發生愛情的幾率也會急劇降低吧?
或許正是出于交往的容易,到了互聯網時代,以安妮寶貝為首的言情小說,開始主打“不相信愛情”的論調。其實在此之前,“美女作家”衛慧和棉棉——甚至更早之前的林白和陳染——也曾因書中大量的性描寫和私體驗而名噪一時,雖然她們挨了不少罵,但她們書中對于自我觀念和生活態度的張揚讓她們顯得非常酷。以往的言情小說總是在突圍和沖破,總想打碎什么或叛逆什么,而E時代的女性對規則根本視而不見,這其實是一種很大的蔑視姿態。反過來對照瓊瑤和梁鳳儀,或許壓抑的愛情更能產生刺激,因為有時候人們相愛的程度來源于別人破壞和不贊同的程度。可是當外界的阻力忽然消失,戀人們或許才會真正去追問自己的內心。所以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安妮寶貝才能走紅。
安妮筆下過于細膩和精致的內心描摹,以及絕望的愛情和無望的男人,被批評為“毒藥文字”,可是安妮的擁躉卻能從“毒藥”里提煉出百種意蘊和千種暗示,自己也據此跌宕起伏,忽入地獄,忽登天堂,書里一聲輕笑,這邊心事已過萬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