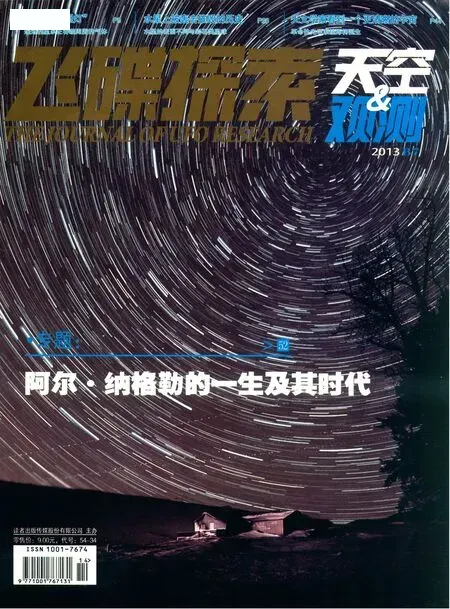中微子
李沃龍
僅有少數的物理學家能有幸為世界引入一種新的基本粒子。沃爾夫岡·泡利在1930年想到中微子這個概念時,內心的疑慮使他對此粒子有所保留。泡利稍后告訴同事:“我做了件可怕的事,我假設有一種無法被偵測到的粒子存在。”
中微子確實難以捉摸,它如鬼魅般的本質,使它幾乎不受阻礙地穿越物質,包括那些物理學家在粒子探測器中所使用的材料。事實上,大部分中微子可利落地穿透地球而不碰觸到其他粒子。不過,泡利的憂慮稍微夸張了些:中微子其實是可以被偵測到的,雖然需要花費極大的力氣并設計精巧的實驗才能成功。
中微子是最奇特的一種基本粒子:它們不能用來建構原子,也不會與其他物質作用;它們是唯一不帶電荷的物質粒子;它們非常輕,質量不到電子這種次輕物質質量的百萬分之一;此外,中微子還是所有粒子中最善變的,它們可在三種形態間變換身份。
80余年來,這些微小粒子一直令物理學家感到驚訝。直至今日,一些關于中微子的根本問題仍懸而未決:中微子的形態真的只有三種,抑或更多?為何所有的中微子都如此輕?中微子的反物質是否就是它自己?為什么中微子可以如此輕易地變換身份?
針對這些問題所設計的新實驗,正在世界各地的粒子對撞機、核反應器,甚至廢棄的礦坑里如火如茶地進行著。所獲得的答案,應該能對大自然的內在運作方式提供基本線索。
中微子的奇異特性可作為一盞明燈,指引物理學家邁向大統一理論(該理論除了重力之外,所有的粒子與作用力,都可用條理一貫的數學架構描述)。標準模型是目前關于粒子與作用力的最佳理論,但它無法包括中微子的所有復雜性質,因而亟須擴展論述。
在標準模型上擴充中微子的部分,最常用的方式是引入一種被稱為右旋中微子的新粒子。正如電荷規范粒子的電性多寡一樣,自旋決定了一個粒子能感受到弱核力,即造成放射性衰變的作用力;只有左旋粒子才能感受到弱核力。因此,這些假設存在的右旋中微子,必然比那些已經被實驗證實的左旋中微子更難以捉摸。所有的中微子都被歸類為輕子,這代表它們并不會感受到強核力。由于不帶電荷,中微子也不會受電磁力的影響。如此一來,三種已知形態的中微子能感受到的只剩下重力與弱核力,但右旋中微子甚至不受弱核力的影響。
如果右旋中微子真的存在,它將合理解釋另一項中微子之謎:為何電子中微子、緲子中微子與T中微子這三種左旋中微子的質量如此微小?
大多數基本粒子通過與無所不在的希格斯場作用,來獲得它們的質量。2012年,在瑞士日內瓦附近歐洲核子研究組織LHC工作的物理學家宣布,他們已辨識出一種新粒子,其性質符合長期尋找的希格斯玻色子,希格斯便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此玻色子是希格斯場所對應的粒子,就像光子是電磁場所對應的粒子一樣。在此過程中,希格斯粒子會帶走與其作用粒子的弱核力版本的電荷。由于右旋中微子缺乏這種電荷,它們的質量并不取決于希格斯場。取而代之的是,這些質量或許源自一種發生于大統一時全然不同的極高能機制,造就右旋中微子成為超重粒子。
量子效應可聯結右旋中微子與其左旋兄弟,使得其中一方將其巨大的質量“傳染”(infect)給其他粒子。不過,這種傳染力非常微弱:例如右旋中微子若得了肺炎,左旋中微子只會有輕微的咳嗽,這意味左旋粒子的質量將極微小。這一關系被稱為“蹺蹺板機制”,就像是右旋中微子與左旋中微子在蹺蹺板的兩端,而質量較大的粒子會將質量較小的粒子抬起。
中微子質量的另一項解釋來自于超對稱,那是標準模型之外的新理論選項。在超對稱的假設下,每個標準模型里的粒子都擁有一個尚未被發現的伴子。這些被稱為超伴子的質量必定非常巨大,以至于到今天仍無法偵測到,而且它們至少會立即將基本粒子的數目加倍。假如超對稱粒子真的存在,LHC或許能產生它們,并測量它們的性質。
超對稱理論最吸引人的特色之一,是有一種稱為中性伴子的超對稱粒子,很適合用來解釋暗物質,這些物質構成星系與星系團的大部分質量,能夠施展重力但卻不發光,也不會以其他明顯的方式將自己顯露出來。不過,只有當中性伴子能長期穩定存在,而不是迅速衰變為其他粒子時,才能夠作為暗物質。
因此,短命的中性伴子將會把研究人員送回黑板前重新構思,但可能對物理學家不無益處。中性伴子的穩定性取決于一種被稱為R-宇稱的假設性質,它可防止超伴子衰變成任何普通的標準模型粒子。但是,如果R-宇稱不存在,中性伴子將變得不穩定,而其衰變有一部分取決于中性伴子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