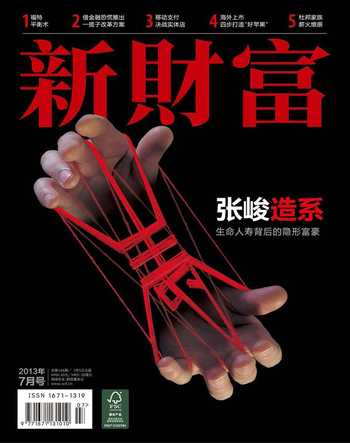借金融恐慌推出一攬子改革方案
李稻葵


中國近期金融恐慌的根源,是實體經濟內非中介融資受阻,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冰火兩重天。針對恐慌,放水救市不可行,而按兵不動則連帶傷亡巨大,唯一合理的選擇是以此為契機,推進討論已久的一攬子改革方案。
中國出現了金融恐慌。2013年6月24日,上證指數下跌5%以上,其背景是,商業銀行紛紛遭遇資金短缺,導致市場彌漫緊張情緒。在此之前的幾天內,銀行隔夜同業拆借利率高達13.44%,創歷史新高,社會上也流傳著個別銀行出現短期借貸違約的言論。一時間,社會關注點聚焦于央行。救市還是不救市,成為央行決策和大眾關注的焦點。
金融恐慌的深層原因是
實體經濟非中介融資(DNI)受阻
金融恐慌的根本原因,是當前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走入了極端的困境,實體經濟出現冰火兩重天的罕見格局。
冰指的是民營經濟體找不到投資方向,投資無門,轉而把大量的現金投資于金融體系和理財產品,導致了金融體系信用盲目擴張。而另一方面,十八大前后新上任的地方官員卻干勁沖天,對項目融資表現了火一般的熱情,他們在積極謀劃新一輪的經濟增長。而地方政府所能直接影響的經濟活動,絕大部分是與國有企業緊密相關的一大批投資項目,它們所依賴的融資渠道主要是正規的金融中介機構,包括銀行、信托、債券市場等。
然而不要忘記,在正常情況下,中國經濟的投資主體是民營經濟,占GDP高達60%以上的固定資產投資,其70%以上的融資來源是企業留利所形成的直接投資,即筆者最近的研究中所稱的國內非中介融資(DNI,Domestic Non-Intermediated Investments)。這種非中介融資主要來自于民營經濟。
于是乎,在當前冰火兩重天的境地下,包括銀行貸款在內的社會融資總額迅速上漲,2013年一季度,同比增長接近60%。但畢竟,這種正規渠道的融資并不是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主體,袖手旁觀的民營經濟體并沒有直接參與固定資產投資。這就導致了固定資產投資本身并沒有快速上漲。DNI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正常年份的70%下降到2013年1-5月的60%出頭。而由于固定資產投資是GDP增長的最大拉動力量,所以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那就是,社會融資總額和增長幅度不斷創下新紀錄,而宏觀經濟增長速度卻持續下滑。這對矛盾的最后結果就是銀行打光了子彈,資金告急。更火上澆油的是,因為宏觀經濟在減速,大量企業利潤在下降,開工率持續下降,產能利用率下降,這又反過來使得相關企業難以償還以前的貸款。這種情況下,銀行等其他金融中介機構比實體經濟還要著急,它們必須要用新貸款覆蓋已經到期、不能償還的舊貸款,掩蓋幾年前的不良貸款的漏洞。這就是當前金融恐慌的深層次原因。這種金融恐慌很自然地對已經十分脆弱的股市投資者帶來了進一步的崩潰性的沖擊,最終使得股票價格一瀉千里。
分析清楚了當前金融恐慌的原因,下面的問題是應該怎么辦。
放水救市不可行
第一種應對策略就是央行放水救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或者是降息、降準給銀行注入流動性。
這種策略當然是立竿見影,但是不能解決上述問題之根本,只能短期內緩解金融機構資金不足的壓力和金融市場的恐慌,經濟增長仍無法保障。金融機構拿了新錢也只能繼續填補不良貸款的漏洞,前述矛盾的解決則會繼續拖延。由于不治本,新的一輪金融恐慌遲早會到來,而且會以更大的力度爆發。所以說,開閥放水救市只能是飲鴆止渴。
按兵不動可行,但連帶傷亡巨大
目前看來,政策界與學術界壓倒性的意見是按兵不動,目的是逼著銀行尋找新的思路,同時也讓產能過剩進一步暴露,促進經濟結構調整。
但是,這種按兵不動的策略很可能連帶傷亡巨大,乃至為中國經濟與社會所不堪承受。按兵不動會導致金融市場的信心持續下滑,恐慌還將繼續,資金短缺的情況還將延續,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將進一步下降,增長速度也會下降。這種做法堅持下去,最終當然會逼迫銀行進行改革,進行重組,但必須看到,其代價是非常大的。
為什么這么講?因為當銀行資金緊張的時候,一定會出現以新錢補舊賬的局面,其后果一定是那些最需要投資、最有投資潛力的項目得不到融資,而銀行卻會利用寶貴的資金去填補那些事實上已經成為呆賬、壞賬的投資項目,所以我們會看到,社會上的好企業、有潛力的企業和項目變成銀行過去幾年不良貸款的犧牲品,也就是說,會發生大量的好企業為銀行幾年前的不良貸款埋單的局面。
更不用說,因為宏觀經濟增速的下降,有大量的企業停止招聘甚至于解雇工人,最終的受害者會變成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以及急需尋找就業機會的新畢業的大學生。無論對于社會的穩定和整個宏觀經濟的平穩增長,還是從公平的意義上講,這一結果都是非常不合理的。因此筆者認為,不應該采取簡單的緊縮方針,這一方針的連帶代價太大。
唯一合理選擇:
迅速出臺一系列改革措施
迅速出臺一攬子改革措施,是解決當前宏觀經濟增速放緩以及金融恐慌唯一正確的應對方式。這一攬子的改革重組方針應該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條是迅速推出一系列的改革,大規模放開對民營投資的限制,鼓勵民營投資者直接進入一系列重大經濟活動領域。這個措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穩增長,就是要啟動國內的非中介投資,讓那些擁有大量資金的民間投資者直接投資到一些實體經濟的項目中去。
中國經濟,非常客觀地講,有巨大發展的空間。概括說來,中國經濟目前最缺的是一大批準公共產品,包括城市基礎設施與城際交通。而這些項目作為準公共品,完全可以通過改革為它們的投資者帶來直接的回報。舉例說來,最近筆者到山西曾經的貧困地區呂梁市調研,結果發現呂梁是一個資源大市,可是呂梁與太原之間的高速公路仍然十分擁擠,鐵路也運力不足,這直接影響了當地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這種高速公路和鐵路完全可以采取市場化—誰投資誰受益,誰使用誰付費的方式來引導民間投資者介入。事實上,呂梁地區并不缺民間投資者,他們有大量資金找不到投資方向。
再比如說,在城市化過程中,完全可以把一部分的街道,包括它地下的管網建設部分承包給一些民營企業,由它們進行投資運營,這個街道的命名權、沿街的廣告收益可以在未來若干年內承包給投資者,政府可以和投資者簽訂一個投資回報率保底的協議。通過這種方式,調動民間投資者介入基礎性設施的投資建設,其目的就是要穩增長,恢復DNI在中國經濟正常增長中應有的作用。
一攬子方案的第二點就是進行大規模的金融整頓。過去幾年,中國金融機構的擴張速度非常之快,由此也帶來了大量隱性的不良資產,必須經過一個重組清理的過程才能把資金盤活,否則當前“新錢填補壞賬”的尷尬局面就會不斷延續下去。
如何重組?中國在這方面不乏經驗,本世紀初的一輪銀行重組就非常成功。比如說,央行或財政部拿出一部分資金,聯合成立若干個資產重組公司,介入銀行與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清理。這種債務清理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起到1元錢清理出2到3元錢的作用,因為這種清理過程類似于清理三角債。通過這些清理,可以將中國經濟體系中的一些不良資產像切除腫瘤一樣切除出去,讓其不再影響中國金融和整體經濟。
在這個過程中,中央政府也應該積極擴大中央財政的發展規模。當前中國國債的規模遠遠不夠,中國的國債在國際市場上是稀缺產品,而中國地方政府通過投資平臺、地方投資公司所產生的債務卻是一桶渾水,需要徹底澄清。
第三條就是重新厘定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推出地方財政改革的一攬子計劃。地方財政是這一輪不良資產問題的始作俑者,抓住地方政府的公共財政就抓住了根除這一問題的七寸。為此,必須要給地方政府一些穩定的財政收入。在這個意義上,房地產稅是非常值得在短期內推出的。筆者反復強調,房地產稅的主要功力并不在于短期內控制房價—它不可能很快逆轉買房家庭的房價上漲預期,但是卻能夠給地方政府一個財政收入上漲的預期。此外,建議中央政府給地方政府更多的財政分成,對一些主要稅種比如增值稅,可以調整中央與地方分成的比例,地方占比可以從現在的25%上升到30%或者40%,讓地方政府獲得穩定財源。
與此同時,大規模清理地方融資平臺,規范地方政府的借債行為,從而鏟除未來地方政府不良貸款的根基。在某些地區,應該要求地方政府變賣一部分國有資產用于還債。同時,中央財政也要擴大債務的發行,可以用出臺金融整頓特別國債的方式來清理地方債務。
面對金融恐慌的底線思維
2013年的中國經濟比之于歷史上的一些困難年份比如1989和1999年要好得多,銀行總體上仍然有非常好的盈利,大量非金融國有企業也是盈利的,中央財政并沒有很多赤字,國債余額僅占GDP的18%,央行擁有巨額外匯儲備,中央與很多地方政府還有大量經營性資產,這些有利條件是合理應對金融恐慌的底氣,中國經濟的決策者沒有任何理由驚慌失措。
把金融恐慌變為全面改革的契機
這一輪金融恐慌不完全是壞事。它以一種集中爆發的方式暴露了中國經濟運行機制的不可持續性,充分顯現了改革的迫切性。這一輪金融恐慌勢必會催谷本來已經討論很久的一攬子改革措施的實施,通過改革,中國經濟完全有可能重拾過去30年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