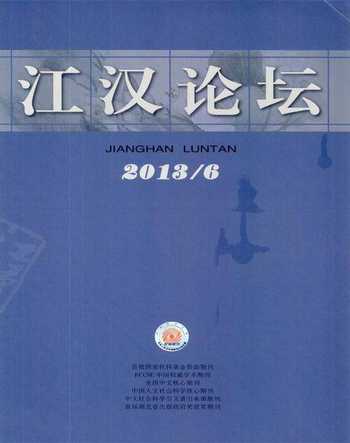主持人語
儒學與人權、民主的議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熱點問題。盡管我并不贊同白魯恂(Lucian Pve)的如下觀點——伊斯蘭教的民主尚屬可能,而“儒家民主”完全是不可能的,但我很重視他的詮釋立場。作為杰出的政治學家,他對我們理解亞洲特別是中國的政治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他深思熟慮的觀點必須被提及。他通過對中國人精神一文化的社會化與政治行為之間關系的分析。認為獨裁心態——他視之為儒家學說的典型特征——在中國人的“心靈習性”中根深蒂固,以致于即使有建立親近民主制度的良好意圖,也會不可避免地失敗。然而,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相信,有利的外部條件能使情況有所改觀,而且沒有理由認為文化不會改變。
既然在一些儒家社會,包括那些文化中國的社會,例如臺灣,這種改變事實上已經發生了,因此經驗已經證明,儒家文化圈內的社會絕不是不可能實現完全的民主的。誠然。新加坡和香港都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民主國家(地區),但法律規則在這兩地都得到了堅決貫徹。在這些地區,伴隨著出現公民社會的可能性、民主化進程在我看來十分順利。諷刺的是,臺灣的民主糾纏于毫無基本優雅可言的黨派政治,被大陸的大眾媒體廣泛報道,成為了中國公眾的反例。即使是深謀遠慮的知識分子,除了日益減少的自由主義者,都對臺灣的民主經驗表達了保留意見。但近些年來,隨著臺灣的民主化進程逐步走向正規。這種情況顯然已有了較大改變。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海內外似乎出現了一批聲音漸強的學者,在明顯沒有政府審查或鼓勵的情況下出版了許多論著,探討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民主制度和實踐與中國的治理方式并不相適宜。這暗示了無論是一種不同的民主形式或者甚至是一種非民主體系都更加適合中國國情。羅思文(Henry Rosemont)、安樂哲(Roger Ames),特別是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等學者做了很多工作,探尋“人權”對中國的社會幸福的有效性,以及就這點而言美國的情況。當然,質疑的目標并非人權本身,而是將個人主義作為人權的前提條件的自由主義觀點。一個顯著的例子是丹尼爾·貝爾支持“非自由民主”的觀點。
我個人的立場則有本質不同。我自忖為儒學復興運動中第一代和第二代思想家和實踐者之儒家精神的傳遞者。張君勱的儒家憲政主義和徐復觀的儒家自由主義并非對西方模式的被動接受。誠然,這兩種觀點是根據西方啟蒙運動最優秀的遺產——自由、理性、法治、人權和個人的尊嚴——而進行的創造性轉化。他們提倡一種新的儒家政治,反對獨裁主義、因循守舊和集體主義。他們從未懷疑,在西方的影響下和根據啟蒙精神。現代儒家人格應當是思想自由、理性、遵守法律、尊重和改善人權以及有力地保衛個人的尊嚴。畢競,儒家為了“成為君子”或“成圣成賢”的“為己之學”、“身心之學”、“天道性命之學”,與作為現代人類繁榮基礎的價值觀可能存在緊張與沖突。
換言之,沒有理由預設儒家民主在原則上是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此外,我們可以質疑基于個人的自由思想的普遍性,但我們必須承認,本著時代的精神,對分配正義、機會平等以及言論、出版、集會、宗教等自由的關注,即使不是抽象的普遍性倫理,也是世界性的倫理。誠然,正是在儒家批評精神的偉大傳統下,徐復觀將他自己定義為一個儒家自由主義者。
總而言之,新儒家公共批判的自覺意識已完全是民主的。中國整體是“現代民主”一種變體的宣稱,至少在今天看來,無法僅僅由簡單的經驗觀察所證實。對“中國模式”的主張不僅無知,而且顯得傲慢。儒學復興是一柄雙刃劍,成為獨裁主義的借口和對侵略性民族主義的盲目支持的危險都確實存在。然而,儒家民主并非臆想,而是一種美好的愿景;中國向功能上等同于一種新形式的自由民主的改革,不僅確實可能,而且在道德上也勢在必行。
二十年前,我與哥倫比亞大學狄百瑞教授共同推動北美地區儒學與人權的研究,其成果最后匯集在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一書中。近些年來,梁濤教授在推出思孟學派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同時,也積極致力于儒學與人權的研究,我與他在北大高研院曾先后舉行過兩次“儒學與人權”研討會,集中一批搞中國哲學和政治哲學的學者,對此問題作出深入探討。《中華讀書報》2010年09月30日曾以《學界熱議儒學發展新路向,用人權激活傳統儒學》為題做了報道。引起學界的關注。現梁濤教授將其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問時搜集到的西方學者的相關成果翻譯編輯成書,將以《美德與權利——跨文化視域下的儒學與人權》為名由北京大學出版社下半年出版。這些成果均在海外產生過一定的影響,相信對大陸學者也會有一定借鑒、參考作用。現《江漢論壇》愿意在該書正式出版前發表其中的部分文章,我認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特對《江漢論壇》表示感謝!也愿意對梁濤教授將要出版的新書做出鄭重推薦。
主持人:杜維明,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