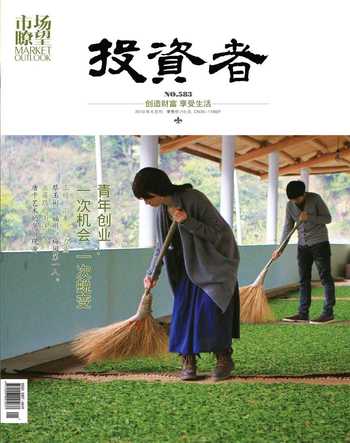蔡玉彬:福州“梅園第一人”
張芬
對古梅樹情有獨鐘的蔡玉彬從十多年前開始收集古梅樹根,如今自己的梅園內(nèi)已有上萬株各種名貴品種的古梅樹,他也成為福州“梅園第一人”。
由于鼓嶺的新梅園尚未完工,當下又恰巧不是“踏雪尋梅”的季節(jié),記者只好帶著遺憾和蔡玉彬約在他的小梅園見面。小梅園位于車水馬龍的浦上大道,距離倉山萬達廣場只需五分鐘車程。近年來,伴隨城市建設的步伐,梅園也逐漸被都市的“水泥森林”包圍,但這反而更加襯托出它那份高雅古樸的韻味,將園外的喧囂擋在每一個為梅而來的人身后。
重現(xiàn)萬梅勝景
置身于梅園內(nèi),遒勁黝黑的古梅樹錯落有致地隱藏在海棠梅、茶花、桃樹之中,盡管現(xiàn)在并非梅樹的花季,蔡玉彬仍然用心把梅園打理得井井有條,滿眼的郁郁蔥蔥似乎預示著下一次的綻放必定更加絢爛。
蔡玉彬與古梅樹結(jié)緣已經(jīng)有十余年,他也從“小蔡”成了“老蔡”。老蔡出生于福州的“花木之鄉(xiāng)”閩侯縣建新鎮(zhèn),在家鄉(xiāng)傳統(tǒng)和生活環(huán)境的熏陶下,他對花草有著天然的熟悉。從上世紀80年代起,蔡玉彬就開始經(jīng)營自己的苗圃。1998年,蔡玉彬在倉山梅塢一帶做城市綠化工程,無意中發(fā)現(xiàn)有不少古梅樹的樹根埋在老房子的院墻角無人問津,經(jīng)他打聽得知,老房子的主人搬走時,把古梅樹樹干砍走另作他用,卻嫌挖掘樹根太麻煩就留下了。蔡玉彬告訴記者,上百年的古梅樹就這樣被破壞真是太惋惜了,還好梅樹的生命力極其頑強,雖然被廢棄多年,那些古樹根還是存活的。
蔡玉彬表示,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里,“歲寒三友”或“四大君子”都少不了梅花,可是如今在福州卻難覓梅花成片的景象,很是遺憾。“其實,福州種梅花也曾興盛一時。《藤山志》載,‘明朝自梅塢至程埔頭周圍十里,家家戶戶門前遍地皆梅。每逢冬季梅花盛開,過江賞梅的游人川流不息,倉山因此被稱作‘梅花塢,現(xiàn)在倉山的梅塢路也由此得名,‘梅嶺冬晴更被列為‘南臺十景之一。”蔡玉彬說。
“十里花為市,干家玉作林”,在采訪中,蔡玉彬多次用福州方言反復念這兩句詩。他說,這是明代著名藏書家徐熥在《藤山觀梅》中的句子,說的正是明代福州倉山(古時稱藤山)成千上萬的梅花競相開放。“只可惜在明末清初時,大部分梅林毀于戰(zhàn)火,加上后人不懂得保護古梅樹,肆意砍伐,曾經(jīng)的香雪似海一去不復返。”蔡玉彬告訴記者,“想象當年的十里梅花該是多么震撼啊,既然福州有梅花興盛的歷史,生態(tài)綠化又越來越受重視,作為園藝師的我有心愿和責任重現(xiàn)萬梅勝景。”
尋古梅的“瘋子”
蔡玉彬想方設法到處收集古梅樹樹根,往返于福州倉山、閩侯是家常便飯,甚至安徽、山東、浙江都留下他的足跡。有一次,在他苗圃做事的一位來自永泰的老工人告訴老蔡,為了提高產(chǎn)量,永泰有大量樹齡古老的果梅被砍伐,樹根直接被丟棄。心疼不已的老蔡立刻驅(qū)車前往永泰,出高價把當?shù)氐睦厦窐淙抠I下。老蔡說,“梅樹主要分花梅和果梅兩類,由于花梅在特殊時期幾乎都被毀了,留存下來的古梅樹樹根基本都是果梅的,要經(jīng)過嫁接的等方式改為觀賞梅。”
只要聽說有古梅樹的消息,蔡玉彬就會立馬親自趕去查看,尋到根系完整的老梅樹頭,他就買下帶回福州。永泰一帶的村民們經(jīng)常能看見老蔡在村子里轉(zhuǎn)悠,很多人都認為他是一個“瘋子”,那些死樹根拿來燒火都不好使,還花錢買去,簡直是傻瓜。
有不少古梅樹根還是老蔡在緊要關頭搶救回來的。他指著一棵樹干上有段鋸痕的古梅樹告訴記者,朋友從永泰打來電話,說看到有村民為了蓋房子準備砍掉一棵古梅樹,問他要不要買。蔡玉彬二話不說,立即讓朋友先墊付定金,可因為正值夏天不適合移栽梅樹,他最終多花了一倍的價格請村民把樹保留到了冬天,又再花數(shù)千元雇了8、9個工人從村子里抬出來運回福州。
“一線皮就有生命一線天”,蔡玉彬相信梅樹的頑強,也相信自己能讓老樹“復活”。只要有活的樹皮,絕大多數(shù)的古梅樹經(jīng)老蔡的“妙手回春”都成功嫁接,但是做活古梅樹也非常辛勞,要管護上十年才能成為看不到嫁接口的原生樹,而且樹齡越長的樹干產(chǎn)生的空洞也越大,容易患病蟲害,夏天要一點一點地把藥打進每一個空洞里。不論是人力、物力還是財力,老蔡都自己承擔,但他從未打算靠賣古梅樹營利。“樹是有靈性的,尤其是古梅樹沉淀著福州一段歷史滄桑,在我看來,古梅樹是無價之寶。”蔡玉彬說。
做福州最大的梅園
蔡玉彬把收集來的古梅樹集中在閩侯南通鎮(zhèn)。經(jīng)過10多年的栽培,南通基地里已有上萬株梅花,不乏古梅樹發(fā)起的新枝,其中樹齡在百年以上的有50多株,30年以上的多達300多株。
當蔡玉彬帶著記者參觀小梅園時,他向記者介紹,到目前為止,他成功培育出的梅花品種有朱砂梅、大紅梅、垂枝梅、游龍梅、金皮梅、珍珠梅及白梅等十多個名貴品種,最令他驕傲的是,經(jīng)過多年研究試驗所得的極品觀賞紅梅“骨里紅”。正說著,老蔡隨即摘下身旁梅樹的一條枝椏,掰開樹皮看到骨頭里都是紅的,真是名副其實的“骨里紅”。“古梅樹經(jīng)歷數(shù)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風吹雨打,千溝萬壑的樹根古老蒼勁,如同化石一般蘊藏著它一生的故事。”蔡玉彬說。
小梅園中的古梅樹是眾多古梅樹中最具特色的。一棵“臥梅”映入眼簾,橫躺的粗壯的樹干已經(jīng)枝繁葉茂。在“臥梅”旁邊的是一株“手足相連”,一條筆直的樹干將兩根分叉的樹干相連在一起。“這本來是路旁橫倒的樹頭,我看它的粗細該有上百年了,帶回來整整花了5年時間終于成活。沒長葉的時候,路人說我怎么種死樹,到了開花長葉的季節(jié)他們才發(fā)現(xiàn)老樹也有新芽能開花。”蔡玉彬一邊撫摸著“臥梅”,一邊介紹著,眼中滿是喜愛之情。
眼下,老蔡位于鼓嶺的新梅園正在加緊建設,到今年冬天,那里便能成為福州規(guī)模最大的梅園。老蔡告訴記者,從南通搬遷到鼓嶺主要是因為,鼓嶺的氣溫相對低,可以讓梅花的花期更長,花開得更艷麗,而且鼓嶺天然的青山綠水和梅園交相輝映。
老蔡說,他打算讓鼓嶺梅園春天開桃花,冬天開梅花,一年四季都是花的海洋,再加上水榭樓臺,未來肯定能成為福州賞梅的好去處。他還表示,“鼓嶺梅園將免費向市民開放,美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嘛,我也盡最大的努力,讓福州重現(xiàn)‘千古寒香似海來。”
鏈接
福州的梅花印記
長樂梅花鎮(zhèn):唐武德年間(618—626年)因種植梅花花而得名,稱梅花坊新開里,明代改稱梅花所。轄梅城、梅新、梅南、梅北、梅東、梅西等6個村,為福建省第三大漁鎮(zhèn)。
倉山區(qū)梅塢路、梅塢頂、梅峰里和中洲梅花道:明時藤山(今倉山)多梅花,每逢冬天梅開時節(jié),滿山香透,郡人多栽酒來游,被譽為“瓊花玉島”、“梅花塢”,以后簡稱“梅塢”。
鼓山梅里:鼓山涌泉寺西南向的梅里景區(qū),因遍植梅花而得名。文人墨客在鼓山種梅、賞梅、晾詠梅的歷史可追溯到942年前,有至今保留的四幅摩崖石刻為證。目前古梅里一帶仍保留著一株百年古白梅,與涌泉禪院門口的一株百年古紅梅遙相呼應。
連江梅洋村:相傳清順治年間,劉邦的后人劉哲達在福建尋找世外桃源,在接近今日連江宦溪和亭江交接處,發(fā)現(xiàn)一條自東向西流動的小溪和許多老梅樹,于是定居此地(即梅洋)。現(xiàn)在海拔800多米的梅洋,仍有獨特的“梅溪、梅峰、梅林”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