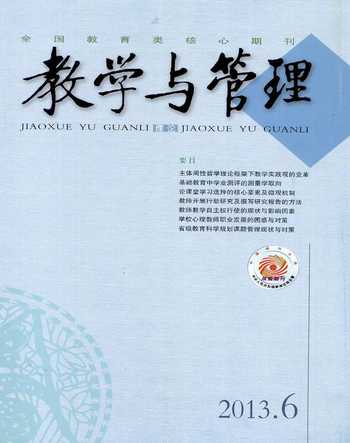略論教育知識的歸屬
萬正維
“教育知識”在當代知識論的學術語境下灌注了理論內涵。然而,概念內涵的更新不等于觀念的創(chuàng)新,“教育知識”若要與“教育理論”等術語相區(qū)分,避免“新瓶老酒”之詬病,宜先明確其自身獨特的性質與定義。探討“性質”與“定義”應以“屬概念”的界定為前提,由此,教育知識的“歸屬”便成為當下亟待解決的理論課題。本文擬立足于知識類型的劃分,從“劃歸依據(jù)”、“歸屬特點”與“理論啟示”等初探教育知識的“歸屬”。
一、知識及其類型
何謂“知識”。這或許是歷來最難解的哲學問題之一。難處不僅在于解答本身有多種角度,欲得公允的觀點殊為不易;更難者恐還在“知識”概念的彌散性,指稱內容充溢于各理智領域,難以劃出確切的認知界限。本文對知識的界定采用傳統(tǒng)“三要素”理論,即僅當(1)命題P是真的,(2)S相信P,(3)S的信念P恰當?shù)氐玫睫q護(justification),三個條件都得到滿足時才能說“S具有關于P的知識”[1]。為更加明確“知識”的涵義,特將其與“理論”概念相比較。廣義上“知識”包括“理論”,但知識論視野中的“知識”有別于“理論”。一方面,知識含有“信念”成分,某命題若不為人相信則絕無可能成為知識,知識具有“親主體”(pro-subject)的性質;理論一旦產(chǎn)生則竭力凸顯其“中立性”,含有“去主體”(de-subject)意蘊,成立與否皆力避主體信念的影響。另一方面,“辯護”是知識的構成要素之一,沒有獲得辯護的命題不能稱為“知識”;與知識的辯護相對的是理論的證明,但證明并非理論本身的構成要素,如常有所謂“有待證明的理論”。由此,知識和理論不容混淆,否則將失去其獨有的學術視角。
知識的辯護類型。根據(jù)“三要素”理論,“辯護”是知識生成的關鍵,辯護類型可作為劃分知識類型之依據(jù)。已有研究主要從形式(即辯護方式)上將辯護類型分為“內在主義”、“外在主義”與“語境主義”等。本文重在從實質(即辯護證據(jù))上分析辯護類型。知識的辯護證據(jù)大致有“事實”、“價值”以及“意念”三類,相應的辯護類型即為“事實辯護”、“價值辯護”與“意念辯護”。“事實”與“價值”解讀者甚眾,其涵義明晰易曉,“意念”則須稍作說明。所謂“意念”,簡而言之,是一種心理力量,含有認識和邏輯成分[2],是研究主體對人類主體的自覺歸附,以類主體的精神力量專注于求解某一知識難題的特殊意識。我國古人很早就開始關注“意念”,例如,“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3],論者已認識到,意念的對象并非簡單的事物形象,而是更高級的某種存在;又如,王弼的“言意論”認識到,意念是“圣人”制定的,可根據(jù)意念所表現(xiàn)的內容探尋圣人的本意[4]。此處若把“圣人”理解為人的“類主體”而非“個體”主體,則無疑是十分深刻而獨到的見解。
知識類型與辯護類型密切相關。依據(jù)上述劃分,可將知識分為“事實知識”、“價值知識”與“意念知識”。“事實知識”指,知識辯護的最終證據(jù)是“事實”,命題的指稱對象與“事實”一致;“價值知識”指,知識辯護的最終證據(jù)“價值”,命題涵義以一般價值取向為支撐;“意念知識”指,知識辯護的最終證據(jù)是知識主體的意念,這種意念不是個人的意念,而是知識主體向類主體的自覺歸附而感悟出的堅定意念。綜觀三類知識可得,其一,知識的辯護證據(jù)皆非“個體”的主觀臆想。“事實”證據(jù)的非主觀性自是無庸贅言,“價值”與“意念”作為辯護證據(jù),是知識主體以人類主體的精神力量對知識的深度確證,并非個體的價值偏好與意想信念。其二,比較“事實”、“價值”與“意念”三個范疇,事實屬于客體范疇,“價值”屬于主客結合范疇,意念屬于主體范疇,三者包含了所有辯護的證據(jù)類型。從邏輯上看,上述知識類型的劃分是周延的。其三,知識類型的判斷依據(jù)是“知識辯護的最終證據(jù)”。“最終證據(jù)”對應的知識體系中的命題可稱為“基本命題”,基本命題是知識體系中的“阿基米德點”,其辯護證據(jù)的類型是決定知識歸屬的重要參照。
二、教育知識的劃歸依據(jù)
據(jù)上述,分析某種知識的辯護與類型,須找出支撐其體系的基本命題,基本命題的辯護證據(jù)是判斷知識歸屬的重要依據(jù)。那么,教育知識體系中是否存在“基本命題”呢?本文認為,教育知識體系中有兩類基本命題,一是本體性命題,二是目的性命題。本體性命題,即關于“教育是什么”的命題。各種教育知識體系都預設了對“教育是什么”的回答與辯護;回答與辯護既標明知識主體的教育本體立場,又確保和支撐整個知識體系的一致性與穩(wěn)定性。作為其他命題的辯護基礎,本體性命題常以隱性的方式滲透于整個教育知識體系。分析隱性的本體性命題,需要對教育知識體系作整體考察,才能歸納和概括出表達“教育本體”思想的命題。目的性命題,即關于“教育為了什么”的命題,引導教育知識體系的發(fā)展方向,是顯在而“活躍”的要素,在教育知識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歷史上各種教育學說都是從教育目的的假設中推衍出來的建議體系;目的性命題是教育知識的一大邏輯前提,其不同用法和含義決定著教育知識的不同性質[5]。
本體性命題的辯護證據(jù)。對“教育是什么”的辯護,從根本上說不能以“事實”為證據(jù)。現(xiàn)實的教育錯綜復雜,“教育是什么”基本上是個無法求解的知識難題[6],更是難以用確定的事實或價值證據(jù)對其辯護。本體性命題的辯護是形而上的論證過程,辯護證據(jù)是人的類主體“意念”。本體性命題的辯護需要知識主體自覺感悟、移入人的類主體意念,借助類主體意念深刻反省辯護命題,最終形成堅定的個體意念。不同知識主體對同一本體性命題的辯護程度不同,這緣于個體對類主體意念的感悟能力不同,個體的“感悟能力”集中反映了其自身的人文素養(yǎng),決定其對人類主體的歸附程度。一般而言,人文素養(yǎng)越高對類主體意念的反省和認識越深刻,然而深刻的感悟極有可能一時間得不到其他知識主體的認同,如赫爾巴特曾為此悲嘆道:“我那可憐的教育學沒能喊出它的聲音來。”[7]但隨著人類素養(yǎng)的普遍提升,最終必然獲得更多認同,也正如隨后赫爾巴特思想影響的迅速擴大。
本體性命題辯護的歷史考察。拉開歷史的帷幕不難發(fā)現(xiàn),一部教育知識史就是一部知識主體感悟類主體意念,并以此辯護教育基本命題的歷史。大體說來,人們對本體性命題的回答和辯護形成有“工具論”—“適應論”—“生活論”—“教化論”等知識體系。“工具論”貫穿古代教育思想。以柏拉圖教育思想為例,柏氏以教育可將各類素質的人“篩選”出來過正義生活為意念,以此辯護教育是建構“理想國”不可缺少的工具,提出“工具論”的教育知識體系。此后,盧梭以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崇拜”思想反對“工具論”,他以“出自造物者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8]為意念,以此辯護教育就是適應人發(fā)展,提出“適應論”的教育知識體系。杜威從另一角度批判了“工具論”,他以“學校即社會”、“從做中學”、“教育即生長”為意念,辯護教育本身就是生活而非生活的預備,提出了“生活論”教育知識體系。近來我國論者提出,教育是一種促進人精神發(fā)展的而避免規(guī)訓的教化[9],論者以人的“自由”本質為意念,辯護教育是一種自由的實踐(即教化)而不是束縛自由的實踐(即規(guī)訓),提出“教化論”的教育知識體系。綜上,知識主體感悟類主體所獲的意念,既為本體性命題提供堅定信念,又作為主體性證據(jù)助其辯護,不斷催生新的知識體系,是教育知識演進的內在動力。
目的性命題的辯護證據(jù)。目的性命題的辯護以社會一般價值為證據(jù),體現(xiàn)了知識主體對社會一般價值的認同。在辯護中,知識主體須自覺感受社會價值取向,深沉追問“教育何為”?并將所得化為教育自身的追求。本體性命題是知識主體內向反思教育本體而獲得辯護,目的性命題則是知識主體外向導入社會價值而獲得辯護。教育活動總是以具體的人為對象,社會價值通常在教育活動中凝結為人的理想模型,因此關于人的理想模型自然成為目的性命題的核心要素。據(jù)有論者研究,教育思想史上有關人的理想模型大致有,“宗教人”—“自然人”—“理性人”—“社會人”等[10]。各自的辯護邏輯大致如下,“宗教人”(Homo Riligiosus),以熱愛、贊美、信仰和服從上帝的價值取向為證據(jù),辯護教育就是為完善人的神性;“自然人”(Homo Naturalis),以遵循和尊重自然的價值取向為證據(jù),辯護教育應幫助人發(fā)展自身固有的內在傾向;“理性人”(Homo Sapiens),以崇尚理性生活的價值取向為證據(jù),辯護教育應該培養(yǎng)有理性的人;“社會人”(Homo Sociologicus),以社會生存和發(fā)展的價值取向為證據(jù),辯護教育應促使人的社會化。
三、教育知識的歸屬及啟示
教育知識的類型。知識類型的劃歸須依循其基本命題的辯護證據(jù),此論若屬不謬則可得出下述結論:教育知識體系包含“本體性命題”與“目的性命題”兩類基本命題,其辯護證據(jù)分屬“意念”與“價值”,由此,教育知識當橫跨價值知識與意念知識兩大類型,具有“兩棲性”特點。此特點表明,不能將教育知識僅作為價值知識而忽視了沉思與追尋類主體的意念,也不能將教育知識只作為意念知識而忽視了感悟與遵循社會一般價值取向。由于意念知識與價值知識的辯護遵從不同的理路,各自擁有不同類型的辯護證據(jù),故教育知識既相當豐富和復雜,又充斥著各種爭論和“迷惘”。不少爭論甚至伴隨著教育知識的始終,例如,教育知識的科學化問題,教育知識與實踐的關系問題,教育的社會本位和個人本位問題等等。不清楚教育知識的歸屬特點或許正是許多爭論“山重水復疑無路”之癥結,利用教育知識歸屬理論或能為解決理論紛爭提供新的思路。限于篇幅,現(xiàn)以“教育知識的科學化問題”與“教育知識與教育實踐的關系問題”為例粗作分析。
“教育知識科學化”既應放在整個知識史中反思,又應結合知識的辯護理論分析。據(jù)福科(MichelFoucault)研究,“所有門類的知識的發(fā)展都與權力的實施密不可分”[11],知識演變是各種權力爭斗的痕跡。在知識史上,意念知識,如遠古神話知識與古代宗教知識,因其是統(tǒng)治階級解釋君權的理論根據(jù),最先被認可為人類知識。隨著市民社會發(fā)展成熟,社會本身需要以正義、公平等一般社會價值來維護,市民階級也需要以世俗價值體系反抗神權。以社會一般價值為辯護證據(jù)的價值知識開始獲得統(tǒng)治階級承認。工業(yè)革命后,追求物質利益的資產(chǎn)階級居統(tǒng)治地位,自然科學因能助其攫取物質利益而被宣稱為“知識”,不符自然科學辯護特征者被貶為“非知識”。在事實知識主導知識界的背景下,教育知識為辯護自己的“知識身份”便努力改變辯護方式,取向事實知識的辯護路徑。然而,吊詭的是,當知識主體改以“事實”作為教育知識的辯護證據(jù),教育知識卻失去了“知識”的身份。甚至有人稱道,“理論(知識)”對于教育來說只是一個“尊稱”[12]。可見,“教育知識科學化”并不是出于深刻認識教育知識的辯護性質與類型歸屬的結果,實乃教育知識在知識“場域”中的迷夢。若以上述歸屬理論觀之,教育知識屬于意念知識和價值知識,“事實”并不能為其提供最終辯護,其基本命題的辯護證據(jù)屬于“價值”與“意念”。因此,只有“價值”與“意念”才能為教育知識筑就堅實的基礎,建成輝煌的知識體系的大廈。
教育知識與實踐的關系通常有兩種表述,一種常見表述為:“教育知識與實踐相結合。”“結合”以一定程度的“符合”為前提,教育知識與實踐相“符合”意味著,實踐活動直接為教育知識提供辯護,教育知識自動發(fā)揮對教育實踐的影響。然而據(jù)前文所述,能為教育知識提供最終辯護的不是客體性證據(jù),而是非客體性證據(jù)的“價值”與“意念”,而且知識具有“親主體”特性,教育知識只有以主體信念(包括知識和實踐主體)為“中介”才能影響實踐活動。因此,上述表述顯然是“去主體”的“理論”思維的認識結果,而非從“知識”角度出發(fā)得出的研究結論,其中“教育知識”只是“教育理論”的“替身”,整個表述不過是“教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翻版而已。另一常見表述為:“教育知識指導實踐。”判斷這一常識性表述宜先明確,上述三類知識與實踐的關系各不相同,處理知識與實踐的關系時,需要區(qū)別對待而不能相互僭越對知識的期望。事實知識以客觀事實為辯護證據(jù),客觀事實具有較強的穩(wěn)定性,由它辯護而成的事實知識可以“指導”實踐主體對其余同類事實的認識和改造。價值知識以社會價值為辯護證據(jù),社會價值的可變性使此類知識不具有確定性,它只能通過“引導”教育實踐主體的價值追求來影響實踐。意念知識以知識主體感悟的類主體意念為辯護依據(jù),它可“啟發(fā)”實踐主體感悟類主體意念,助其祛除實踐主體的“洞穴假相”,使其以類主體的氣度從事教育實踐。教育知識屬于價值知識與意念知識,它只能“引導”教育實踐主體的價值追求、“啟發(fā)”實踐主體積極感悟類主體意念,“間接”地影響教育實踐。由是觀之,“教育知識指導實踐”以事實知識作用實踐的方式類推價值知識和意念知識,是對教育知識與實踐關系的又一誤解。
參考文獻
[1] 徐向東.懷疑論、知識與辯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 金丹元.傳統(tǒng)藝術思維與意念.文藝理論研究,1999(6).
[3] 莊子·秋水.王巖峻,吉云,譯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4] 任繼愈.中國哲學史(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 瞿葆奎,等.教育基本理論之研究(1978~1995).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6] 顧明遠.對教育定義的思考.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3(1).
[7] [美] S·E·佛羅斯特.西方教育的歷史和哲學基礎.吳元訓,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4.
[8] [法]盧梭.愛彌兒.李平漚,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9] 金生鈜.規(guī)訓與教化.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
[10] 石中英.重塑教育知識中人的形象.教育研究,2002(6).
[11] [法]M·福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嚴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2] [英]奧康納.教育理論是什么.瞿葆奎,譯.教育學文集·教育與教育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責任編輯 關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