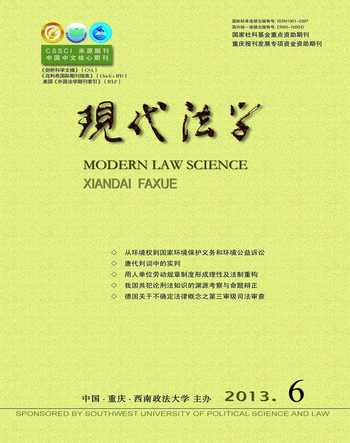漢代簡牘文獻刑事證據材料考析
張琮軍



摘 要:通過研究漢代簡牘文獻發現,漢代的刑事證據制度已趨向規范化、制度化,在司法活動中表現為重事實與證據,初步創立了客觀主義的刑事證據制度。在訴訟程序中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證據鏈條:包括據證起訴制度、庭審質證制度、據證決斷制度以及俱證乞鞫與驗證復獄制度等。漢代刑事證據制度的確立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為中國傳統刑事證據制度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也為當代中國刑事證據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借鑒價值。
關鍵詞:漢簡;刑事證據;據證定罪;俱證乞鞫
中圖分類號:DF09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3.06.04
經過對《張家山漢簡》、《居延漢簡》及《居延新簡》等簡牘文獻的細致研究,不難發現,漢代的刑事證據制度呈現出鮮明的客觀性傾向,其司法審判強調據證斷罪、依律量刑。《奏讞書》中記載的諸多漢代案例,都能夠對此進行印證。司法官吏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注重各項證據的收集、檢驗,并將之相互印證。以求案件事實清楚、明白,最后依據相應的律條作出判決。證據居于主導地位,它的運用貫穿于訴訟的全過程,并且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鏈條,從而為訴訟審判活動提供了重要保障。筆者總結出證據運用于訴訟程序的全過程,即起訴是依據證據提起控訴的過程;官府的庭審活動是鑒別證據,由原被告雙方進行質證的過程;審案官吏的判決是據證定案的過程;乞鞫是司法機關驗證復審,平復冤獄的過程。
一、起訴證據材料的研究
漢代提起訴訟,主要有自訴、告發、舉劾三種方式。其中,前兩者統稱為告劾。提起訴訟是“據證起訴”的過程,也是刑事證據形成與運用的首要環節,經由此開始收集各類證據,對案件事實予以調查和認定。
以下分別對漢代刑事案件的四種起訴方式加以論述,并作總結概括:
(一)自訴與證據
漢代的自訴既可以書面形式提起,又可以口頭形式提起。
1.自言
以口頭形式提起的自訴在簡牘資料中稱為“自言”。漢簡中關于“自言”的記載數量也比較多,以《居延漢簡》為例:
字初卿,在部中者,敢言之,尉史臨,白故第五燧卒司馬誼自言,除沙殄北,未得去年九月家屬食,誼言部以移籍廩,令史田忠不肯與誼食……(居延漢簡89·1—2)陳兵指出,我國古代特別重視口供的作用,持“斷罪必取輸服供詞”與“無供不錄案”的斷罪原則,所以將口供稱為“證據之王”,直至清朝仍是如此。(參見:陳兵.解讀現代“刑訊逼供”現象的根本原因——從我國古代拷訊制度合法化層面人手[J].江西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3,(4).)劉顯鵬也指明,中國傳統訴訟的特殊之處在于極為重視被告人口供的“口供主義”,在中國傳統的訴訟當中,被告人口供是最重要的證據,沒有被告人供認,一般不能定罪。其他證據的證明力都比不上口供高,人證、物證、書證只是輔助證據,而且必須在具有口供的情況下方能發揮作用,如無口供,僅憑其他證據不能定案。相反,如果有口供,即使沒有其他證據,也可定案。(參見:劉顯鵬.中國古代口供制度粗探[J].國土資源高等職業教育研究,2004,(3).)
即尉史臨說:“第五烽燧的卒司馬誼自行投訴,其除沙于殄北,去年九月沒有獲得應配送給家屬的糧食,他將領取糧食的憑證交與配送部門,而令史不肯向其配送糧食……
□此處“□”為原間殘缺,間文不可釋。下同。
壽自言,候長憲傷燧長忠,忠自傷,憲不傷忠,言府一事一封。(居延漢簡143·27,143·32,143·33)
壽自行投訴說,候長憲傷害燧長忠,(查悉)忠系自傷,并非被憲所傷……
以自言的方式提起訴訟,形式簡單、操作便利,因而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尤其適合于不識文墨的廣大鄉民就簡易的刑事案件向官府自行投訴。
2.書告
書告,是指控告者以書面形式向地方或中央的司法機關提出訴訟,這種形式一般用于各種重大案件的訴訟與直訴。因上書的對象和方式不同,可分為普通上書與越訴。
普通上書是指案件受害方以書面材料提出訴訟,此類訴訟主要由當地司法機關受理。《奏讞書》中記載了多則書告案例,試例如下:
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戌,“三月己巳大夫祿辭曰:六年二月中買婢媚士五點所,價錢萬六千,迺三月丁巳亡。”(簡8—9)[2]
(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八月初三日,“三月己巳日,大夫椽狀辭:六年二月中,在士伍點住處買婢女媚,身價一萬六千錢。三月丁巳日逃跑了。”
十二月壬申大夫詣女子符,告亡。(簡28)
(漢高祖十年)十二月壬申日,大夫送來一位名叫符的女子,告她逃亡。
(二)告發與證據
即當事人以外的同居、同伍、同里的普通百姓知悉犯罪后進行控告或揭發的行為。漢代的告發是由秦代繼承而來,是由行為人主動地或者由法律規定的強制性義務而引發的。《居延新簡》中記載了一則告發案例:
內郡蕩陰邑焦里田亥告曰:所與同郡縣□□□□死亭東內中,……(居延新簡E·P·T58·46)[3]
即名為田亥的人報告說,同郡縣的人死于亭東內中東首。
漢代為了糾舉犯罪,對于告發屬實者,法律規定給予獎勵,如《二年律令·捕律》記載:
诇告罪人,吏捕得之,半購诇者。(簡139)
即給予告發者一半的獎勵,如同秦一樣,應該是黃金一兩。同時,漢律也明確作出規定,諸同居、同伍、同里及職務相關(包括相鄰商販)者均負有相互監督、舉報罪行的義務。如《二年律令·盜律》規定:
劫人、謀劫人求錢財,雖未得若未劫,皆磔之。罪其妻、子,以為城旦舂。其妻子當坐者偏(徧)捕,若告吏,吏捕得之,皆除坐者罪。(簡68—69)
這是關于同居者相告的法律規定。劫人、謀劫人案的親屬如不及時告發將以連坐論處,只有告發才能免除其連坐的罪責。
《后漢書·百官志》記載了漢律關于同伍者相互伺察,有罪相告的規定:“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這項義務在《二年律令·戶律》中有具體的規定: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為伍,以辨□為信,居處相察,出入相司。有為盜賊及亡者,輒謁吏、典……不從律,罰金二兩。(簡305—306)《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漢代爵級共分為二十等級,五大夫為第九爵,屬于大夫之列。《周禮·地官·司徒》曰:“五家為鄰,四鄰為里。”
即凡是爵位在五大夫以下者,相鄰五家為一聯保單位,相互監督,發現為盜賊及逃亡者,立即報官,違背者受處罰。《二年律令·錢律》中也規定了同居、同伍者有罪相互告發的法律義務:
盜鑄錢及佐者,棄市。同居不告,贖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罰金
四兩。(簡201)
如果同居者對“盜鑄錢”罪行不告發的,以“贖耐”論處。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發的,罰金四兩。
不僅同居與同伍者有相互告發罪行的法律義務,而且,因店鋪相連的商販之間,也有相互監督告發罪行的義務。《二年律令·市律》中規定:
市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贓)為盜,沒入其所販賣及賈錢縣官,奪之列。列長、伍人弗告,罰金各一斤。(簡260)
即商販藏匿商物而不據實納稅的,對其本身進行處罰之外,與之同列的列長、同伍者也要受到處罰。
由上可見,漢代統治者為了打擊犯罪,穩定社會秩序,繼承了秦代的做法,在法律上作出了較為周密的規定。不僅鼓勵告發犯罪行為,而且設置了諸多主體之間的舉告義務。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護和抑制犯罪行為發生的作用。
(三)舉劾“劾”的字義,舊律盡管皆圍繞治罪立義,但具體解釋卻頗有不同。《說文·力部》云:“劾,法有罪也。”段注云:“法者,謂以法施之。《廣韻》曰:‘推窮罪人也。”《急就篇》“諸罰詐偽劾罪人”,顏師古注曰:“劾,舉案之也,有罪則舉案。”《尚書正義·呂刑》云:“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相較而言,四種釋義以顏師古注為允當,顏注也是前有所承。《文選·通幽賦》“妣聆呱而劾石兮”,注引項岱云:“舉罪曰劾”。 與證據
上述兩種訴訟的提起方式均可稱為告,是“下告上”訴訟行為的總稱,而劾是“上告下”訴訟行為的總稱,誠如沈家本所云:“告、劾是二事,告屬下,劾屬上。”[4]漢代繼承了秦代的舉劾制度,即各級司法官吏代表官府舉告犯罪行為。漢代在犯罪案件審理過程中,劾奏是必備程序,否則將視為違法,并追究相關者的法律責任。根據被舉劾對象的不同,可以分為對普通人犯罪的舉劾和對官吏犯罪的舉劾兩種。
1.對普通人犯罪的舉劾
漢代負責糾察罪犯的基層組織機構稱為“亭”,“求盜”是亭中專門負責捕“盜”的官吏。《漢書·高帝紀》注引應劭語:“求盜者,亭卒。”這是由秦代承繼而來的。
《奏讞書》中記載了有關基層官吏舉劾普通人犯罪的案例,如:
六月戊子發弩九詣男子毋憂,告為都尉屯,已受致書,行未到,去亡。(簡1—2)
六月戊子日,發弩卒九解送到男子毋憂,告發該犯接到都尉征發屯卒的文書后逃跑,不去指定地點報到。
如果官吏未能積極行使其應盡的舉劾職責,將受到處罰,輕為失職,重則坐罪。即使對于犯罪行為不知情,也要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
《二年律令》中有關于官吏失職的法律懲處規定:
盜賊發,士吏、求盜部者,及令、丞、尉弗覺智(知),士吏、求盜皆以卒戍邊二歲,令、丞、尉罰金各四兩。令、丞、尉能先覺智(知),求捕其盜賊,及自劾,論吏部主者,除令、丞、尉罰。一歲中盜賊發而令、丞、尉所(?)不覺智(知)三發以上,皆為不勝任,免之。(簡144—145)
意為發生賊盜案件,士吏、求盜所管轄的地區及令、丞、尉未發覺,士吏、求盜以卒身份戍守邊防兩年,令、丞、尉各處罰金四兩。如果令、丞及尉能夠事先覺察將其捕獲或者徑行舉劾,由直接負責的官吏承擔責任,對令、丞及尉不予處罰。如果一年中發生三次以上未發覺賊盜犯罪的行為,令、丞及尉均免職。
這條律文在史籍中多印證,如《漢書·酷吏傳》載:“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即發生眾盜賊作亂的案件未能覺察,或者雖覺察而未捕滿一定人數盜賊的,郡守官以下直至小吏主管人一律處死。
2.對官吏犯罪的舉劾
秦漢時期,已形成了一套對官吏較為嚴密的監察制度。監察發現官吏的犯罪行為,進行舉劾,啟動追究其刑事責任的訴訟程序。漢代出土簡牘法律文獻中記載了大量舉劾官吏的案例,如《奏讞書》中的案例三是江陵丞等人對臨菑(淄)獄史闌的劾;案例十四是安陸丞忠對獄史平舍匿無明數大男子種的劾。這些案例均是縣級專管司法的丞對縣級一般官吏的舉劾。《合校》中記載了一樁關于兩名戍卒相互斗傷的案件,因雙方皆致傷,故對兩人分別進行舉劾,并行拘捕。兩份劾文如下:
戍卒東郡畔戍里靳龜,坐乃四月中不審日,行道到屋蘭界中與戍卒函何
陽爭言,斗,以劍擊傷右手指二所。地節三年八月已酉械擊。(簡13·6)
戍卒東郡□里,函何陽,坐斗以劍擊傷戍卒同郡縣戍里靳龜,右脾一所,地節三年八月辛卯械擊。(合校簡118·18)
即東郡畔戍里靳龜的兩名戍卒相互械擊,兩人皆致傷,一位傷右手指,一位傷右脾。
在漢代,舉劾官吏犯罪要求有書面的劾狀。《居延新簡》中的“不侵守候長業劾亭長等盜官兵逃亡”的劾狀較為典型,原文如下:
建武六年三月庚子朔甲辰,不侵守候長業敢言之:謹移劾狀一編,敢言之。
迺今月三日壬寅,居延長安亭長王閎、閎子男同、攻虜亭長趙常及客民
趙閎、笵翕等五人俱亡,皆共盜官兵,臧千錢以上,帶大刀、劍及鈹各一,
又持錐、小尺白刀、箴各一,蘭越甲渠當曲隧塞,從河水中天田出。案:常
等持禁物蘭越塞,于邊關傲逐捕未得,它案驗未竟。蘭越塞天田出入□狀辭曰:公乘居延中宿里,年五十一歲,姓陳氏,今年正月中府補業守
候長,署不侵部,主領吏跡候備虜盜賊為職。迺今月三日壬寅,居延常安亭
長王閎、閎子男同、攻虜亭長趙常及客民趙閎、笵翕等五人俱亡,皆共盜官
兵,臧千錢以上,帶大刀、劍及鈹各一,又各持錐、小尺白刀、箴各一,蘭
越甲渠當曲隧塞,從河水中天田出。案:常等持禁物蘭越塞,于邊關傲逐捕
未得,它案驗未竟,以此知而劾無長吏使,劾者狀具此。
三月己酉甲渠守候 移居延寫移如律令。掾譚、令史嘉。(新簡E·P·T68:54-76)居延,漢代縣名,位于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常安、攻虜均為居延縣所屬亭名。不侵部,甲渠候官屬部。
這篇遞送劾狀的文書,簡文較為完整。劾狀通常是逐級上報的,本案公訴人不侵守候長陳業將劾狀報送甲渠候官,然后由候官轉呈有關部門。劾狀主要由呈文、劾文及狀辭三部分合成。第一段為呈文,清楚地說明了起訴時間、起訴人、文件名稱及數量;第二段為“劾文”,說明被告的犯罪事實及對其調查情況;第三段為“狀辭”,包括原告身份的說明、被告的犯罪事實及調查情況;最后一段為上級機構甲渠候的轉呈文。
在《漢書》中也記載了多則舉劾官吏的案件,如《蓋寬饒傳》載:“(蓋寬饒)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眾多。”這是負有監察職責的司隸校尉舉劾官吏的記載。
如果官吏“劾人不審”以及“輕罪重劾”則要承擔“失”罪與“不直”罪的后果。《二年律令·具律》載:
劾人不審為失,其輕罪也而故以重罪劾之為不直。(簡112)
意為官府舉劾嫌犯不當是過失行為,將輕罪故意舉告成重罪為不直。
經過論證可知,舉劾是官府對刑事案件主動進行糾舉,類似于今天的公訴。漢律對于舉劾制度做出了明確的法律規定,規制了明確的執行主體、具體的運行程序及嚴格的劾狀形式。
通過對漢代訴訟提起方式的分析與論證,可以得出結論:同秦代一樣,漢代刑事訴訟的提起是“據證起訴”的過程。告劾是啟動訴訟必不可少的程序,通過告劾形成劾狀,當中涵蓋了啟動刑事訴訟程序所要求的基本證據。以自訴、自首及告發三種方式提起的刑事訴訟,至少具備了供辭證據。如前所述,供辭證據包括被告的口供、原告的陳述及案外人的證人證言。而且,由以上所提供的材料可知,多數情況下起訴人還會同時提供一定的物證。舉劾則更是一種據證起訴的方式,因為官吏之所以會舉劾,要么是發現了殺傷、賊盜等犯罪事實,要么是接到了發生犯罪的舉報。
可見,提起訴訟是整個刑事訴訟審判環節證據運用的首要步驟,也是獲取刑事證據的最初環節。正因為如此,漢律中對刑事訴訟的提起作了嚴密的法律規制。強調了告劾的重要性,沒有告劾而系人,則被視為違法,要受到法律制裁。西漢“治淮南王獄”,列舉其罪行時,便有“擅罪人,無告劾系治城旦以上十四人。” [5]的記述。《二年律令·具律》中對此作出了明確的規定:
治獄者,各以其告劾治之。敢放訊杜雅,求其它罪,及人毋告劾而擅覆治之,皆以鞫獄故不直論。(簡113)
司法官吏應根據告劾內容審斷案件。如敢制造障礙不法審訊,審斷告劾以外的罪或者無告劾而擅自審斷的,均以故意不如實斷案論罪。
[HS(3] [HTH]二、審判證據材料的研究
[HTSS][HS)]
審判程序首先要進行質證,包括聽取被害人的陳述、訊詰被告及詢問證人。通過這些環節收集和審查刑事證據,以便確定案件事實。對審訊過程中原告、被告和證人的言辭及其他證據的收集、審查情況,要制做詳細的書面記錄,稱為“爰書”。這是法官最后進行量刑與斷決的依據。《史記·酷吏列傳》中便有“傳爰書”的記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史記·酷吏列傳》裴骃集解引蘇林曰:“爰,易也。”司馬貞索隱引韋昭曰:“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漢書·張湯傳》引師古注:“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籾山明也提出,“毋庸贅言,這些文書是為了給縣官做判決提供依據。因為這些文書就是爰書,所以才稱其為‘傳爰書”。(參見:籾山明.爰書新探——兼論漢代訴訟[G]//簡帛研究譯叢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1):178.) 以下詳細論述刑事證據在整個案件鞫斷環節中的具體運用。
(一)庭審中的質證
漢代承襲秦代的質證制度,將原告的陳述、證人證言與被告的口供進行質對,以便澄清案件事實。在審訊過程中,原被告雙方或其代理人必須到庭接受法官的訊問,進行質對。同時,由于證人提供的證言是重要的證據,對澄清案件事實意義重大。因此,證人也必須出庭作證,并參與質對。《奏讞書》中的第二則案例,向我們展示了庭審質證的情形:
大夫祿辭曰:六年二月中買婢媚士五點所,價錢萬六千,迺三月丁巳亡,求得媚,媚曰:不當為婢。
媚曰:故點婢,楚時去亡,降為漢,不書名數,點得媚,占數復婢媚,賣祿所,自當不當復受婢,即去亡,它如祿。
點曰:媚故點婢,楚時亡,六年二月中得媚,媚未有名數,即占數,賣祿所,它如祿、媚。
詰媚:媚故點婢,雖楚時去亡,降為漢,不書名數,點得,占數媚,媚復為婢,賣媚當也。去亡,何解?.
媚曰:楚時亡,點乃以為漢,復婢,賣媚,自當不當復為婢,即去亡,無它解。(簡8—12)
這是原告祿、被告媚及證人點三者在法官的主持下進行質證的情形。祿控訴說,自己以萬六千錢從點處買得媚,三月丁巳日逃跑了,抓獲她后,她說:自己不應當是奴婢;媚辯解道,她以前是點的婢女,楚時期就逃脫了。到了漢朝,沒有上戶籍。點逮住她后,仍將她作為奴婢,報了戶口,賣給祿。她認為自己不應該還是奴婢,就逃跑了。其他情況,和祿所說的相同;證人點提供證言,媚以前是他的婢女,楚時期逃跑了。六年二月中找到她,她沒有戶口,給她報了戶口,賣給了祿。其他情節,和祿、媚所說相同;法官詰問媚,你以前是點的奴婢。雖然楚時逃跑了,可是到漢朝后,并沒有申報戶籍。點逮住你后,仍將你作為奴婢報了戶口,將你賣與他人,符合法律。逃跑掉了,怎么解釋?媚回答道,楚時候她已經逃跑,點認為到了漢朝后她仍是他的奴婢,賣了。她認為自己不應當還是奴婢,就逃跑了。沒有其他要辯解的。
這則案例較為清晰地記錄了漢代庭審過程中的質證情形,首先是原告的控訴,其次是被告對原告控訴的回應,接著證人提供證言。然后法官進行訊問,當事人都必須如實回答。《奏讞書》的第四則案例也對法庭的質證過程進行了詳細地記錄:
大夫所詣女子符,告亡。
符曰:誠亡,詐自以為未有名數,以令自占書名數,為大夫明隸,明嫁符隱官解妻,弗告亡,它如所。
解曰:符有名數明所,解以為無恢人也,娶以為妻,不知前亡,乃疑為明隸,它如符。
詰解:符雖有名數明所,而實亡人也。律:娶亡人為妻,黥為城旦,弗知,非有減也。解雖弗知,當以娶亡人為妻論。何解?
解曰:罪,無解。(簡28—31)
即大夫控告女子符逃亡;女子符辯稱,她是逃跑,并謊稱自己戶籍,依照法令的規定去報了戶口,成為大夫明的奴隸。被嫁給隱官解為妻,但沒有告訴他自己逃跑的事。其他情況和控告的相同;解說,符在明家有戶口。他認為符沒有什么特殊之處,不知她從前曾逃跑過,以為她是明的奴婢,其他情節與符所說相同;法官詰問解,雖然符在明家有戶籍,而實際上是一個逃亡的人。法律規定:“娶亡人為妻,黥以為城旦,弗知,非有減也”。你雖然不知道,仍應該按照娶逃亡者為妻論處。你有什么可以辯解的?解答道,自己認罪,沒有要辯解的了。
通過展示案例可知,普通身份的原、被告雙方在質證過程中進行控訴與供述,證人提供證言,法官隨之反復訊問,直至澄清案件事實為止。如果原、被告對法官的訊問不如實回答,或者所答與法官了解到的案情不符,法官則可以用刑逼取。
漢代的質證程序已趨于規范化。漢律對原、被告及證人的質證行為作出了法律規定,他們必須如實舉證,否則將承擔法律責任。前文已敘述了《二年律令·具律》中關于“證不言情”的法律規定,此外,漢代法律中還有一條未署律名的規定:
證財物故不以實,臧(贓)五百以上,辭已定,滿三日而不更言請(情)者,以辭所出入罪入罪。
意為在陳述案件事實時故意不如實提供財物數目,案件贓值達到五百錢以上者,如果供述后滿三日不更正并說出實情,則以其供述所出入之罪反及其身。這是漢代的一項審訊制度,按其性質應當屬于漢代《囚》律。在漢簡中,凡記錄審問案件的簡牘幾乎都有這條法律規定。現將所掌握簡牘中的這類律文抄錄一部分如下:
《居延新簡》:
“□辭已定,滿三日□。”(E·P·T5:111)
“□故不以實,臧(贓)五百十以上令辨告。”(E·P·T51:290)
“賈而買賣而不言證財物故不以實臧(贓)二五百□。”(E·P·T54:9)
“□三日而不更言請(情)書律辨告。乃驗問……”(E·P·T51:228)
“□市券一。先以證財物故不以實。”(E·P·T51:509)
“□先以證財物不以實律辯……”(E·P·T53:181)
“而不更言請(情)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乃爰書驗問恭辭曰上造居延臨仁里年二十八歲……”(E·P·F22:330)
“□□案,不□更言,以辭所出內(納)罪人。”(E·P·W13)
“建武四年三月壬午朔丁酉,萬歲候長憲□□燧·謹召詣治所。先以證縣官城樓守衙□而不更言請(情),辭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E·P·F22:328)以上所錄簡文,有的是該律文的節錄,如“證財物故不以實”;有的是該律文的殘篇,如“□辭已定,滿三日□。”
以上簡文中的“贓五百以上”、“贓二百五十以上”、“縣官城樓守衙”等語,不是這條律文的組成部分,而是審判官問案時,根據審問案情的需要引用的有關令文[6]。
經由上述論證可知,質證是整個刑事案件審判的核心環節。原、被告及證人三方之間對案件事實及證據進行質辯,法官則對案件疑點及不明之處反復查問,必要時不惜用刑逼供,直至主觀性證據與客觀性證據印證吻合,使得是非分明、事實大白,為案件最終的決斷提供充足的理由。
(二)據證鞫、判
1.鞫鞫,亦作鞠,史籍對其多有注釋。如《尚書·呂刑》:“輸而孚。”傳:“謂上其鞫劾文辭。”疏:“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周禮·秋官·小司寇》:“讀書則用法。”注引:“鄭司農云:‘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疏:“鞫謂劾囚之要辭,行刑之時,讀已乃論其罪也。”《漢書·刑法志》:“今遣廷史與郡鞫。”如淳注:“以囚辭決獄事為鞫。”李奇注:“鞫,窮也,獄事竟窮也。”《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新畤侯趙弟,坐為太常鞫獄不實。”如淳注:“鞫者以其辭決罪也。”以上所釋“鞫”,核心含義為“窮”,即“窮竟其事”。
質證結束之后,法官就需要對案件事實作出歸納總結,這一環節在漢代被稱為鞫。如張建國先生所言:“鞫是審判人員對案件調查的結果,也就是對審理得出的犯罪的過程與事實加以簡單的歸納總結”[7]其在程序中處于質證結束之后,判決作出之前的階段。《尚書》卷十九《呂刑》正義:“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
《奏讞書》所記載的秦漢審判案例,印證了“鞫”的存在及其性質。試例如下:
鞫之:媚故點婢,楚時亡,降為漢,不書名數,點得,占數,復婢,賣祿所,媚去亡,年四十歲,得,皆審。(簡14—15)
意為媚原是點的奴婢,楚時逃亡,到了漢朝后沒有申報戶籍。點逮住她,仍以奴婢上了戶籍,并將她賣給祿,后又逃跑被抓獲。現年四十歲。經審訊,均屬實。
鞫:闌送南,娶以為妻,與偕歸臨淄,未出關,得,審。(簡22—23)
意為闌負責遣送女子南去長安,其間娶南為妻。非法攜帶南返回臨淄。尚未出關即被查獲。經審訊屬實。
鞫之:武不當復為軍奴,弩告池,池以告與視捕武,武格斗,以劍擊傷視,視亦以劍刺傷捕武,審。(簡45—47)
意為被告武不應當再做軍的奴隸。軍以亡向校長池告發,根據控告,池帶領求盜視去逮捕武。武拒捕,用劍擊傷視,視回擊,用劍刺傷,并逮捕武。一切經審訊屬實。
鞫之:蒼賊殺人,信與謀,丙、贅捕蒼而縱之,審。(簡91)
意為蒼故意殺人,信主謀,丙、贅抓獲蒼后,又將其釋放,一切經審訊屬實。
通過上述案例不難發現,“鞫”的內容是法官對案件事實的認定,而非法律的認定,是事實判斷的過程。法官經由它作出法律認定,即依法作出最終的判決。其類似于當代刑事判決書中的“經法庭審理查明”部分。該程序內容也不包含原、被告行為的定性、法律條文的適用等內容。其中,結尾處的“審”或“皆審”,意味案件已調查清楚屬實,審判官吏對之確認。其類似于當代刑事判決書中的“以上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2.判決
判決是法官依據案件事實,對當事人的行為從法律上加以認定,是價值判斷的過程。在漢代,判決多以“論”的形式表現。張建國先生曾言:“‘論實際才相當于判決。”[7]陶安先生提出:“斷獄無疑是以‘論斷終結,但是更具體地說,‘論與‘斷是指怎么樣的程序呢?這一點恐怕還不太清楚。‘斷似乎不是文書用語,它僅作為描寫用語在法律條文以及相關注釋等出現。”[8]更確切地講,“論”是根據鞫之后的犯罪事實,尋找相適應的法律條文,對案件作出決斷。例如《興律》中所見“論”字:
縣道官所治死罪及過失、戲而殺人,獄已具,勿庸論,上獄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毋害吏復案,問(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丞謹錄,當論,乃告縣道官以從事。徹侯邑上在所郡守。(簡397)
簡文中“勿庸論”、“當論”之“論”即為“處置”、“定罪”之意。
《后漢書》李賢注說“決罪曰論”,就是說根據法律規定某罪應當給予何種處罰。《奏讞書》中的案例能夠印證此觀點。例如第四則案例,經過質證之后,確定了案件事實,并上報廷尉,廷尉據證依律判決為“娶亡人為妻論之”。簡文中的“論”顯然具有“定罪”或“以……定罪”之意。
分析《奏讞書》和其他文獻中記載的斷罪案例,發現漢代在案件事實認定后,則會據證依律令作出判決或者據證比附作出判決,以下對此兩種判罰方式進行分析:
第一,據證依律判決
在證據確鑿、事實清楚的基礎之上,案審官吏則需依律進行判決。漢代最基本的成文法是律與令,并且已對兩者作了初步的區分,《漢書·宣帝紀》言“令甲”,文穎注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律經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鹽鐵論》記載:“文學曰:春夏生長,圣人象而為令。秋冬殺藏,圣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9]在案件事實,即鞫部分認定確鑿,法律對其規定清楚時,法官必須依律令作出論斷。如《漢書·匡張孔馬傳》曰:“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即按照法令,犯法者都要依照犯法時的法律論處,在時間上有明確的界限。
《奏讞書》中記載的大多數案件都明示依據律令而作出論斷,試例如下:
令曰:諸無名數者,皆令自占書名數,令到縣道官,盈三十日,不自占書名數,皆耐為隸臣妾,錮,勿令以爵、賞免,舍匿者與同罪。以此當平。(簡65—67)
即按照“令”的處罰規定論處平。
律:盜贓值過六百六十錢,黥為城旦;令吏盜,當刑者刑,無得以爵減、免、贖,以此當恢。(簡72—73)
即依照“律”的處罰規定論處恢。
律:賊殺人,棄市。.以此當蒼。律:謀賊殺人,與賊同法。.以此當信。律:縱囚,與同罪。.以此當丙、贅。(簡93—95)
即分別于律的不同規定對蒼、信及丙與贅進行處罰。
可見,漢代法官在斷決案件時,如果法律對之有明確規定,則直接援引律或令作出判決。
第二,據證比附判決
在有法律明文規定時,法官應當據律斷罪。但是,如果遇到法律規定不明確,而案件又較為復雜、頗有爭議時,法官就要比照近似的法律條文或者依照判例作出決斷。
《奏讞書》中的案例記載:
蜀守讞:佐啟、主徒令史冰私使城旦環,為家作,告啟,啟詐簿曰治官府,疑罪。廷報:啟為偽書也。(簡54—55)
即左啟與令史冰役使服城旦刑的刑徒環為其做家務活,有人告發了啟。在刑徒勞役記錄簿中,啟謊稱該城旦環在修理官署。此案件中啟的行為在法律中沒有明文規定,地方官吏不知如何定罪,于是上讞,廷尉依照比附作出“為偽書”的判決。
另一種比附形式是依照判例進行決斷。依據成例作為依據斷案,這是由法律的本質屬性決定的。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準則,法律必須保持相對的穩定,否則人們將無所是從,這導致其在現實生活中的滯后性。為了克服法律的這一缺陷,使法官在斷決案件時能夠有據可依,中國古代形成了判例法的傳統,以此來彌補成文法的不足與僵硬。這在秦漢時期表現的尤為明顯,秦代的判例稱為“廷行事”,漢代則稱為“決事比”。
判例即判案成例,漢代較為普遍地適用判例斷絕案件。比的數量也較多,張湯上奏章治罪于顏異曰:“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比。” [10]自此便形成了“腹誹”之法的先例。《漢書·刑法志》記載,漢武帝時僅死罪決事比就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注“比,以例相比況也。”
作為判決“標本”的判例,是已經生效的案件中具有一定示范意義的典型性判例。該類案件一般較為復雜,或者頗有爭議。判例形成之后,法官在日后遇到類似的案件時,即可將其作為判決依據。《奏讞書》就是一部案例集,它所載的二十多則判例,大多數都具有典型的示范性功能。它當中本身也有引用判例作為定罪依據的案件。最為典型的是案例三,當中引用了先例:
人婢清助趙邯鄲城,已即亡,從兄趙地,以亡之諸侯論。今闌來送徙者,即誘南。.吏議:闌與清同類,當以從諸侯來誘論。(簡23—25)
因為對于本案被告行為的認定,缺乏法律的明文規定,審訊官便在案件的判決部分引入了這則決事比,認為對被告御史闌的定罪量刑可以參照此則判例適用。
甘肅武威磨嘴子18號漢墓出土的《王杖十簡》中也記錄了決事比的案例,如:
……高年受王杖……有敢妄譬、毆之者,比逆不道。
年七十受王杖者……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
這是兩則關于侵犯長者的法律規定,參照“逆不道”或“大逆不道”處罰。
在漢代,判例的條目繁多、體系龐雜,有些甚至彼此矛盾,很難掌度。對于輕重的比附,缺乏嚴格的法律規制,這就使得司法官吏的自由裁量權過大,以致“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 [5]這種隨意比附的流弊,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司法的公正性。
引《奏讞書》中記載的第五則案例“江陵余、丞驁敢讞案”為例,以圖表的形式歸納漢代刑事證據在起訴與審判環節的具體運用:
《奏讞書》江陵余、丞驁敢讞案中
述武曰:故軍奴。楚時去亡,降漢,書名數為民,不當為軍奴。視捕武,誠格斗,以劍擊傷視,它如池。(簡37—39)
視曰:以軍告,與池追捕武,武以劍格斗,擊傷視,視恐弗勝,誠以劍刺傷武而捕之,它如武。(簡39—40)
證人證言
軍曰:武故軍奴,楚時亡,見池亭西。以武當復為軍奴,即告池所,曰武軍奴,亡。告誠不審,它如池、武。(簡40—41)
詰問詰武:武雖不當受軍奴,視以告捕武,武宜聽視而后與吏辯是不當狀,乃格斗,以劍擊傷視,是賊傷人也。何解?(簡41—42)
武曰:自以非軍亡奴,毋罪,視捕武,心恚,誠以劍擊傷視,吏以為即賊傷人,存吏當罪,毋解。(簡43—44)
詰視:武非罪人也,視捕,以劍傷武,何解?(簡44)
視曰:軍告武亡奴,亡奴罪當捕,以告捕武,武格斗傷視,視恐弗勝,誠以劍刺傷捕武,毋它解。(簡45)[]質證
驗問
問武:士伍,年卅七歲,診如辭。(簡45)[]確認證據
據證鞫案[]鞫之:武不當復為軍奴,軍以亡弩告池,池以告與視捕武,武格斗,以劍擊傷視,視亦以劍刺傷捕武,審。(簡45—
漢代承繼了秦代的乞鞫制度,在案件作出判決之后,允許當事人及其親屬在遵照法律規定的前提下提出復審要求。經過乞鞫,啟動復審程序,上級司法官吏通過核實各項相關證據,重新審視案情,并作出復審處理決定。如果相關證據證明案件確屬冤、錯,法官會據證重新判決,并追究原判法官“審判不實”的責任。如果原判決準確,乞鞫者理由不成立,則其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漢代乞鞫制度較之秦代,進一步趨于規范化。《二年律令·具律》中對乞鞫制度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
罪人獄已決,自以罪不當,欲乞鞫者,許之。乞鞠不審,加罪一等;其欲復乞鞫,當刑者,刑乃聽之。死罪不得自乞鞫,其父、母、兄、姊、弟、夫、妻、子欲為乞鞫,許之。其不審,黥為城旦舂。年未盈十歲為乞鞫,勿聽。獄已決盈一歲,不得乞鞫。乞鞫者各辭在所縣道,縣道官令、長、丞謹聽,書其乞鞫,上獄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都吏所覆治,廷及郡各移旁近郡,御史、丞相所覆治移廷。(簡114—117)
這一規定就明確了乞鞫成立的前提條件、主體、提起的期限等。下面將此項法律規定展開分析,以便透徹了解漢代的乞鞫制度:
(一)乞鞫前提
“自以罪不當”,即已被判刑的罪犯自認為判決不當。這是古今通在的引發上訴制度的主觀心理狀態。它是行為人提起乞鞫的前提條件。
(二)乞鞫主體
即有資格向上級審判機關提出乞鞫的行為人。根據法律的規定有兩類:一為被判處刑罰的罪犯,其可以“自乞”,但被判死刑者除外;二為罪犯的親屬,包括其父、母、兄、姊、弟、夫、妻、子等人。同時,排除了未滿十歲兒童的乞鞫權。從以上《具律》的規定可以解讀到,被告人若被判死罪,其乞鞫權被剝奪,該權利可以由其親屬代替行使。《漢書·趙廣漢傳》記載了一則由親屬提出復審請求的案件:“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此案即是由蘇賢的父親提出復審請求,上級官吏下達重新審理案件,趙廣漢獲罪,后獲赦,被降一級俸祿。
《晉書·刑法志》記載了三國時魏國對該律文作出了修改,進一步限制了親屬的乞鞫權,“改漢舊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為了減輕斷獄程序上的瑣累,縮減了親屬的乞鞫權,被告人若被判處兩年以上刑的,就不許親屬為之乞鞫了。
(三)乞鞫期限
根據《具律》的規定,被告人或其親屬必須在判決結果作出一年之內提出乞鞫請求,超過此期限,則不得提出乞鞫請求。在《周禮·秋官·朝士》中已有關于聽審期限的記載:“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十三經注疏》注引鄭司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乞鞫期限的設定,一則在于督促行為人即時行使乞鞫權利,時間長久會導致相關證據的流失或難以確認,妨礙清楚認定案情;再則乞鞫拖沓時間過長,會造成案件的過度積壓,增加司法審判機關的壓力,耗費司法成本。
(四)對乞鞫“不審”所謂“審”,即“正確、確實”之意。如《法律答問》中載:“甲殺人,不覺。今甲病死已葬,人乃后告甲。甲殺人審。”(簡68)所以,“不審”即意為“不正確、不確實”。《二年律令·賊律》規定:“諸上書及有言也而謾,完為城旦舂。其誤不審,罰金四兩。”(簡12)又如《史記》所載“趙高案治李斯”,秦二世“恐其不審”,就派遣使者前往案驗。那么,“告不審”就指不正確的告訴、告發。《法律答問》中對此有定義:“甲告乙盜牛。今乙盜羊,不盜牛。問可(何)論?為告不審。”(簡47)此外,由官吏所為的虛假告發,稱為“劾人不審”。如《懸泉漢簡》中的囚律佚文:“囚律。劾人不審為失,以其贖半論之。”(簡Ⅰ0112:1)若官吏故意進行虛假告發,則構成“不直”之罪。如《二年律令·具律》規定:“劾人不審為失,其輕罪也而故以重罪劾之,為不直。”(簡112) 的處罰
如果是被告人請求復審的訴訟理由不成立,則對其“駕(加)罪一等”;如果是親屬提出復審的理由不成立,則會被“黥為城旦舂”。漢代通過此法律規定,以防止乞鞫的隨意性,減少訴訟的耗費與拖累。
(五)乞鞫的管轄
漢律對乞鞫的管轄主體及處理程序也作出了明確的規定。乞鞫者應當各到其居住地所在的縣、道提交上訴狀。縣道之令、長、丞應謹慎受理,將乞鞫的內容記錄下來,并將獄案上呈其所轄的二千石官,二千石官將案件交給都吏負責再審。都吏對案件進行復審之后,廷尉和郡以文書的形式將審判結果送到附近的郡;御史、丞相復審的案件,其結果應以文書的形式送達廷尉。
經過對漢代律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漢代在承繼秦代乞鞫制度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在法律上對之進行規制。從制度上而言,乞鞫之制確實能夠對司法審判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減少冤滯案件的發生,保障罪犯的合法權益。漢代國祚長久,一度興盛,與此有益的司法監督制度關聯甚大。但是,到東漢末期,國事混亂,動蕩不安,乞鞫制度名存實亡。正如《潛夫論·述赦》所言:
奸猾之黨,……令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徒,下乃論免,而被冤之家,乃甫當乞鞫告故以信直,亦無益于死亡矣。
王符對當時妄行刑辟、濫施赦行的做法進行抨擊:往往被冤之家剛剛“乞鞫”,而害人者即被“論免”,這對于蒙冤死去之人而言,就沒有多大意義了。從中反映了,當時的司法活動已遭到嚴重破壞,乞鞫制度存在的現實價值已甚微。
現將該案例歸納為圖表的形式,以便更加詳細、透徹地對乞鞫案件進行分析,具體了解漢代刑事證據在再審案件各環節中的運用情況:
四、研究新見
通過對大量漢代簡牘資料的分析考查,不難發現,漢代在訴訟程序中已經確立了較為完善的證據運用制度。漢代刑事證據的運用制度具有雙重屬性:既有客觀性的方面,也有主觀性的傾向,是一種綜合性的證據運用制度。所謂證據的客觀性,是指通常在判斷案情過程中,重制度、重勘驗、重原始證據的客觀效力,主張據證定案的傾向;所謂的證據主觀性,主要指先入為主或因政治權力之爭,或因經濟利益之爭,或因案情復雜、證據不足時偏離證據的客觀方面,主觀認定,甚至羅織罪名、偽造證據,動用刑訊手段陷人于罪的傾向;其綜合性即是指將證據的客觀性與主觀性相結合,來判斷現有證據是否合法有效,以及在案情認定上所具有的證明力的大小等。
以往對古代刑事證據制度的研究,偏重其一個方面,即“口供至上”,強調傳統刑事證據的主觀性特征。陳兵指出,我國古代特別重視口供的作用,持“斷罪必取輸服供詞”與“無供不錄案”的斷罪原則,所以將口供稱為“證據之王”,直至清朝仍是如此。(參見:陳兵.解讀現代“刑訊逼供”現象的根本原因——從我國古代拷訊制度合法化層面人手[J].江西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3,(4).)劉顯鵬也指明,中國傳統訴訟的特殊之處在于極為重視被告人口供的“口供主義”,在中國傳統的訴訟當中,被告人口供是最重要的證據,沒有被告人供認,一般不能定罪。其他證據的證明力都比不上口供高,人證、物證、書證只是輔助證據,而且必須在具有口供的情況下方能發揮作用,如無口供,僅憑其他證據不能定案。相反,如果有口供,即使沒有其他證據,也可定案。(參見:劉顯鵬.中國古代口供制度粗探[J].國土資源高等職業教育研究,2004,(3).) 這樣的認識,雖有一定的道理,但卻值得商榷。不可否認,“口供”是漢代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據,稱其為“證據之王”也實不為過。但是,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漢代的法制文明取得了相當的成就,運用于訴訟之中的證據制度,尤其是刑事證據制度獲得了突出發展,在刑事證據理論上表現出了較為明顯的客觀性傾向。在案件調查中注意對物證、書證及證人證言的采集,而且還注重錄制勘驗報告;在審判的質證環節,也強調使用客觀性證據來印證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真實性。最終達到確定性定案的追求。正如滋賀秀三所指出的,“總而言之,把本人的供述,與證據以及一切情況都加以對照并進行總和的考慮,供述似乎有不充足不正確的地方時又得重新進行反復的詰問,這種程序就是那樣充滿苦澀的調查過程。” [11]在這里,他雖未專指漢代的證據應用規則,但卻是在闡釋中國古代證據應用的普遍規則,即重視使用其他證據對口供進行驗證。這是經過對漢簡刑事證據材料的全面研究之后,得出的研究新見。
五、結語
綜括上述,漢簡較為全面地為我們展示了漢代刑事證據在訴訟程序中的運用制度。使我們了解到,漢代刑事證據規則已趨于規范化與制度化。在提起訴訟環節注意對物證、書證及證人證言的采集,而且還注重錄制勘驗報告;在審判的質證環節,強調使用物證、書證等客觀性證據來印證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真實性;在上訴復審環節重視重新審核證據,查驗案件事實。從提起訴訟,到勘驗取證,再到庭審判決,直至乞鞫復審,證據的運用貫穿于訴訟活動的全過程,發揮著支配與主導作用。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漢代尚處于我國法制建設的早期,其法律制度的粗糙與落后是顯而易見的,訴訟審判制度有待健全。“口供至上”依然是核心的證據規則,司法實踐中審訊方式的隨意性也較大,為了獲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辭,往往使用酷刑。而且,對原告和證人動用刑具也甚為常見,且為制度所容。血肉橫飛、哀嚎不盡之中導致冤獄叢生。這有奴隸制殘余思想影響的因素,但更主要是緣于主觀唯心主義的取證觀念。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筆者認為,研究漢代刑事證據的最大意義在于,它是中國本土優秀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歷史傳承性是顯而易見的,對當前國情民俗的適應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通過對漢代刑事證據的研究,可以達到追本溯源的功效。因而,考察漢代刑事證據的制度化、系統化的嘗試與成敗得失,對當代中國刑事證據制度的完善意義深遠。誠如博登海默所言,“作為使松散的社會結構緊緊裹在一起的粘和物,法律必須巧妙地將過去與現在勾連起來,同時又不忽視未來的迫切要求。” [12]漢代的證據制度作為法學或法律的積累成果,不失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ML
參考文獻:
[1]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照.居延漢簡釋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155.
[2]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92.
[3]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352.
[4]沈家本.漢律摭遺[G]//鄧經元,駢宇騫,點校. 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1372.
[5]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2.
[6]高恒.秦漢簡牘中法制文書輯考[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151.
[7]張建國.漢簡《奏讞書》和秦漢刑事訴訟程序初探[J].中外法學,1997,(2):55-56.
[8]陶安.試探“斷獄、“聽訟”與“訴訟”之別[G]//張中秋.社理性與智慧:中國法律傳統再探討.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2008:70.
[9]馬非百.鹽鐵論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4.
[10]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4:2731.
[11]滋賀秀三.中國法文化的考察——以訴訟的形態為素材[J].比較法研究,1988,(3):22.
[12]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