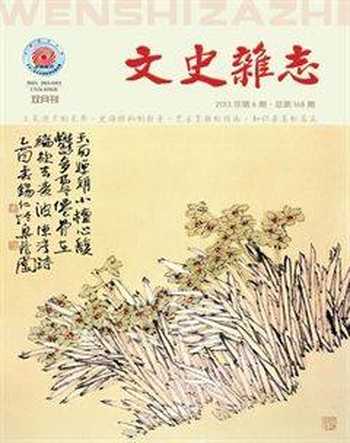談談張籍《節婦吟》的詩題、創作背景及母本
劉安
唐張籍有《節婦吟》一首,謹錄如下: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
感君纏綿意,系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一、詩題是《節婦吟》還是《還珠吟》?
一次,聽一位文學院教授講張籍《節婦吟》,當講到最后一句“恨不相逢未嫁時”時,筆者忽然有了一個疑問:既然是節婦,為何要對丈夫以外的另一個男子表達如此強烈的曖昧之情?翻檢傅增湘藏宋本《樂府詩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第1 版影印本)及明趙均小宛堂本覆宋本《玉臺新詠》(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此詩最后皆作“何不相逢未嫁時”。
“何”字,略表遺憾,而“恨”字,表示非常后悔。僅從兩字意思輕重來看,用“何”字更好些;但作深一步分析,卻發現不是那么簡單。通讀全詩,作者想要表達的是一位有夫之婦委婉拒絕第三者的追求,其情纏綿悱惻,婉轉留戀,欲說還休。雖然最后與之決絕,可是前面不僅將男子所贈之明珠系在自己紅羅襦上,又贊男子用心如日月,而且還男子明珠時雙淚暗垂滴,最后竟然后悔意生——何(恨)不相逢未嫁時。如此情愫,號稱“節婦”,不也惑乎?后來翻閱宋代文獻,見劉克莊《后村詩話》(新集卷三)稱其為“還珠吟”。筆者認為,若以此為題目,此詩內容與形式就更貼切了。
二、此詩是寄“李師道”還是“李師古”?
《孟子·萬章下》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認為,文學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時代背景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論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寫作的時代背景,才能客觀地正確理解和把握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中說:“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知人論世,應當是“論世”第一,“知人”第二;進行文學批評,也必須知人論世,才能對作品作出正確的評價。筆者查閱資料,了解到張籍此詩寫于永貞元年(805年)。宋洪邁《容齋三筆》(卷六)之“張籍陳無己詩”載“張籍在它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卻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以寄之。”宋姚鉉編《唐文萃》(卷十二)、宋計有功編著《唐詩紀事》題目后有“寄東平李司空”,而明正德十年(1515年)劉成德刻本《唐張司業詩集》(以下簡稱“劉本”),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陸貽典影宋抄本《張司業詩集》(以下簡稱陸本)題目后有“寄東平李司空師道”。
這里涉及到兩個人,即李師古與李師道。到底征召張籍的李司空是誰,要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張籍辭書幣事在何時。在各種材料中,最早關于張籍“辭聘”的文字為姚崇曾孫姚合《贈張籍太祝》一詩,其中有“甘貧辭聘幣,依選受官資”詩句。而卞孝營《張籍簡譜》記載,元和元年(806年),張籍依選調補太常寺太祝,由此可知“辭聘”時間應為元和元年張籍調補太祝或太祝秩滿而待授它官之時。而查閱史書,發現在這個時候李師道并沒有擔任司空一職。《舊唐書·李正己列傳附李師道》載:“(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加(李)師道司空……”而元和十一年,張籍在韓愈舉薦下轉任國子監助教,故推論張籍所辭司空并不是李師道。
那么李師古又是何人,查閱《舊唐書·李正己列傳》,發現李師古是李師道的異母兄,二人均為鄆州長史李納之子。同書載“師古雖外奉朝命,而嘗畜侵軼之謀,招集亡命,必厚養之,其得罪于朝而逃詣師古者,因即用之”;巧的是,李師古也擔任過司空。《舊唐書·順宗本紀憲宗本紀(上)》載:“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戊寅,以韋皋兼檢校太尉,李師古、劉濟兼檢校司空……元和元年潤六月壬子朔,淄青李師古卒。”而貞元二十一年(即永貞元年),張籍正在家“依選”,故而在時間上吻合。臺灣學者羅聯添在《張籍年譜·貞元二十一年》中有“(張籍)作《節婦吟》詩寄鄆州李師古,疑在本年”也可為明證。
三、母本來自《羽林郎》還是《陌上桑》?
劉克莊在《后村詩話·前集》卷一中指出“張籍《還珠吟》為世所稱,然古樂府有《羽林郎》一篇,后漢辛延年所作……(張)籍詩本此,然青勝于藍”。《羽林郎》講述酒家女胡姬不畏強暴,敢于同權貴豪奴調戲作斗爭的故事。筆者認為若要追溯《節婦吟》母本,恐怕還是《陌上桑》更吻合些。
《陌上桑》講述的是一個叫秦羅敷的美麗女子拒絕太守追求的事。具體分析兩詩內容,《節》中有“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陌》中有“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節》中有“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里”,《陌》中有“東方千余騎,夫婿居上頭……”,洋洋灑灑,一共十六句,將自己的丈夫狠狠地夸獎了一番。兩位女主人公的差別之處在于,秦羅敷根本沒有正眼看一眼太守,果斷拒絕;而張籍詩中的節婦在贊其丈夫之時,又感慨他人“用心如日月”,繼而還珠淚流,甚至“恨不相逢未嫁時”。
至于張籍筆下之“節婦”為何對丈夫以外的男子如此婉戀,結合張籍創作此詩的背景就不難理解。張籍寫此詩是為辭謝一頗有權力,能致人生死的地方軍閥,當然不能像秦羅敷辭謝使君那樣決絕,故而不能不婉轉其辭。
實際上,以夫妻或男女愛情關系比擬君臣以及朋友、師生等其他社會關系,乃是我國古典詩歌中從《楚辭》就開始出現并在其后得到發展的一種傳統表現手法。《唐詩三百首》里收錄的朱慶馀《近試上張水部》也是用這種手法寫的,全詩云: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
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唐代應進士科舉的士子有向名人行卷的風氣,以希求其稱揚和介紹于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朱慶馀此詩投贈的對象,正是水部郎中的張籍。張籍當時以擅長文學而又樂于提拔后進而與韓愈齊名。朱慶馀平日向他行卷,已經得到他的賞識,臨到要考試了,還怕自己的作品不一定符合主考的要求,因此以新婦自比,以新郎比張,以公婆比主考,寫下了這首詩,征求張籍的意見。
張籍在《酬朱慶馀》詩中答道:“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足時人貴,一曲菱歌敵萬金。”張籍把朱氏比作越州鏡湖的采菱女,不僅長得艷麗動人,而且有絕妙的歌喉,這是身著貴重絲綢的其她越女所不能比的。文人相重,酬答俱妙,千古佳話,流譽詩壇。
作者單位:宜賓市第一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