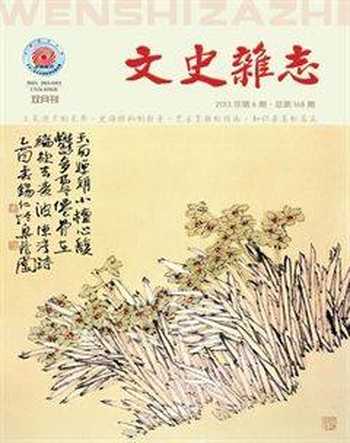披沙揀金 鉤深致遠
曉強
2012年12月,巴蜀書社出版了由胡開全任主編、蘇東來任副主編的《成都龍泉驛百年契約文書(1754—1949)》。該書展示了成都市龍泉驛區檔案館所珍藏的293件契約文書,時間跨度達195年(1754年至1949年),包括土地買賣送討契約、土地房屋租佃和錢財借貸契約以及“分關”繼承文書等。全書以本色影印、標點轉錄并適當注釋的方式,準確地再現了清中葉以降至民國龍泉驛地區的倫理與道德規范、經濟與土地關系、社會與民風嬗變的基本狀況,為研究那一時期的鄉土中國和客家文化提供了一批寶貴資料。
在此基礎上,由成都市龍泉驛區人民政府、中共成都市龍泉驛區委宣傳部主辦,成都市龍泉驛區檔案局(館)、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成都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承辦的成都龍泉驛“百年契約文化”學術交流座談會于2013年8月29日—30日在龍泉驛天倫國際酒店隆重舉行。會議學術交流及評審由江玉祥(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陳世松(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謝桃坊(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王川(四川師范大學教授)、鄧經武(成都大學教授)主持,來自四川大學、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四川師范大學、成都大學、中山大學、臺灣國立聯合大學以及龍泉驛本土的20余名學者提交了論文并作了精彩發言。現將會議主要學術成果綜述如下。
一、誠信至上,孝感天下 ——契約反映的倫理與道德規范
倫理,是指人與人相處的各種道德準則;道德的涵義與之相近,但外延更寬泛。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看法,倫理與道德規范和原則是依據社會的經濟關系以及它們和其他社會意識形態的聯系而發生、發展的。它們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和社會輿論的力量,使人們逐漸形成一定的信念、習慣、傳統,用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調整個人和社會以及人們彼此間的關系。成都龍泉驛百年契約文化的一個巨大閃光點,就是貫穿其間的誠信精神和孝道觀念。這是中國各族人民在五千年來的文明進程中所形成的優秀傳統。它在龍泉驛東山客家人的日常生產、生活中得到堅實印證。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王定璋先生指出,龍泉驛契約文書中的土地買賣契約均書寫清楚,不留后患,且對不誠信行為有嚴格的懲罰條款,以此約束買賣雙方。其講誠信與給懲處相結合,彰顯出契約的生命力。
四川師范大學教授鄧紹輝先生認為,龍泉驛契約文書教化鄉民誠實守信。它們在要求土地買賣雙方各自須享受一定權利并承擔相應義務的同時,又強調恪守各種承諾約定。當地官府則對此加以文本審查和制度管理,將整個活動納入可管控的正常軌道。這便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作為鄉規民約的契約文書的教化功能,促使契約雙方信守承諾。否則,將會受到來自官方或民間的處罰。鄧先生分析道,契約文書中的70件關于土地買賣的契約,除土地買賣交易雙方外,還出現所謂中人、中證、在場人、族人、公職人員等證明人。這種中人制度,鄉約性色彩較為濃厚,帶有民間法律的意味。而在同期的國家法律或民間法律中,涉及土地買賣時,卻缺失中人擔保這一條款。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講,龍泉驛契約文書對國家法律作了補充和完善。它們所體現出的公開性、公正性、懲罰性原則,為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提供了借鑒。
四川師范大學教授湯君先生在對敦煌、黑水城、龍泉驛文獻中的土地買賣契約進行比較研究后提出,龍泉驛的土地買賣契約一律都是杜賣契,即絕賣契(一次性賣斷,永不贖取)。它比敦煌、黑水城的契約在內容與形式上都更為嚴謹,附有官方尾契,最大可能地保證了契約文書的嚴密性、合法性;其杜賣的形式和現代契約很接近。此外,龍泉驛契約又頗富人情味,散溢出濃濃的生活原味道——這是被現代契約所拋棄的。
臺灣國立聯合大學副教授劉煥云博士在對《成都龍泉驛百年契約文書》與臺灣《苑里地區古文書集》作了一番比較后,指出海峽兩岸契約文書具有一些共同點:1.它們均以法律文書的形式進入人們世俗社會與日常生活的行為系統,講究“空口無憑,立字為據”,具有公開性性質,可以杜絕任何文字陷阱或作弊情事。2.立契人都是“雙方甘愿,無強迫之事”,使契約成為舊社會中維持社會秩序與社會和諧的理性依據,具有科學發展精神。3.兩岸契約均顯示出倫理性,規范人們的思想行為,推動社會和諧發展。
四川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員蘇東來先生考察了龍泉驛契約文書中體現出的孝道思想,認為其在產業處置中堅持敬長尊老的傳統;在產業來源上能追思先祖,溯往感恩;遇到產業爭議則奉祖先為大,如堅守“賣產不賣墳,賣地不賣祖”的原則。孝道思想還表現在送討買賣陰地契約中——以死者為尊;即便自己受盡委屈,也要竭盡全力盡孝。契約中的孝行,在無形中構建了由自身到父母再到先祖的孝道體系圖;這必然也會為后世子孫所延續,從而在產權轉移中完成了由近及遠的家族孝道的傳遞模式與脈絡。
二、租佃非罪,生財有道 ——契約反映的經濟與土地關系
傳統社會的土地關系主要指封建土地所有制,其中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租佃制度。關于它的性質,按一般解釋,即所謂“封建地主占有土地,把土地租給(或分給)農民耕種,使他們世代束縛在小塊土地上,并以地租的形式殘酷地剝削農民”。“在舊中國,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極為殘酷,地租往往占收獲量的一半或一半以上。這是農民生活貧困和農業生產停滯的根本原因。”(《辭海·經濟分冊》,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頁)這些看法,無疑給租佃制度打上原罪的烙印。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謝桃坊先生在深入研究了《成都龍泉驛百年契約文書》提供的一批龍泉驛土地租佃契約后指出,對于租佃制度在歷史上是否具有合理性,就佃農方面而言,應當以是否能夠促進佃農的再生產為考察標準。舊時龍泉驛關于土地租佃的實際情況,可以回答這個問題。謝先生認為,若以一戶五口之家(其中全勞力一個,半勞力兩個)租佃十畝土地為例,只要合理安排,勤勞儉樸,就完全可以養活全家且有剩余而擴大再生產并最終致富。其可能導致貧困的因素,應是勞動力弱,缺乏肥料,不善耕種,產量低下。謝先生說,農民經濟地位的變化,貧富的分化,并非租押造成的,而是遵循著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而馬克思也沒有說過地租是殘酷剝削農民的方式。實際上,租佃制度在封建社會經濟中是有利于農業經濟發展的。龍泉驛的許多客家人的入蜀祖先皆是以佃耕土地發家創業的。例如洪河鄉柳樹村馮氏,圣燈鄉陳氏,合興鄉張氏,保和鄉勝利村謝氏,石靈鄉范氏,龍泉鎮萬氏,義和鄉廖氏。在土地租佃制度下,地主僅占有佃農部分剩余價值;佃農有較多的剩余勞動和剩余時間,因而有自己積累剩余價值的可能性。佃農創造剩余價值,轉化為向社會不斷提供農產品,其經濟活動成為封建社會經濟存在與發展的重要基礎。
成都龍泉驛檔案館館員胡開全先生則通過對蘇氏家族從廣東移民到龍泉驛后的經濟情況的剖析,提出其之所以從一個佃戶在近二百年間發展成地方望族,首先是其家族人丁興旺且連續性強;其次是家族關鍵人物的決策正確,發展方式科學,并為家族世代所堅守;再次是產業繼承人健康長壽;最后是樹立健康的家族形象,對產業和文教功名始終保持不斷進取的精神。胡先生特別指出蘇氏家族耕讀傳家的傳統和崇文重教的氣質贏得了當地人民的尊敬和信任。
成都大學教授譚平先生也注意到蘇氏家族在當地的影響,認為蘇家在發家以后能體恤貧弱階層,表現出一定的慈善、關愛行為。他進而指出,當今富裕人群應像蘇氏家族那樣“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用之有義”,堅定地愛祖國、愛家鄉、愛同胞,從而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三、村民自治,女兒自強 ——契約反映的社會與民風嬗變
從社會學角度講,中國傳統社會其實乃是以家族為中心的宗法社會,家庭—家族是宗法社會的基本細胞,也是宗法制度賴以維系的基礎。許多學者通過對龍泉驛契約文書的條分縷析,認識到契約所反映的清乾隆中葉以來的近二百年間,正是大家庭—家族不斷分化解體、宗法社會漸趨式微的時期。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陳世松先生認為,舊時龍泉驛大家庭的“別籍異財”,表現出中國鄉村社會擺脫困境的一般現象——家庭因為人口負荷過重、膨脹壓強過大,超出了家庭經濟的承受能力而自救。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屈小強先生指出,龍泉驛大家庭的“別籍異財,除了近代商品經濟的影響之外,還受到蜀地千百年來的傳統或風俗的影響(《隋書·地理志上》講蜀地“小人薄于情義,父子率多異居”;李調元《童山文集·賣田說》亦云“蜀俗好分”)。陳世松先生也有相似看法。他還說,正是經過一次次的“別籍異財”,使作為移民社會的四川宗族規模與實力不斷遞減,以至罕有能與江南和嶺南地區的強大宗族相抗衡者。中山大學博士生郭廣輝先生進而提出,當移民以家庭為單位遷入成都后,伴隨著人口增加與不斷分家導致的產權變更,使得成都地區宗族居住形態呈現出分散特征,形成美國學者施堅雅所說的“分散型村莊”模式。至于今天成都平原的鄉村景觀——很多林盤變成超過數十戶的聚居型村莊,以新都區石板灘土城村土城小區為代表——的形成,也完全是產權變更的作用。
成都大學教授鄧經武先生還認為,龍泉驛土地房產買賣的契約,使我們了解到舊時龍泉驛鄉間淳樸息爭的民風,許多問題可自行協商解決,這便極大地減輕了國家行政運行的成本。這種“村民自治”,可為當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提供歷史經驗。
胡開全先生則指出,龍泉驛契約文書表明,當時土地所有者的稅賦負擔并不重。而地方政府能在比較低的稅率下維持運轉,則與政府機構簡單,開支不大有關,如華陽縣鄉鎮公事人員連鄉長在內只有13人,簡陽縣洛帶鄉的公事人員(包括工友)則為12人。
一些學者還注意到龍泉驛契約文書中的女性地位的獨特性。成都大學副教授張曉霞女士在對龍泉驛與重慶巴縣兩地契約檔案進行比較后認為,盡管清代至民國的女性總體地位還很低下,但是,仍有少數婦女能夠全面地參與契約的訂立,包括獨立立契賣出與買進產業、獨立立約自主婚嫁。這說明當時四川已有部分女性在家庭和社會生活中擁有一定權利。
屈小強先生亦提出龍泉驛契約文書中的一件關于女子(或是出嫁女子)與男兒同享家庭財產繼承權的“分關”(指分家析產文書)比較特異。因為從中國共產黨于1928年提出為農村婦女爭取包括繼承權在內的正當權利起,直至90年代初葉,在實踐中還有相當多人不贊成出嫁女子與兄弟平分娘家財產。于是,這份產生于國民政府治下的龍泉驛鄉間的男女平分家產的文書,便有了突破性意義。它應是具有數千年傳統的中國宗族制度的森嚴高墻迅速坍塌、宗法社會走向末日的一個令人鼓舞的象征。
作者單位: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