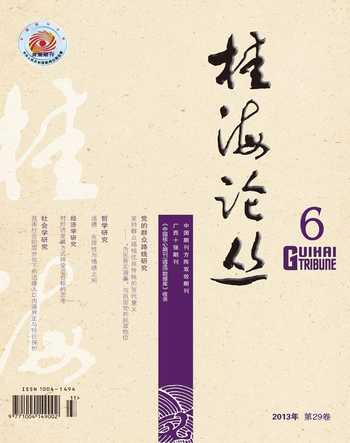道德:在理性與情感之間
甘紹平
摘 要:在西方倫理學發展史上,道德究竟是以理性還是以情感為基礎,就此而言存在著理性倫理派和情感倫理派之間針鋒相對的兩種立場。文章在闡釋和分析了以霍布斯和休謨為代表的契約論理性倫理和以叔本華為代表的同情倫理的基礎上,論證了從根本上說情感與理性在倫理道德中并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我們道德決斷中交織在一起共同作用的因素。人之所以需要守德,與人既是由理性驅動、也是由情感引導的特性相關,因而應從理性合作和情感驅動兩個方面,才能厘清人類服從道德要求的動力機制。
關鍵詞:理性;情感;契約論;同情;道德
中圖分類號:B8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3)06-0025-06
在西方倫理學發展史上,道德究竟是以理性還是以情感為基礎,就此而言存在著針鋒相對的兩種立場。認定道德以理性為基礎者,被統稱為理性倫理派,以霍布斯、休謨的契約論倫理學為代表。認定道德以情感為基礎者,被劃歸為情感倫理派,以叔本華的同情倫理為集中體現。而對理性的信仰則大體上支配了叔本華以前的西方哲學界。
一
在理性哲學家們看來,同情只屬于原始的情感,并不能發揮什么重要的作用。柏拉圖強調情感應受控于理性的引導。斯多葛派則因同情與理性的主導觀念不符而對同情持否定的態度。在近代對理性的信仰又由于霍布斯開創的契約論倫理學而獲得了新的邏輯支點。在霍布斯的啟示下,人們相信可以通過對人性的理性洞察,運用理性設計制度的方式來避免由人性之惡所導致的沖突,最終使每個人的長遠利益都得到保障。這就是說,人們完全可以通過對自身本性、自身利益和社會秩序之必要性的理性認知而成為一種(守法意義上的)道德公民,從而實現社會的安寧和國家的繁榮。“這樣一種有關理性的力量及其與道德關系的樂觀主義的見解,在啟蒙了的同代人中獲得了超出英國的巨大反響,并且影響到了現代的國家理念”①。近代哲學中的斯賓諾莎和法國唯物主義,也由于認定同情遠離于理性論證而視其為無用的、甚至有害的。康德當然也不相信同情心對于行為主體的行為具有多大的驅動性力量。需要一提的是,盡管康德也屬于理性倫理派,但他的理性道德與契約論代表的經典的理性道德差別巨大。
把道德奠立于理性之基礎上的所謂理性倫理派的最經典、最有影響者,當數契約論倫理學。契約論倫理學的提出則要首先歸功于近代的霍布斯。他設想了一種自然狀態,由于該狀態中沒有道德規則,沒有行為限制,人人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結果是大家相互傷害,誰也無法過好。為了避免這種結局,人們建構了道德規范,禁止所有的人互相欺騙、偷竊、傷害和殘殺。雖然這些道德規范對每個人的自由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一種安定的社會生活卻由此得到了保障。“當我們設想,個體遵守其規則,則他們雖不能達到完全沒有沖突地相處(這一點由于資源缺乏而被排除),但他們卻擁有可能,和平地調節其沖突并以此方式平衡地享受其勞動成果”②。可見,在霍布斯這里,道德起源于維護人們的基本利益免受他人的侵害,“道德的決定性的理由在于,避免惡行和損害”③,“人們應當道德,因為否則的話別人就會受到傷害”④。于是,在為何要道德或者道德究竟起源于何種理由這一問題上,霍布斯給出了維護利益免受侵害的解答,也就是說,禁止傷害構成了所謂霍布斯式的答案。霍布斯的觀點非常鮮明:“就基本道德而言,出于對他人的好處而行動并非首要是指,做對他有用之事,而是放棄損害他人之事”⑤。拜耶茨(Kurt Bayertz)認為,霍布斯式的答案集中體現了道德這個詞的狹窄含義。“這個詞的狹義便是指對人類起源發生學意義上的傷害的禁止。許多人會覺得這一點不夠。但在一種后宗教的、后形而上學的、多元的世界里,我們無法針對每位主體令人信服地論證,為何應借由道德這一詞寬泛的意義來限制其行為自由”⑥。
與霍布斯認定道德起源于維護人們的基本利益免受他人的侵害的解答不同,在契約論倫理學內部,還有休謨式的有關為何要道德這一問題的答案。休謨認定道德起源于對人們的基本利益的增進,而并非是像霍布斯所理解的那樣僅僅在于對傷害的禁止。這種對基本利益的增進是通過相互的理性的社會合作得以實現的。亞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每個人從本性上講都生活在一個集體之中”⑦,休謨也認為,“一種完全的孤獨性或許是能夠給予我們的最嚴重的懲罰”⑧。但是,即便是對集體的需求屬于人的本性,我們仍然需要一個與之獨立的理由,來說明社會合作對人類的益處。其實這種理由不勝枚舉。“因為顯而易見的是合作性的聯合對于為生存的抗爭構成了一種優勢:聯合使共同防御外在的危險成為可能,并且通過勞動分工的可能性給所有參與者帶來益處”⑨。休謨特別強調社會合作在對基本利益的增進上發揮的作用,在他看來,“人類個體擁有僅靠自己力量所無法實現的需求。通過相互的合作他們可以共同創造他們所需的、作為單個者卻無法生產的產品”⑩。休謨的例子是兩位農民收糧,兩人都難以獨立完成收割自己的。于是便合作,第一天共同收一個人的,第二天共同收另一個人的。這個合作過程順利完成的前提,是守約。“如果潛在的合作方沒有情感上的聯系,則他們便需要有一種特殊的理由,來相互信任并基于此而能夠依時而合作”11。這個特殊的理由,就是守約。因而體現在守約上的道德是社會合作的基礎與前提。沒有道德就沒有合作。一般而言,社會合作能夠給與合作雙方帶來從獨自而為中無法獲得的好處。但是,合作的各方也會擔心,如果對方不講道德,則自己的合作行為便意味著吃虧受損。這種情況特別體現在一次性的合作經歷。當然,如果從長期來看,從重復的合作活動的角度來看,則道德“生存”的幾率就會大大增加。“因為如果合作伙伴是同一個人且合作是重復進行的,如果參與者數量眾多,則可能的合作贏利就明顯增大,從長期來看會勝于損失的風險”12。《合作的進化》一書的作者阿克塞爾羅德(Robert Axelrod)也持同樣的觀點,“當盡可能多的回合得到博弈,并且這一組人馬相互間實施了足夠量的互動,在這種條件下,阿克塞爾羅德認為,我們就可以確信,合作在一個沒有中心統治總部的情況下才能夠在一個自私主義者的世界里出現”13。總之,只要合作是重復性的,只要參與者數量眾多,則合作還是肯定會有利于當事人自身利益的增進,即便是他無法排除遇到無道德者的風險。而合作所帶來的利益,又定能使無道德者發現自己原先的行為得不償失,他或許可以從一次不合作中獲利,但無法持續。“一位毫無顧忌的自利主義者,全然不顧他人的利益,僅僅并且是任何時候都追逐己利,這樣在特定條件下就會抽空他自己的基礎。成功的自利行為,顧及到其他參與者的利益,考慮到利益的均衡,即便這有時需要做出放棄,或者有時甚至會給自己帶來損失”14。道德意味著自己無法為所欲為,意味著對自己自由的某種限制,但聰明者知道,“這種損失會通過好處得到遠比補償更多的東西,這好處來自于合作和有著可能結果的勞動分工”15。因此道德最終是有利的,這源于以道德為前提的合作能夠給所有的人帶來益處。
當然,這種道德的實質在于利益的相互性、對等性、平衡性,而不是自我犧牲式的利他。荷蘭哲學家布思克斯(Chris Buskes)指出:“相互的利他主義意味著,某個人在某個時候為另一人付出精力和注意力,并期待著某個時候會有一種對此的回報”16。這種回報并非總是直接發生,“這種回報不一定直接回饋給我們,更不是以現金的形式還給我們。它的存在方式之一在于,我們在一個社會組織中的地位,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威望提高了,如果我們顯示出樂于助人的話”17。總而言之,道德在于利益的相互性、對等性和平衡性,道德既要克服極端自利,也要避免極端利他。“道德行為最好的論證是相互性原則”18,道德對于所有的人都應是物有所得。而人的這種體現在互助互利上的道德性,也是一個群體、一個社會得以持存的基本前提。“一種社會只有當其成員至少是在某種最低程度上相互合作,才能中期直至長期得以維持。借此互助或相互的利他主義原則便凸顯出來了”19。
這樣我們就看到了,在契約論倫理學的內部,針對有關人們為何要道德,或者道德起源于何種考量這一問題存在著兩種解答方式。如果說霍布斯式的解答所展示的是道德的消極性的益處,即保護個體不受他人的傷害,那么就可以說休謨式的解答所強調的則是道德的積極性的益處,即道德的存在能夠使個體獲得好處。這兩種解答方式并不是對立的,而是處于相互補充的關系。霍布斯和休謨的“兩種論據均表明,一種道德存在和對道德的遵守原則上對于大家都有好處”20。道德構成了社會成員正常的共同生活的基本前提。
值得指出的是,霍布斯和休謨的兩種解答或兩種論據的共同點就在于正確理解并處理了道德與利益的關系。一方面,他們都不否認人們對正當利益的追求和主張,不否認“每個人都擁有權利,毫無良心顧忌地主張其利益和伸張其需求”21。這樣也就完全排除了道德與絕對利他主義之間的必然關系。另一方面,他們也認為,“由于我們自己的安康從本質上取決于我們如何對待他人,故較為合宜的便是合作以及顧及他人的希冀和需求”22。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早就指出:“只想到自己并且逐利無所不用其極的人,決不可能過一種倫理上負責任的生活。如果你想為自己而活,就必須為他人而活”23。而道德便在于因他人之故而對自己過度的逐利活動做出限制。美國法學家霍爾姆斯(Oliver Wendel Holmes)的比喻非常形象:“揮舞我拳頭的權利止于他人鼻子的邊上”24。這就是說,我的確擁有為所欲為的權利,但該權利的邊界在于不得傷及他人。這樣也就完全排除了道德與絕對利己主義之間的任何關系。這也就是說,絕對利他主義與絕對利己主義都是道德所拒斥的,道德容納和包含了正當利己與顧及他人這兩個因素,“道德不是要說,你如果為自己著想便是個壞人,而是說,你如果只為自己著想便是個壞人”25。
由于道德容納和包含了正當利己與顧及他人這兩個因素,既認可善待他人,亦認可善待自己,因而它也就體現了一種不偏激、不過分、合宜、適度和均衡的理性的態度。一句話,道德是合乎理性的。這樣一來就涉及到道德與理性的關系問題。所謂“理性是這樣一種能力,使我們能夠論證、推理,追循抽象的思路,辨別真假”26。理性意味著人們是出于理由來評價、判斷和行動。擁有理性者能夠正確面對其情感沖動、生物本能、盲目意志,能夠在拉開距離的前提下對它們進行審思、檢視、評價和必要的約束控制。訴諸理性者善于依據理由進行反思和權衡:“我所樂意的東西對我真的是有利的?對他人是有利的?在道德上真的是正確的?對自身意志做出評價的能力,被人們稱為自主的理性。……我們并非總是和無條件地聽從我們意志的提示。我們必須在我們自己面前對這種意志……進行辯護”27。簡言之,基于理性就意味著得到理由的辯護或論證。由于正當利己與顧及他人都可以得到理由的辯護,故理性就意味著對極端自利與極端利他的否定,意味著一種合宜的、避免極端的,在自利與他利之間、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進行調節并使之保持平衡的處事態度。這樣,善于理性思維者就能夠認清其利益的內在關聯,能夠在決斷時顧及到其行為的長遠后果,必要時放棄對其需求的短期的、即刻的滿足,從而更快、更好、更便捷地實現自身的總體目標。從道德和理性均合乎人們的總體利益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就可以說:“倫理上的善等同于對于一個人從長遠來看……何為理性的東西”28。一句話,道德的就是理性的。
二
在西方思想史上,對以同情為核心的情感在倫理學中的作用持認同立場者雖不眾多,但也還是存在的。中世紀基督教哲學家把仁慈和近愛看成是核心的德性,而同情則屬于這種德性,故同情是作為德性論的內容得到研究的。盧梭相信同情為人際間的一種基礎性的、前理性的約束性力量。休謨對同情的認可是建立在其情感主義理論的基礎上的。他認定“所有的人類行為歸根到底都是奠立于痛苦和快樂之基礎上的。四種感覺……構成了對我們自己和對其他人做出全部積極和消極評價的底蘊:自豪和羞恥、喜歡和厭惡。于是,休謨便這樣地闡發出其情感主義的核心論斷:‘道德與其說是一種判斷之事,不如說是一種感覺之事:能夠引發自豪或喜歡的事情,我們就會爭取,能夠導致羞恥或厭惡的事情,我們就會努力避免”29。當然,同情倫理的最大代表則首推叔本華。叔本華是霍布斯最激烈的反對者,他否認人的認知能力與道德素質之間的關聯性,認為人的頭腦可以更清醒,但并不妨礙心靈仍然依舊。他也不滿足于康德只講義務的道德理論的空泛性,認為康德只是說出了我們應當道德地行動,但沒有講清楚為何應當道德地行動。叔本華就是要為道德行為給出一個清晰明確的理由,他的答案是:道德真正的驅動力是人的同情感。與不相信情感的理性主義哲學傳統(如柏拉圖、斯賓諾莎和康德)完全不同,叔本華認定并非人的理性,而是人的同情、移情的能力才構成了道德的唯一基礎,這種能力才是唯一真實的道德動力。在他看來,所謂同情就是對他人痛苦直接的感同身受,換言之,同情是一種將他人的存在與感受視為自身的感受的細膩的道德情感,“它是一種對他人受苦的有感觸并且不能無所謂之態度的一般的表達”30。同情意味著設身處地地為他人(也包括動物)著想的能力,“在對異在的痛苦的同情中,我們與其換位思考,并且‘在其命運中觀察到‘整個人類的命運,隨即首先是我們自己的命運”31。通過這種對命運的反思,我們便虛擬地“將自己設置在被我們的行為所關涉到的其他個體的位置上,我們就能夠也必須明了自己的道德義務,我們設問:這些行為的后果對于他們是否是可接受的”32。叔本華從同情中引導出他的兩個德性定理:“不傷害任何人;盡可能幫助所有的人”。這是每種道德的簡潔的表述。這樣,叔本華便通過同情,將他人的痛苦直接轉變成為我的行動的動機,從而清晰地展示了同情倫理所要表達的同情感對道德行為的驅動作用。叔本華之后,霍克海默爾把同情理解為是對他人尊嚴予以尊重的一種具體的表達。“在作為以團結為活動內容的同情中,個體能夠在痛苦著的他人中認識自己”33。20世紀上半葉,在元倫理學領域,把倫理陳述僅僅視為情感表達的假定達到了一個高潮。
毫無疑問,作為道德情感的同情非常重要,它是一種自然的緣于人類本身的相似性的對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以及由此而激發的對馳援的準備與心愿,因而構成了人的道德行為的一種不容忽視的動機,是倫理道德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武克提茨(Franz M.Wuketits)指出:“即便是在一個大眾社會里人們也應當期待一種最低限度的關懷之存在,為什么?因為我們……具備同情、移情的能力”34。也就是說,即便是在匿名的大眾社會里,“也根植著某種情感的結構”35。在一般的環境下,良心的不安與對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的的確確都能夠使我們自覺遠離違規和缺德的行為。而良心、同情感的樹立有待于在家庭、學校及工作崗位長期的教育與熏陶,才有可能從一種偶發的情感沖動成長為一種穩固的心理定勢、堅定的價值取向和自明的道德直覺。
但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如果像叔本華那樣,把同情視為道德的唯一基礎而排除了其他,則也就有些偏激了。關于這一點,如果我們回憶和檢視一下思想史上出現的對同情倫理的三大駁斥理由,就可以看得更為清晰。
第一個理由來自于理性主義對情感之缺陷的最經典的批評,即同情作為情感不僅在人際間是各異的,是一種難以度量的、測不準的值,而且即便是對于同一主體而言,它也是不確定的、任意的、主觀的、與情境相關涉的;同情感充滿了偶然性與隨機性,難以經受一種主體間可以理解的批判性的審視,故在理性主義的哲學傳統中,無法輕易得到認可。赫斯特指出,屬于情感之列的“良心作為道德正確行為的尺度是不可信的,它會失誤”36。羅素甚至提醒人們良心可以命令我們犯下最惡劣的罪行。可見,盡管同情心對某些道德行為具有驅動性的功能,但這種功能缺乏堅實性。“沒有哪樣強烈的情感……可以要求有一種道德規范那樣的約束性”37,“而道德規范要求有一種普遍的適用性”38,每一個人,不論是何種人,不論有何好惡,均必須遵循之。而情感卻提供不了這樣一種穩定一致的有效性,故同情作為情感無法替代對道德行為的理性反思,無法為一種經過理性的審視與驗證的、對所有的人均平等適用的普世性的道德及其約束力提供一種牢靠穩定的論證。康德盡管承認同情之感的美好,但同時也批評這一“良性的激情”是軟弱的并且在任何時候都是盲目的,在他看來,“同情不是道德行為確定的理由”39。
第二個理由在于作為情感的同情的覆蓋面是有局限性的。休謨盡管強調同情作為人性的一部分構成了人的行為的強大動力,但他也承認同情的適用性僅局限于近親。的確,我們的道德同情之感,是像一塊擊入水面的石頭所激起的漣漪那樣,沿著由內到外、由近及遠的軌跡輻射的。基于人類在進化中發展出來的生物性和情感性的基本結構,我們不可能對所有的人施予同等的同情,“我們對親近于我們的人的評價,不同于對陌生人,這是一種天然的本能”40。擁有同情感的同一個人對于不同的對象只能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同情:“良心不懂得平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妻子、自己的親戚和朋友不可能不獲得比他人更大的重要性。我們如果不是這樣,從火中救出別人的孩子而不是自己的,則我們以后就會遭受到無法忍受的良心折磨”41。這個例子說明同情感的由近及遠性是一種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現象。但是,如果換一種場景,同情倫理的局限性和有害性就明顯呈現出來了。據一項全球性的關于道德的思想實驗的調查,當問到是否可以用一個無辜的大胖子來堵路以阻擋壓過來的電車,從而挽救軌道上五條人命時,四分之三的回答是可以,因為五條人命大于一條。但若問到,如果是用您自己的孩子來堵路呢?結果是無人同意。可見,我們的主觀道德情感與普遍的理性道德之間,具有著難以低估的巨大區別。道德情感有時無法體現正確,“盡管我們或許都有這樣的理性的洞見,即每個人的生命原則上都是等價的,但這只是原則上而言。事實上我們對親近于我們的人命與并非如此的人命做出了巨大的區分”42。這個事例清楚說明了情感判斷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絕對難以成為道德的唯一的確定基礎。
第三個理由在于,同情表現了強者對弱者的非對等關系,不符合道德公正的對等性要求。我們知道,同情所展現的是一種強勢的同情者與弱勢的被同情者之間不對等的關系與態勢,其著眼點在于單方面的強者情感的驅動力,它所提升的可能是同情者在與他人關系中的勢力與威嚴,它所貶低和鄙視的可能是受苦受難的被同情者的尊嚴,在這里無法體現道德對人際間對等權利與義務的要求。而“從概念上講道德是一種相互要求的宇宙”43。僅就這一點而言,盡管同情在倫理道德中具有一種重要的價值地位,“但同情……不能成為道德的基礎,……因為如果那樣的話相互的要求便不再屬于道德了”44。另外,在現代社會,對于弱者而言最關鍵的在于權利與正義的伸張,而非僅僅在于對同情與關護的乞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尼采激烈地批評以同情、近愛為核心的猶太-基督教道德是由神甫煽動的奴隸道德,它所體現的只是弱者的怨恨以及神甫對他人統治的興趣。這樣一來,同情便意味著強化而非減弱世間的苦難,“因為同情與一種積極的生活感覺的強化正相反對,恰恰由此而使得消除世間的痛苦變得困難”45。所以尼采自己鼓吹一種自我肯定、抬升生命的英雄道德。
當然,歷史上出現的對同情倫理的所有抨擊并不能起到完全顛覆同情在倫理道德中的地位的效果。因為“同情是一種力量,一種現存的傾向,它們能夠在具體的人性的和社會的關系與關聯中得到實現”46。而有關道德究竟是以理性還是以情感為基礎的爭論,即便是到了今天也沒有停歇。“我們是否依據理由來決斷,抑或是依照與此相系的情感的強大來決斷,這是一個我們永無能準確回答的問題。理由是明顯的:我們的意識本身就無法清楚地區分情感與思想”47。這表明,直覺、感覺與理性在我們的道德決斷中是交織在一起共同作用的因素。“道德感覺保障了個體的連續性,它在大部分日常生活中構成了復雜決斷的唯一安全的基礎”48。這就是說,“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大多是聽從我們迅捷的道德靈感。我們依照同情或反感做出的判斷遠快于按照道德準則”49。但當感覺與感覺之間發生沖突的時候,當決斷單方面地倒向某些感覺而忽視了其他感覺的時候,當在復雜的社會情境面前要求我們做出巨大抉擇之時,我們就需要訴諸理性的引導,需要借由理性來對感覺間的沖突進行化解和調節,需要通過對理據的審視、辯駁、反思和權衡來做出明智的道德決斷。由此可見,情感與理性在倫理道德中從根本上說并不是對立的,情感為理性決斷提供了養料并構成了助力。
結束語
道德究竟是以理性還是以情感為基礎,是倫理學的一個基礎性問題,也是倫理學家必須關注和回答的問題。倫理學家要從人類幾千年以來的思想寶庫中汲取已經、正在并且應當左右我們生活的精神養料,對之進行分析闡釋,說明盡管這個世界業已高度發展并變得無比復雜,但人類仍然要有道德的導引。接著,倫理學家要從學理上論證人們遵守道德規范的緣由,說明人之所以需要守德,與人既是由理性驅動,也是由情感引導的特性相關,進而從理性合作和情感驅動兩個方面來厘清人類服從道德要求的動力機制。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倫理學家本身便是人們應當學習和效仿的道德權威。倫理學家的優勢更多是在于,具備倫理學領域的專業知識,了解基本的道德價值與原則以及像自主性、人的尊嚴這樣的倫理學核心理念的意義,善于明晰概念、辨識問題、邏輯思維、理性論證。其作用一方面類似于一個過濾器,在倫理論證中依靠理性的標準和武器來鏟除混亂的、矛盾的、不合邏輯和難以說明的論據及立場。另一方面像一只羅盤,對于具體事態的是非判斷、情境的道德維度的把握以及有關重大的倫理問題的決斷,提供一種普遍的道德標準和致思路徑,就像“羅盤并非直接標示正確的道路,而是指出了正確道路如何得以獲知”50那樣。倫理學家能夠對不同場景中的道德行為做出論證,辨析典型事例中倫理因素的構造,幫助人們在復雜的事態中確立一個正確的前行方位,但對道德意識的呼吁和召喚,并不能直接導致對象的行為的貫徹落實,因為這最終取決于行動者自己的自由抉擇。“然而就像羅盤只是幫助其使用者找到正確的道路,而無法強迫其真的去走這條正確認識到的道路那樣,倫理學只是引導行為者以道德的方式來確定其意志,而無法強迫其真的去實施道德上得以認知的行為”51。因為每個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人,為此他就必須運用自身的判斷力,來決定是否接受倫理學家的建議,來對自己應當走的道路做出選擇,并最終為此而承擔應有的責任。這盡管對于社會意味著道德安穩感的喪失,對于個體意味著抉擇風險的出現,但同時卻又體現了人的從咎由自取的不成熟狀態的最終擺脫,體現了人類運用自身理智的巨大勇氣,體現了自由選擇這一啟蒙運動所推崇的最高價值。
注釋:
①48Georg Lind: Die Entwicklung moralischer Gefuehle durch Vernunft und Dialog,in:Georg Lind/Gundula Pollitt-Gerlach(Hg.):Moral in unmoralischer Zeit,Asanger 1989,S.12,S.28
②③④⑤⑥2032Kurt Bayertz: Warum ueberhaupt moralisch sein Muenchen 2004,S.130-131,S.117,S.117,S.116, S. 119-120,S.132,S.125
⑦Aristoteles:Nikomachische Ethik, 1097b
⑧Zitiert bei David Hume,vgl. Karl Hepfer: Philosophische Ethik, Goettigen 2008,S.12
⑨1214152628Karl Hepfer: Philosophische Ethik, Goettigen 2008,S.12,S.72,S.74,S.66,S.81,S.134
⑩11Vgl. Kurt Bayertz: Warum ueberhaupt moralisch sein? Muenchen 2004,S.131,S.131
13Peter Fischer: Einfuehrung in die Ethik, Paderborn 2003,S.76
16Vgl. Franz M. Wuketits: Wie viel Moral vertraegt der Mensch? Guetersloh 2010,S.33
171819223435Franz M. Wuketits: Wie viel Moral vertraegt der Mensch·Guetersloh 2010,S.38,S.121,S.32,S.39,S.85,S.87
2125Reiner Erlinger: Moral,Frankfurt a.M.2011,S.30,S.30
232427Vgl. Richard David Precht: Die Kunst,kein Egoist zu sein,2.Auflage,Muenchen 2011,S.161,S.30,S.122
29Vgl. Karl Hepfer: Philosophische Ethik, Goettingen 2008, S.124
30Uta Eichler: Mitleid und Pflicht, in: H. Klemme/M. Kuehn/D. Schoenecker(Hg.): Moralischer Motivation, Hamburg 2006, S.247
31Vgl. Gunzelin Schmid Noerr: Geschichte der Ethik,Leibzig 2006,S.109
33Vgl.Alfons Maurer:Mitleid,in:Jean-Pierre Wils/Christoph Huebenthal(Hg.):Lexikon der Ethik,Paderborn 2006,S.237
36Norbert Hoerster: Ethik und Interesse, Stuttgart 2003, S.14
37385051Annemarie Pieper: Einfuehrung in die Ethik, 4. Auflage, Tuebingen und Basel 2000, S.190,S.190,S.115,S.116
394546Alfons Maurer:Mitleid,in:Jean-Pierre Wils/Christoph Huebenthal(Hg.):Lexikon der Ethik,Paderborn 2006,S.237,S.237,S.239
40424749Richard David Precht: Die Kunst,kein Egoist zu sein,2.Auflage,Muenchen 2011,S.241,S.240,S.124,S.123
41Hans-Joachim Niemann: Ist das Gewissen wirklich die letzte Instanz? In: Aufklaerung und Kritik, 1/2010,S.39
4344Ernst Tugendhat: Vorlesungen ueber Ethik, Frankfurt a.M. 1993, S. 196,S.191
Morality: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Emotion
Gan Shaop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thics, the rational ethic group and emotional ethic group has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moraliy, it should be based on rationality or emotion. Articles interpret and analyze Hobbes and Hume's contract theory of rational ethics and Schopenhauer's sympathy ethics, to demonstrate fundamentally that emotional and rational ethics do not diametrically opposed, but factors in our moral decision. The reason why people have to obey the moral is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are not only driven by the rational, but also guided by the emotional factors, thus, it has to analyze r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motional drire to clarify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people's will on morality.
Keywords: rationality, emotion, contract theory, sympathy, mor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