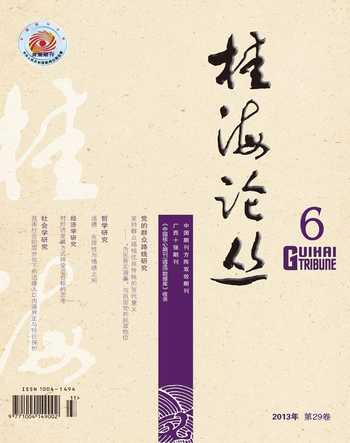養老保障體系的分割與整合
侯慧麗
摘 要:文章以北京市為研究個案,對養老保險城鄉統籌制度進行分析,發現以地方政府為主進行的養老保障統籌直接弱化了社會保障的城鄉分割,但強化了養老保障的地區間分割。雖然在地區內縮小了城鄉福利水平的差距,但實際上是加大了地區之間養老保障收入的不平等。這種“福利地方”意味著社會保障在國家范圍內的“碎片化”狀態的持續,將會對一個地方的人口規模、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及勞動力市場的健康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關鍵詞:養老保障體系;養老保險;北京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3)06-0094-06
目前我國的養老保障制度存在著城鄉分割和地區分割兩種特征。城鄉分割根源于原有的城鄉二元分割的社會保障制度,基于戶籍的劃分,在城市和農村實行完全不同的兩種保障制度,也就是厚城市薄農村,在之后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過程中,也經歷了一個先城市后農村的路徑。20世紀80年代中期,城鎮的養老保障制度開始試點改革,歷經近30年的發展,目前已經比較健全,完成了從傳統的單位養老保障體制向社會養老保障體制的轉軌,建立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障制度。相比較城鎮養老保障制度,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發展要緩慢的多,甚至出現過停滯和倒退。近年來,隨著城市化加快和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上升,建立農村養老保障體制的緊迫性才越來越強,2009年,國務院決定在全國10%的縣市實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爭取2020年之前基本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
同樣基于戶籍的劃分,養老保障制度還是屬地化的保障制度,這樣就產生了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都以戶籍地作為享受社會保障的基礎。但是我國的地區發展十分不平衡,在各省、市、自治區均有權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社會保障地方法規和規章的情況下,各地根據自己的財政力量和實際情況,在社會保險和險種設置、繳費比例與給付水平上千差萬別,形成了社會保障的地區分割的狀況。
社會保障制度的這種分割狀態使得養老保障不能進行養老保險關系和統籌賬戶的轉移和接續,而且容易形成社會統籌的非均等化,形成養老保障制度的“碎片化”,造成“便攜性損失”[1],對勞動力地區間流動和一體化建設形成了巨大障礙。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流動成為必然趨勢,因此,勞動力市場的發育對養老保障的分割狀態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2009年12月由國務院批準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暫行辦法》出臺,意味著城鎮養老保障從制度上又向全國統籌的目標前進了一步。但是在此《辦法》規定中,雖然允許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但是能夠實現異地轉移接續的條件是比較嚴格的,而且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并沒有產生多少預期效果。沒有真正實現全國的養老保障統籌就不會有實質上的養老保障的整合。
本文以北京市的養老保障制度發展為例,首先概括了北京市的多層次城鄉統籌養老保障體系的基本內容,在此基礎上分析了北京在地區內部實現了城鄉統籌的養老保障和北京與其他省份地區的養老保障關系,認為在目前以地方為主導推進養老保障體制的改革弱化了城鄉分割,但卻會強化地區分割,不利于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中央政府的行政力量和財政力量應該是實現全國統籌的主要力量。
一、我國養老保險從分割到整合的趨勢
為適應經濟體制的轉軌,社會養老保障體制的改革也在經歷從計劃向市場的逐漸變革。原有的具有城鄉分割和地區分割特征的社會保障制度的許多弊端在市場體制中不斷顯現,比如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尤其是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因此,在養老保障體制的改革中,從地方到中央都在緩慢地將制度從分割推進到整合。
從1984年起,全國各地先后實行了養老保險費用社會統籌,但統籌層次一般只在縣市級。1991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實行國家、企業、個人共同負擔的養老保障體系。1997年,國務院正式頒布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提出全國統一按職工工資的11%建立個人賬戶。為了解決不同所有制企業和部門之間的社會保障負擔不均現象,1998年,國務院又實行了職工養老保險全國并軌,由市級統籌向省級統籌過渡,養老金的差額繳撥改為全額繳撥,實施養老金的社會化發放。2001年以后的改革,主要是進一步完善養老保障體制,著力解決個人賬戶空賬、提高統籌層次、解決歷史欠債和擴大養老保障覆蓋面等一系列深層次問題。到2009年,全國已有13個省、市、自治區實現了省級統籌。
在養老保障的改革過程中,國家逐步實行城鎮養老保障從地方分立到全國統一,從市縣級統籌到省級統籌的改革。同時,在一些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由于財政實力比較強,開始了城鄉養老保障統籌的試點,當然,這些試點只是限制在某一個地區之內。比如嘉興市在2007年就推出了《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暫行辦法》,規定本市行政區域內,年滿16周歲至60周歲,符合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或現有各類社會養老保障對象之外的城鄉居民(不含在校學生),可以參加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同時對在《暫行辦法》實施前已年滿70周歲(含),且符合相關條件的高齡老人,實行養老生活補助。這個辦法涵蓋城鄉,是繼嘉興市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突破城鄉二元結構的一項重大舉措。天津2009年開始對已經實施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農村居民基本養老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障制度進行調整,統一了城鄉居民基本養老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使城鄉居民基本養老和基本醫療制度一體化,是全國第一個實現兩項制度城鄉統籌發展的省級統籌地區。另外,還有無錫、蘇州等地方也都進行了城鄉統籌養老保障制度的探索。
從分割到整合其實是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發展和改革的目標,在改革的過程中,從政策和實踐上都在遵循著這個目標行進。但是把發展不平衡的城鄉、地區碎片式的保障制度整合起來,在這個過程中會遇到許多的障礙。北京市在2009年實行了城鄉居民養老保障之后基本實現了全面覆蓋,是全國率先實行了城鄉統籌的省份。在北京實行了地區內部的城鄉整合之后,是否會與實現全國統籌的目標更近了呢?
二、北京市養老保障的進展
北京市養老保障體系主要由基本養老保障、城鄉無社會保障老年居民養老保障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障組成。這三種保障制度基本上將城鎮和農村應保人員都納入了保障范圍,實現了養老保障的全民覆蓋。
(一)北京市養老保險內容
最新的北京市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參保對象為本市行政區域內的企業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城鎮職工、城鎮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基本養老金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組成,繳費標準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資為繳費工資基數,按照8%的比例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全額計入個人賬戶,企業以全部城鎮職工繳費工資基數之和作為企業繳費工資基數,按照20%的比例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存入基礎養老金賬戶。
2008年起,北京市實行了城鄉無社會保障老年居民養老保障辦法,規定凡具有本市戶籍、男性年滿60周歲,女性年滿55周歲且不享受社會養老保障待遇的人員,享受城鄉無社會保障老年居民養老保障待遇,即每人每月享受200元的老年保障待遇,待遇水平根據本市經濟發展水平和承受能力適時調整,一般稱為福利養老金。
2009年,北京市出臺了《北京市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辦法》,規定具有北京市戶籍,男年滿16周歲未滿60周歲、女年滿16周歲未滿55周歲(不含在校生),未納入行政事業單位編制管理或不符合參加本市基本養老保險條件的城鄉居民都可參保。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實行個人賬戶與基礎養老金相結合,個人繳費、集體補助與政府補貼相結合的制度模式。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費采取按年繳費的方式繳納,最低繳費標準為上一年度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9%,最高繳費標準為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保險待遇由個人賬戶養老金和基礎養老金兩部分組成,個人賬戶養老金由個人賬戶支付,基礎養老金標準由全市實行統一的每人每月280元。
按照北京市人口結構,我們推算了三種養老保障制度的覆蓋比例,如圖1。
圖1 北京市60歲以上(包括55歲以上女性)老人三種
養老保障領取比例
(二)北京市養老保障水平
由于三種養老保障制度實施的時間不同,覆蓋對象條件不同,政府補貼條件不同,養老金積累差異很大,所以養老金領取水平在三種人群中差距較大。
基本養老保險從試點到形成比較完善的體系經歷了20、30年的時間,個人企業繳費時間較長,養老金積累比較雄厚,所以養老金水平比較高。根據北京市2008年統計公報,2008年末,北京市參加基本養老保障人數671.1萬人,離退休人數為171.2萬人。根據2007年人口抽樣數據推算出北京市戶籍人口領取養老金人數為124萬人,2008年經調整后養老金月均水平為1580元[2]。城鄉居民養老保障從2009年正式實施,本文為了說明養老保障的水平,用相關數據進行了推算和計算,模擬了2008年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障的領取人數和養老金數額。如果按照最低繳費標準,即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9%繳費,2007年,北京市農民人均純收入為9440元。那么,一年后繳費為850元。同時假定個人賬戶收益率每年為3%,2000年北京市總體預期壽命為76歲,在每月基礎養老金為280元不變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計算繳費一年后領取養老金為285元。由于2009年1月開始實行,目前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除去基本養老金和福利養老金人數,大概估算第一年有9萬人可以領取城鄉居民養老金[3]。
北京市共有60歲以上城鄉老年人210.2萬,其中有70萬老年人還沒有享受社會養老保障待遇,包括城鎮19萬人,農村51萬人,加上56歲-59歲老年女性約有7萬人。城鄉無保障老年居民養老保障將近77萬無保障老年人全部納入了福利養老范圍內。77萬老年人將享受到政府每人每月200元的福利養老金。
三種養老保障制度的養老金待遇雖然有很大差異,但是這個養老保障體系將60歲以上老年人口全部納入了養老保障。
(三)北京市養老保障制度體系的特點
北京率先在全國實現了城鄉統一覆蓋全民的養老保障制度,從對三種不同層次、不同保障水平組成的制度體系看,北京市養老保障具有全民享有、政府兜底、動態發展、戶籍權益的特點。
北京市的養老保障體系除了把有就業單位的人,還把沒有就業身份的城市居民、農村居民都也都包括進來,并且將已經超過參保年齡而沒有參加其他社會保險的60歲以上(含56歲-59歲的女性人口)老年人口全部給以標準一致的福利養老金,這樣就使得人人都享有了基本的養老保障。但是這個全民僅僅是限定有北京市戶籍的人員,即北京市范圍內的全民。
對于未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城市居民、農村居民和老年居民來說,通過實行完全個人賬戶積累制很難實現對他們的養老保障,尤其是在短期內實現全民養老保障更是不可能。因此,北京市對這些人群實行政府補貼的辦法,對60歲以下的未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城鄉居民實行基礎養老金由政府補貼兜底,個人賬戶由個人繳費累積。對60歲以上的未享受養老保障的居民實行政府補貼,全部由政府負擔養老金,這樣通過政府的財政補貼,實現了全民覆蓋的養老保障。
城鄉無保障老年居民養老保障給60歲以上(含55歲以上女性)居民按200元/人/月的標準發放,解決了所有沒有參加社會保險的而且從年齡上也不可能再參加社會保險的老年人口的養老金問題,并且規定這類人群的范圍不再擴大。也就是說從2009開始,隨著滿60歲的人口逐漸消亡,領取福利養老金的人口將消失,根據2000年北京市人口生命表計算,這個過程大概需要40多年的時間,而未滿60歲的沒有參加基本養老金的人口將全部參加居民養老保障,那么,城市的養老保障體系就從現在的三種類型變為基本養老保險和居民養老保險兩種類型。這也將是養老保障制度發展的方向。
三種養老保障制度中,在參保對象的確定上,除了基本養老保險沒有限定參保人員必須是北京市戶籍外,城鄉居民養老保障和城鄉無保障老年居民養老保障中都明確規定了參保人員和領取人員必須具有北京市戶籍。依附于戶籍之上的保障利益仍然清晰可見,在北京雖然城鄉戶籍之間的差別已經消失,但是北京戶籍與外地戶籍的地區差異導致的利益仍然明顯的存在。政府的財政補貼也正是建立在戶籍劃分的人口上。
三、戶籍分割下的人口結構與養老保障資源享有的不平等
北京市養老保障體系中,通過地區的戶籍身份來劃分參保對象仍然是一個顯著特點。雖然在北京市社會保障制度的政策安排中,基于城鄉戶籍制度分割的福利差距已經不存在了,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的社會保障已經完全形成一個體系,實現了城鄉一體化。但是用戶籍的地區性質來限定參保對象的規定仍然沒有改變。除了城鎮職工社會養老保障之外,城鄉居民養老保障與城鄉無保障老年居民養老保障的規定嚴格規定了參保者只能是擁有本市戶籍的人口,不論是城市戶籍還是農業戶籍。
基本養老保險大多是由單位的職工參加養老保險,由于全國勞動力市場逐漸發育成熟,相應的勞動力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也應逐漸打破地區和城鄉界限而形成統一的保障體系。在政策安排中,基本養老保險不再用戶籍來限定參保人員,但是在另外兩種養老保障類型中,仍然將戶籍作為一個很重要的限定條件。
(一)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的老齡化程度
在《中國統計年鑒》中,對人口統計有兩種口徑,一個是戶籍人口,一個是常住人口。而使用最多的是常住人口,每年抽樣統計的人口數都是常住人口數,在財政收入與GDP統計中使用的也是常住人口。表1是北京市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相關指標的不同統計結果。
表1 北京市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的統計分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8》,《北京統計年鑒2008》,《北京市2007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齡事業發展狀況報告》。
從表1中可以看到幾點:第一,不論是按戶籍人口還是按常住人口計算,不論是按60歲人口還是65歲人口計算,北京市都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第二,戶籍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和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都大于常住人口的比例,就是說,按戶籍人口計算的老齡化程度遠遠高于按常住人口計算的老齡化程度。第三,常住人口集中在15歲-60歲勞動年齡組,總人口中,戶籍人口總人口占常住人口的74%,而60歲以上人口中,戶籍人口占常住人口93%,65歲及以上人口中,戶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96%,因為常住人口的年齡結構以勞動年齡人口為主,其次為14歲以下未成年人。
(二)養老保障資源享有的不平等
按常住人口來計算的老齡化程度遠遠低于按戶籍人口計算的老齡化程度,老年負擔系數也大大降低,僅從人口年齡結構上的簡單比例的計算上就可以看出,外來勞動年齡人口為北京減輕了沉重的養老負擔。外來人口中以勞動年齡人口為主,意味著這些年輕勞動力一方面為北京創造著地區生產總值的上升,增加著財政收入,上繳的養老基金統籌都留給了北京。另一方面卻沒有給北京增加養老負擔,因為北京的福利養老金和城鄉居民養老金把他們排斥在外,雖然外來勞動力可以參加北京市基本養老保險,但是在目前沒有實現養老金管理全國統籌的情況下,真正能做到按北京標準在北京領取養老金還是比較困難的。如果按照60歲以上人口的老齡比例和地區生產總值兩者的關系來看,北京在全國屬于老齡化程度處于中上水平,而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處于非常高的地區,僅次于上海,位于全國第二位。
北京的人均財政收入水平也非常高,接近1萬元,在全國處于第二位,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因此在北京市用福利養老金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障制度完成全民覆蓋和城鄉一體化的時候,其實是享受了外來勞動力利益的再分配,利用了外來勞動力的利益來增加一個地區的有限的養老保障資源。
如果從全國范圍看,老齡化程度高的地區分布在經濟發展水平的兩端,京、津、滬等屬于經濟發達的勞動力輸入地區,由于生育率非常低,人口預期壽命較高,自然增加人口偏少,這些省份的老齡化水平都在10%以上,人均GDP都在30000元以上,最高的上海達到66367元,但同時,皖、渝、川等勞動力輸出地區由于勞動年齡人口大量外出,并且越來越多的是以孩子隨遷的家庭形式的遷移,老年人口則返鄉或不再外出,這樣造成了勞動力輸出地區的老齡化程度偏高,都在10%以上,而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相當低,人均GDP不超過15000元,不到發達省份的一半。如表2。
表2 勞動力輸出地區和勞動力輸入地區的老齡化
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8》。
這樣來看,老齡化水平都較高的情況下,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能力卻相差懸殊,養老保障資源在各地區之間由于勞動力流動和戶籍分割越發顯得不平衡。其中勞動年齡人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據鄭秉文(2008)根據2005年普查數據的推算,北京流入人口有324.02萬人,為打工地留下了14.7億元的基金,而流出基金為1.8億元,流入的基金為基金平衡貢獻了12.9億元,這僅僅是基本養老保險上繳的統籌基金在北京的沉淀,還不包括流動人口為北京創造的財政收入轉為城鄉居民養老和福利養老金的政府財政補貼部分。
其實,這也說明了外來流動人口的養老保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流動人口社會保障問題直接影響到了地區之間的養老保障資源的擁有,影響了地區之間的養老保障水平的不平等。
四、結論與討論
(一)強化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地區分割
北京市在全國率先實行城鄉一體的全民覆蓋的養老保障體制是養老保障制度發展的一個典范,實行以來,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僅就農村養老參保覆蓋面來看,建立城鄉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后,北京市農村參加養老保險的人數大幅度上升,2008年已達到127.5萬人,是1995年的8倍以上,覆蓋率提高到85%。北京市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財政能力、城市化水平及人均收入水平等都在全國處于先進行列,所以對全民覆蓋和城鄉一體化的養老保障制度具有一定的財政負擔能力。但是從對福利養老制度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障制度的參保人員的戶籍限定條件來看,北京的養老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了外來勞動力的養老保障資源,這種占有會進一步導致地區間養老保障水平的差距。北京實行的城鄉統籌雖然在北京地區內縮小了城鄉福利水平的差距,但實際上是加大了地區之間養老保障資源享有的不平等。
從北京市的例子中,我們不難發現的一個結果就是在以地方政府為主進行的養老保障統籌直接弱化了社會保障的城鄉間的分割,而間接強化了保障的地區間的分割,但是這樣的發展方向并不是我們整合目標發展的方向。
(二)從福利地方向福利國家的轉變
由于目前的財政制度是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分權制度,在中央把社會保障責任和權利都下放給了地方政府的狀態下,又對地方的社會保障發展缺乏財政支持和直接管理,在地方政府主導下,必然會優先發展本地區的社會保障,積極在本地區內實現整合,完成本地區的城鄉統籌和地區統籌,形成一個“福利地方”。但是在向全國統籌推進,打破地方分割時,地方政府往往就會維護自己的利益,一個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對流動人口會采取直接或間接的排斥態度,這樣加劇了地區間的社會保障資源和水平的不平等。社會保障的地區分割狀態是“碎片化”的根源,難以實現從“福利地方”向“福利國家”的轉變。
“福利地方”意味著社會保障在國家范圍內的“碎片化”狀態的持續,將會對一個地方的人口規模、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及勞動力市場的健康發展產生巨大影響。作為福利國家之一的英國歷史上曾出現過一個教訓是斯賓漢姆蘭德制①。北京的養老保障模式似乎恰恰與斯賓漢姆蘭德制相反,是一種完全封閉的地區保障制度。利用戶籍制度,將非北京市戶籍的人口完全排斥在養老保險體制之外,這樣確實排除了由于保障水平高而導致的大量人口流入所帶來的福利支出的壓力,但是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限制了人口的流動,即使許多勞動力流動進入北京,工作很長時間仍然無法享受到北京市的養老保障待遇,這樣就會阻礙勞動力流入北京,特別是高素質的人才流動進入北京。假設北京養老模式中不規定戶籍的限制,也就是說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那么北京也將會出現因為人口多而產生巨大財政壓力的現象。如同斯賓漢姆蘭德制那樣最終一個郡的財力不堪重負而失敗。所以,在地區之間社會保障水平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下,既要考慮到財政的壓力,又要考慮到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那就是將養老保障制度建成全國范圍的統一制度,形成“福利國家”,也就是實施社會保障的主體應該是中央政府。
但是從“福利地方”向“福利國家”的轉變要經歷一個艱巨的過程。即使已經比較成熟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障體系也沒有全部做到省級統籌。2009年,全國只有13個省市自治區實現了省級統籌,大部分地區還是地市級統籌,大大阻礙了勞動力流動和社會保障的發展。
從“福利地方”向“福利國家”的轉變,實際就是減少利益主體的過程。以地區為統籌地的、過度分散的養老保障決策與運行方式下,形成了許多的利益主體,其消極后果不僅在于各地區間養老保險政策、水平難以協調和平衡,更在于形成養老基金分散管理的格局,以及在這種格局下基于積累基金的“所有權”而形成的地方利益。這些地方利益的打破無疑會受到來自利益主體的阻礙。所以既要協調地方利益,又要實現統籌,對中央政府是一個挑戰。
注釋:
①斯賓漢姆蘭德制是在英國斯賓漢姆蘭德郡實行的一種由公共財政出資的地區性最低工資的家庭補貼政策,它旨在避免激烈的競爭給該郡居民帶來的社會風險,其結果雖然為本地居民提供了保障性的家庭收入,但同時吸引了大批的外來人口來到斯賓漢姆蘭德地區,導致勞動力激增,最后導致一個郡的財政無法滿足龐大勞動力規模的社會保障開支,最終造成了局部人口過剩和失業增加,實施僅30年就以失敗告終。斯賓漢姆蘭德制忽略了人口流動的現實,勞動力的流動超出了一個郡的范疇,但是提供財政的部門卻只是一個郡。所以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狀態下,一個郡的財政能力是無法解決一個開放式的福利支出的。
參考文獻:
[1]鄭秉文.改革開放30年中國流動人口社會保障的發展與挑戰[J].中國人口科學,2008.(5).
[2]杜弋鵬.北京市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人均月增二百元.(2008-01-08)http://www.gmw.cn/01gmrb/2008-01/08/content_720152.htm.
[3]北京市人口老齡工作委員會.北京市2007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齡事業發展狀況報告[EB/OL].(2008-10-13).http://zhengwu.beijing.gov.cn/tjxx/tjgb/t/244333.htm.
The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Retirement Pension System
——A Case of Beijing
Hou Huil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Beijing as example to analyze urban and rural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which find out that local government weakens directly the separation of social seaurity between urban and raral, but enhanced inter-regional division of pension security. Even snch measure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welfare, but actually increased pension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regions. This welfare place means that the social security is in a fragmentation state, which affect on the population, rational flow of labor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market significantly.
Keywords: the retirement pension system, pension insurance, Be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