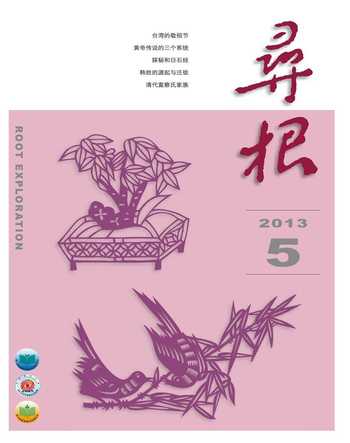漢畫中的佛教造像溯源
王峰
漢畫中的佛教造像是佛教反映在漢代繪畫、雕刻領域的產物,是后世石窟造像普及的先聲。在江蘇、山東、四川、河南等地發現了一批與佛教有關的漢畫圖像,本文把這些漢畫佛教圖像分為漢畫中的佛像圖、漢畫中的佛教故事圖、漢畫中的馴象和乘象圖、南陽漢畫中具有佛教因素的圖像等,并對其源由分別探討分析。
漢畫佛像圖
在山東、四川、新疆等地的漢代畫像以及在江蘇省連云港市孔望山的漢代摩崖造像中,發現一批佛像圖。這些圖像中佛教人物所具有的高肉髻、項光、施無畏印、結跏趺坐等都帶有十分鮮明的佛教藝術造型特征,而且還具有一定的佛教涵義。1959年10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豐縣北尼雅漢墓所出土的一塊藍纈棉布上,畫有一菩薩圖像。此菩薩上身赤裸,慈眉善目,手持鮮花,頭后有項光,身后有背光。四川省樂山市麻浩崖墓享堂的門楣上,刻有一結跏趺坐,右手施無畏印,頭有肉髻,繞頭有佛光的佛像。何謂結跏趺坐?趺者,足背也;交結左右足背并置于左右腿上,即結跏趺坐。《慧琳音義》八曰:“結跏趺坐,結有二種:一曰吉祥,一曰降魔。凡坐先以右趾押左股,后以左趾押右股。此即左押右,手亦左在上,名日降魔坐,諸禪宗多傳此坐……其吉祥坐,先以左趾押右股,后以右趾押左股,令二足掌仰于二股之上。手亦右押左,安仰跏趺之上,名日吉祥坐。如來昔在菩提樹下,成正覺,身安吉祥之坐,手作降魔之印,故如來常安此坐,轉妙法輪。”可見,結跏趺坐乃是佛教徒的一種坐姿,結坐的姿勢不同,其所寓有的佛教含義也不同。至于佛像所施無畏印,根據《造像量度經續·五威儀式》記載:“左手如前正定(即左手下伸),右手胸前,或乳旁,手掌向外略揚之,謂之施無畏印。”另據《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記載:“右手展掌,豎其五指,當肩向外,名施無畏,此印能施一切眾生,安樂一切。”由此看來,漢畫佛像人物的每一種坐姿,每一個手勢,都具有特定的宗教意義,如漢畫佛像人物的結跏趺坐、施無畏印就寓有“轉妙法輪、安樂一切、普度眾生”的佛教宗旨。其實,這也正是漢畫佛像人物的微妙之所在,通過舉手盤足安坐等細微的人體動作來宣傳佛教。通過無聲有形的佛教造像給人們施以潛移默化的宗教影響。
漢畫佛教故事圖
漢畫中的佛教故事圖,目前所能斷定的不多。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目前可能只有三幅。江蘇二幅,山東一幅。山東佛教漢畫的內容是宣傳佛教教義的,本文把它列入佛教故事類。江蘇省連云港市孔望山的摩崖造像,歷來被看作漢代的文化遺存,其手法主要都是以漢代畫像石的減地平級和剔地隱起的淺浮雕的形式表現的,它既有別于后世佛教造像所表現的技法和風格,也不同于東漢墓中所發現的佛教雕像和圖像。孔望山的摩崖造像,開佛教石窟造像之先河,為后世石窟造像的興盛打下了基礎。其中的“佛祖涅槃”圖和“舍身飼虎”圖為佛教故事。“佛祖涅檗”圖是孔望山佛教摩崖造像中較為完整的一幅,其造像以一塊肉紅色的巖石坎臺為中心,在這塊巖石上雕刻出佛祖涅槃像,在與其相鄰的巖石上,雕造了五六十個頭像和跪像。“佛祖涅槃”所描繪的情景與《佛本行贊》中所記載的佛祖涅槃情形極其相似。《佛本行贊》五云:“時諸力土眾,聞佛已涅槃,亂聲同悲泣,如群鵲遇鷹。悉來詣雙樹,靚此來長眠。無復覺悟容,椎胸而呼天。猶獅子搏犢,群牛亂呼聲……彼諸力土眾,或悲泣號眺,或密或無聲,或投身于地,或寂然禪思,或煩冤長吟。”何謂涅檗呢?涅槃即佛祖釋迦牟尼八相之中的入滅之相,《涅經》四曰:“滅諸煩惱,名為涅槃。離諸有者,乃為涅槃。”這幅“佛祖涅槃”圖所宣傳的是釋迦牟尼所倡行的“當修涅槃,永離苦樂”的思想。
“舍身飼虎”圖在“佛祖涅檠”圖之右,其內容為:一人臥于地上,在人身上有虎頭,若欲吞狀。這一“舍身飼虎”佛教故事,在佛經中有十多處記載。關于舍身飼虎故事的內容也有幾種說法。其中《菩薩投身飴餓虎起塔因緣經》載云:“乾越陀國太子梅檀摩提,在國內施舍貧苦、獨、老、贏之人,于大路中施舍貧人,四方來者皆得如意。后至山中大巖窟,修禪道求菩提度眾生苦,因見山中虎產七子,而不得食,太子投身飼虎,骨肉狼藉。后為起七寶塔。”“舍身飼虎”佛教故事所宣揚的是佛教教義中的“因果報應,轉生來世”思想,而且告訴人們“濟人之危,須得誠心誠意;敢于舍得區區一身,才能留得精神傳世”。
在《山東漢畫像石選集》著錄的圖322,是出土于滕縣漢畫像石的圖像,該石畫面漫漶,共四層:一層為西王母,兩側有蛇尾侍者和伏羲、女媧等;二層為牛馬食草;三層為人物相會;四層為牛車、鹿車、羊車各一輛。這組畫像很可能與佛教《法華經》中所宣揚的“三乘”教義有關。
所謂“乘”,據《四教儀集注》記載:“乘以運載為義。”佛經中所謂的“三乘”,是指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法華經》明確地將菩薩乘喻為牛車,是為大乘;把緣覺乘喻為鹿車,是為中乘,亦謂辟支佛乘;把聲聞乘比喻為羊車,是為小乘。這一層畫面正好與此吻合。
《法華經》載云:“初以三車,誘引諸子,然后但與大車,寶物莊嚴,安穩第一。”進而指出:“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這也即所謂的三乘為方便,一佛乘為真實,會三乘而歸一乘的思想,用佛家的話來說,即“三乘歸一”。
漢畫中的馴象乘象圖
馴象活動,商時已有。《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東漢時期,佛教在全國范圍內已有一定的傳播,佛家教義已經為一些人所信仰。漢畫中的馴象圖和乘象圖表明漢代先民已經掌握了馴象之法和騎象乘象之術,這也可能與佛教的“行象”活動有關。但是這一說法缺乏文獻記載。用鉤馴象之法,最早見于晉朝法炬譯的佛經;“行象”活動,文獻中較早的見于北魏時楊街之所著的《洛陽伽藍記》。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佛教影響的日益普及,我國古代的“舞象”活動與佛教的“行象”活動結合起來,并且長久地被保存下來。
在河南南陽、登封少室漢闕,江蘇省徐州洪樓,山東省滕縣宏道院、嘉祥呂村、南武陽功曹闕、南武陽室圣卿闕等地都發現有象奴馴象的圖像。其中南陽漢畫館所藏“馴象”漢畫像內容為:大象長鼻上卷,齒前伸;象奴頭戴尖頂冠,手中持鉤,鉤末端置于象后右肢部。徐州市洪樓“馴象”圖像的內容為:象奴手持長鉤,騎于象背之上,正在馴象。用鉤馴象,文物中最早見于漢畫,文獻中最詳細見于佛經。東漢著名思想家王充在《論衡·物勢篇》中論以小勝大時說:“長仞之象,為越僮所鉤。”但至于如何用鉤馴象,王充卻沒有詳細說明。晉代法炬譯的《法句譬喻經》對此描述得很詳細:“佛問居士:‘調象之法有幾事乎?答:‘常以三事用調大象。‘何謂為三?曰:‘剛鉤鉤口以制口強。”剛鉤即鋼鉤,由此可知,東漢先民在當時已經掌握了鋼鉤鉤口馴象的方法。這也許與佛經所載的馴象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可能與佛教活動有一定聯系。馴熟大象,便于進行“乘象”活動。
佛教徒常在每年四月八日釋迦牟尼誕辰日舉行大規模的“行象”活動,用以擴大佛教的影響。常以馴成的大象馭著佛像或佛牙沿街穿巷,通過演出百戲的形式,向群眾展出佛像,以此來宣傳佛教思想。象在佛經中喻佛性,印度人敬重象,實即敬重佛也。《涅槃經》六載日:“象喻佛性,盲喻一切無明眾生。”《廣弘明集》二十又云:“手擎四缽,始于鹿野之教,身臥雙林,終于象喻之說。”可見象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地位。
在漢畫中也有騎象畫像,如山東省鄒縣黃路屯等地出土有“乘象”漢畫像石,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的壁畫中發現有“騎象”圖像。這些畫像有可能是漢代百戲中的一種“舞象”活動,也有可能就是東漢佛教徒所舉行的“行象”活動。雖然至東漢明帝永平十年,“佛教作為一種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認崇信,在中國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礎和規模”(趙樸初),但是《佛教史略》對于當時佛教徒是否舉行“行象”活動,由于漢代文獻缺少這方面的記載而不能確認,只能推測這些畫像很可能為佛教的“行象”活動。
南陽漢畫中具有佛教因素的圖像
南陽漢畫中反映佛教內容的畫像多以大象、獅子、蓮花等為題材。
在南陽唐河郁平大尹馮孺人墓北側室,有一幅“乘象”圖。其內容為:畫中刻一象,體碩壯做緩行狀,后肢及臀部未刻出,象背之上有二人,一人面向右,跽坐,一人仰臥,兩腿上翹,悠然自得。
南陽漢畫中有許多以伏象、馴象、戲象為題材的作品。南陽英莊出土的畫像石也有人命名為“獵象”圖,說是一人持利鉤正從象身后套取象牙。象為菩薩前身,佛門神獸之一,是佛家惡來善往教化的象征。《涅槃經》曰:“象喻佛性,盲喻一切無明眾生。”《廣弘明集》二十四:“手擎四缽,始于鹿野之教,身臥雙林,終于象喻之說。”象威力巨大,性情柔順。因此經中時常贊美大象,六牙白象更為佛國象中之寶,許多佛教典籍都有記載。據《因果經》等載,釋迦牟尼從蔸率天宮降生于人間時,乘六牙白象,其母摩耶夫人晝寢,夢六牙白象來降腹中,遂生釋迦牟尼。《異部宗輪論》謂:“一切菩薩入母胎時,做白象形。”《普賢觀經》等說乘六牙白象王,若觀念慘悔,菩薩即乘六牙白象為其顯身。東漢時所譯《修行本起經》謂“白象寶者,色白紺目,七肢平峙,力過百象”。這種六牙白象被賦予神圣的色彩,是佛傳中崇拜的神物。
有關獅子形象的畫像,在南陽漢墓中發現有十余幅。如1989年4月南陽縣辛店鄉熊營畫像石墓墓門東門楣上的“武士斗獸圖”,畫面分為左右兩組,左面一組刻一熊,張牙舞爪,中部為一前撲獅子,昂首揚尾,頭上鬃毛高蓬,獅口大張,前肢著地,后肢騰空,似與右側異獸搏斗。再如南陽縣出土的“獅與異獸”畫像石,獅子與異獸角抵決斗,威猛無比。南陽市出土的東漢畫像石“獅、虎、異獸”圖,獅子舞爪戲虎,盡顯王者之風。
西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楞嚴經》日:“我與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阿羅漢。”獅子作吼,群獸懾伏,“獅子吼”成為佛家說法音聲震動世界的代名詞。獅子形象威猛,氣勢凌厲,為萬獸之王。所以獅子被喻指為佛的唯我獨尊,佛法即如同獅子一樣,供奉獅子可辟邪護法。在佛教中獅子是教乘高的神人的坐騎。
漢代獅子多被神異化,在南陽漢畫中,獅子多作祥瑞之獸出現,以能辟邪祓除不祥。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一種神獸“辟邪”是印度梵文的音譯,意為大獅子,因而,辟邪的造型也就以獅子為藍本,似獅但肩生兩翼。這樣一來,外來的真正獅子也使其神異化,成為神獸、瑞獸,人們把其作為吉祥物、守護神、鎮墓神等偶像頂禮膜拜。
南陽漢畫中獅子的特點是身材高大威武,頭大且圓,尾巴細長。值得注意的是,南陽漢畫中對獅子的形象描述筆調笨拙,“似馬非馬,似虎非虎,所不同的只不過鬃毛長一些罷了”。這可能與這些佛教動物剛傳人內地不久,數量少,刻繪者所見極少、觀察不足有關。
1986年、1993年南陽市文物研究所發掘的唐河馬振扶漢墓和桐柏縣安棚漢墓兩座東漢晚期畫像石墓皆刻有蓮紋蓮子的頂蓋。1991年10月,南陽市文物工作隊發掘南陽市第二化工廠二十一號東漢畫像石墓時,發現了一塊蓮花垂石,主體部分呈四棱臺形,圓形頂部,用陰線刻成蓮花狀,此石為墓頂嵌石。蓮花蓮紋多為佛教造像使用。這些南陽漢墓墓頂蓮花、蓮紋頂蓋有可能是受佛教影響所刻意人為。
漢畫中的佛教畫像,是我國古代用石刻畫來表現宣傳佛教的開始階段。伴隨著佛教影響的擴大與普及,到南北朝隋唐之時,宣傳佛教的石窟摩崖造像到處出現,給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宗教文化遺存。
作者單位:河南省南陽市漢畫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