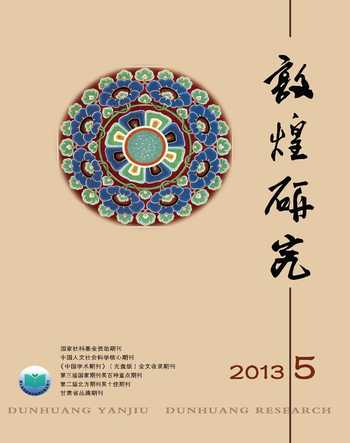大谷文書中十三則《千字文》殘片之定名與綴合
內容摘要:對于大谷文書中的《千字文》寫卷,國內外學者多有關注,但未能網羅無遺。筆者在翻閱《大谷文書集成》過程中,新認定了前人未曾定名或未能準確定名的《千字文》殘片13片,并與其他《千字文》寫卷之間的關系略作梳理。同時,就部分前人已認定,但有進一步研討必要的寫卷,也略作探討。
關鍵詞:大谷文書;《千字文》;殘片;考辨
中圖分類號:G2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3)05-0067-06
Naming and Joining Together the Thisteen Fragments of
A Thousand Words among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he Otani Collection
ZHANG Xinp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Cultur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 The manuscripts of A Thousand Words from the Otani Collection have gained extensive attention, though still incomplete. While reading the collection of the manuscripts from the Otani Collection, the author newly identifies 13 fragments that were previously unidentified or imprecisely identified, and then compares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other already identified ones and addresses the relevant problems.
Keywords: Manuscripts from the Otani Collection; A Thousand Words; Fragment; Textural research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收稿日期:2013-01-20
作者簡介:張新朋(1979- ),男,河北省灤縣人,浙江工商大學副教授,主要從事敦煌吐魯番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
20世紀初日本京都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三次組織“探險隊”進入我國新疆和甘肅地區“探險”,對新疆的交河故城、哈拉和卓(二堡)、阿斯塔那(三堡)、吐峪溝及甘肅的敦煌等地的古墓、石窟寺和古遺址進行盜掘,獲取了數量眾多的敦煌、吐魯番文物,其中以吐魯番文書為大宗。大谷所得品大部分入藏西本愿寺主辦的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除此而外,探險隊成員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的藏品也入藏龍谷大學。上述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所藏文書,學界稱之為“大谷文書”。到目前為止,已分類編號的有10668號[1],以《大谷文書集成》(以下稱《集成》)為題,由日本法藏館分4冊刊出。
在這一萬多號出土文獻中,有為數不少的《千字文》寫卷。對于這些《千字文》寫卷,前賢時彥多有研究,舉其要者,如唐長孺《跋吐魯番所出〈千字文〉》(《唐研究》1995年第1期)、張娜麗《西域發見の佚文資料——〈大谷文書集成〉所收諸斷片について》(《學苑》第742號,2002年)、王素《敦煌吐魯番文獻》(文物出版社,2002年)、劉安志《〈大谷文書集成〉古籍寫本考辨》(《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1期)、陳國燦等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張娜麗《西域出土文書の基礎的研究——中國古代における小學書·童蒙書の諸相》(汲古書院,2006年)及筆者所撰《吐魯番出土〈千字文〉殘片考》(《文獻》2009年第4期)等論著。據筆者統計,截至目前,諸家已認定的《千字文》寫卷有25件①。然吐魯番文獻多有首尾不全的斷章殘篇,甚至只有只言片字,《集成》沒有刊出全部圖版及研究者自身條件等諸多原因的限制,我們并未能將其中的《千字文》寫卷網羅無遺。筆者在翻閱《集成》過程中又新認定《千字文》殘片13片,并就它們與其他《千字文》寫卷的關系略作梳理,今整理成文,示之同好。另有3片前人已認定,但仍有進一步商討的必要一并討論,請大家批評指正。
1. 大谷3524
首尾及上下皆殘。正面存1行,書“尹佐時”3字,有朱點句讀。《集成Ⅱ》題“性質不明文書小片”[2],《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以下稱《總目》)題“文書殘片”[3]。今謂本殘片所存之字出自《千字文》“磻溪伊尹,佐時阿衡”(字下橫線者為參照文本與殘片所存相對應之文字,下同)句,故此殘片當題作“千字文殘片”。又,本殘片之文字與下文第2則提及的3550、3576、3578、3313號等《千字文》殘片字跡頗似,再參之以朱點句讀,頗疑本片與上揭殘片為同一寫卷,然因大谷3524號所存字過少,未敢遽斷(圖1)。
2. 10293(A)+10293(C)+?+3550+3575+3576+3578+3981+3313+3686+3581
(1)大谷10293號,《集成Ⅳ》未提供圖版,《釋文》說明文字云A號存“客”字1個,B號為兩面無字的殘紙一小片,C號存墨痕,但無法判讀。其中,A號《集成Ⅳ》題“性質不明文獻斷片”[4],《總目》未載此件。今據IDP數據庫所載圖片來看,大谷10293(A)號所存之字為“容”,非《集成Ⅳ》所說的“客”字;此外“容”字前后尚各存文字殘跡1行,其前1行文字似“如松”2字,后1行無法據殘跡復原。今謂大谷10293(A)號所書為《千字文》“似蘭斯馨,如松之盛。川流不息,淵澄取映。容止若思,言辭安定”等句,故大谷10293(A)所抄文字當定名為“千字文殘片”。又,同號之C所存之墨痕,經比對,發現它與大谷10293(A)左下角之殘跡相吻合,當是由大谷10293(A)脫落的殘片。至于不存文字的大谷10293(B)號,筆者懷疑亦是由大谷10293(A)散裂的小碎片,不存文字。又,大谷10293(A)+10293(C)上所存之文字,與筆者此前綴合的大谷3550、3575、3576號等《千字文》殘片②字形頗似(參看大谷10293(A)號“容”字、大谷3550號“定”字和大谷3575號“守”字所從之“宀”,大谷10293(A)號“容”字所從之“口”與大谷3550號“言”、“辭”2字之“口”等等),行款相合(行12字),乃同一寫卷之裂片,可以綴合。大谷10293(A)+10293(C)位于大谷3550號上方,二者銜接的2行之間各殘缺2字,分別為“之盛”和“若思”(如2)。
(2)大谷3686號,《集成Ⅱ》未提供圖版,《釋文》云存“圖□”、“田”3字,2行。《集成Ⅱ》未予定名[2]140,《總目》題“文書殘片”[3]197。今由IDP數據庫可見此殘片,知其第1行“圖”下之字似為“寫”字之殘;第2行存2字,首字略有漫漶,然與《集成Ⅱ》所錄之“田”略有差距,細審原卷字跡,當為“甲”字;其下之字僅存右上角殘跡。今謂此殘片所抄文字出自《千字文》“圖寫禽獸,畫彩仙靈。丙舍傍啟,甲帳對楹”句,故本殘片當定名為“千字文殘片”。又,本殘片亦與上文提及的大谷3550、3575、3576號等《千字文》殘片字形頗似,行款相合,它們亦是由同一寫卷散裂的,可以綴合。本殘片接于大谷3313號之下,二者銜接處有1字之隔,所缺文字分別為“驚”字和“啟”字(圖2)。
3. 大谷3700+?+10357(A)+?+3719+?+5127
(1)大谷3700號,《集成Ⅱ》未提供圖版,《釋文》云正面存“孔”、“測”、“秞”、“□”字,4行;背面存一“臣”字。《集成Ⅱ》未定名[2]141,《總目》正面文字題作“文書殘片”,同時亦提及背面的“臣”字[3]198-199。今據IDP數據庫所載該號圖版來看,本殘片首尾及上下殘,正面所存文字亦均殘損,然據殘跡,可知《集成Ⅱ》之錄文不盡準確,如第2行之字,顯然是從“忄”之“惻”,而非“測”;至于“秞”字,單純依據殘形,無法確知為何字之殘,“秞”乃整理者臆補。今謂《千字文》有“孔懷兄弟,同氣連枝”、“仁慈隱惻,造次弗離”、“性靜情逸,心動神疲”、“堅持雅操,好爵自縻”等句,本片正面之文字即上揭《千字文》文句中“孔”、“惻”、“動”、“神”、“縻”等字之殘跡,故本殘片正面之文字,當定名為“千字文殘片”。至于本殘片背面之“臣”字,從書跡上看,與大谷10357(A)背面、大谷3719背面之文字十分相似,當出自同一人之手。而《毛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十月之交》篇“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等句之注解中有毛傳“月,臣道”,鄭箋“臣侵君之象”、“君臣失道”,孔疏“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等12處含“臣”字文句,本殘片背面的“臣”字,當是上揭諸“臣”字之一,然具體為哪句之“臣”,暫時無從判斷。如上所述,本殘片背面,亦當定為“毛詩正義斷片”。
(2)大谷10357(A)號,殘片,首尾及上下皆殘。背面存殘文2行,為《毛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十月之交》篇“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等句,孔穎達正義之文字[5],《集成Ⅳ》定作“毛詩正義斷片”[4]147,甚是。正面存殘文2行,《集成Ⅳ》分別錄作“ □嘉猷□ ”和“腦林。罪□”,有朱點句讀。《集成Ⅳ》題作“性質不明文獻斷片”[4]147;《總目》未著錄此件。今謂本殘片正面文字出自《千字文》,《千字文》“貽厥嘉猷,勉其祗植”、“殆辱近恥,林皋幸即”等句,可參,故本殘片正面之文字當題作“千字文”。據文字殘跡并結合《千字文》文本可知,第1行首尾處所存分別為“厥”字和“勉”字殘跡;第2行行首所存為“恥”字殘跡,《集成Ⅳ》錄作“腦”,誤;同行第3字乃“皋”字俗書,《集成Ⅳ》錄作“罪”,非是。
(3)大谷3719號,殘片,首尾及上下皆殘。正面存殘文2行,分別為“ □招□渠 ”“ □委翳 ”,《集成Ⅱ》定名為“楷書千字文小片”[2]142,《總目》題“楷書千字文殘片”[3]200,均是。殘片背面之文字,《集成Ⅱ》未予錄文,《總目》亦以“背面存2行數字”一筆帶過,并未深究。本殘片背面存殘文2行,第1行存“ □□陽 ”,第2行存“ □之義 ”[2]143。今謂本殘片背面之文字,源自孔穎達對《毛詩·小雅·節南山之什·十月之交》篇“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等句的疏證“是陰侵陽也”、“日辰之義者”[5]843二句,故背面內容當定作“毛詩正義斷片”。
(4)大谷5127號,殘片,首尾及上部殘。正面存殘文3行,第1行,存某3字左側殘跡,第2行存“□年始”3字,第3行存某2字右端殘跡及旁補之字1個(《集成Ⅲ》錄作“家”)。本殘片《集成Ⅲ》題名“佛典斷片”[6],《總目》題“佛典殘片”[3]333。今謂本殘片正面所抄文字源自《千字文》“恬筆倫紙,鈞巧任釣”、“毛施淑姿,工嚬妍笑。年矢每催,曦暉朗曜”等句,故正面之文字當定名為“千字文殘片”。其中“矢”字,本殘片作“始”,“始”當為“矢”字音近之訛①。又,據殘跡,并結合《千字文》文本可知,本殘片第3行所存乃“指薪修祜,永綏吉劭”句中的“祜”字和“綏”字,而“綏”上之“永”字漏書,遂旁補于右側,即《集成Ⅲ》誤錄作“家”者。
殘片背面存殘文2行,從右至左依次為“ 也”、“ 故不”。今觀其文字,與上述大谷3700、10357(A)、3719號背面之文神似,經查,其為孔穎達正義“追及于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里,故不食”[5]842句中之文字,故本殘片背面之文字亦當定名為“毛詩正義斷片”。
今按:上揭4則殘片,書風相似,正面與正面、背面與背面所抄內容均屬同一文獻,行款相近(行18字左右),來自同一寫卷自是無疑,四者可以綴合。依《千字文》文本之順序,大谷3700號居首,大谷10357(A)號次之,二者之間缺起“都邑華夏”訖“鑒貌辨色”72句288字,以行18字計,殘缺16行;大谷3719號位于大谷10357(A)號之后,二者之間缺自“林皋幸即”之“即”至“戚謝歡招”之“謝”31字,以行18字計,殘缺約2行;大谷5127號則位于大谷3719號之后,二者之間缺自“落葉飄搖”句之“葉”至“恬筆倫紙”之“紙”151字,以行18字計,所缺在8行左右(圖3)。
4. 大谷4489+3278
大谷4489號,殘片,《集成Ⅱ》未提供圖版。《釋文》錄正面文字作“ 彼子比見 ”、“ □□ ”;背面文字為“ 待維愍□ ”、“ 德□ ”[2]262。本殘片《集成Ⅱ》置于“佛教關系、其他小斷片”[2]257之下,未給予具體的題名;《總目》題“文書殘片”[3]268。今據IDP數據庫得見本片之圖版,發現《釋文》之文字訛謬較甚,如:“彼”當作“猶”、“見”當作“兒”、“待”乃“行”字之誤、“愍”則“賢”之訛,等等。今據圖版,可知本殘片所抄文字源于《千字文》“景行維賢,克念作圣”、“空谷傳聲,虛堂習聽。禍因惡積,福緣善慶”、“諸姑伯叔,猶子比兒”、“仁慈隱惻,造次弗離”等句,故本殘片當擬題“千字文殘片”。又,本殘片與大谷3278號《千字文》書風相類、字形相似、行款相合(行20字左右),乃同一寫卷之裂,可以綴合,本殘片在前,二者銜接處基本吻合(圖4)。
5. 大谷10602(A)
殘片,首尾及上下均殘,正面存殘文2行:第1行存某3字左側殘跡,第2行存“□房”2字,有朱點句讀。《集成Ⅳ》題作“性質不明文獻斷片”[4]178,《總目》未著錄此件。今謂本殘片正面所抄乃《千字文》“飽飫烹宰,饑厭糟糠。親戚故舊,老少異糧。妾御績紡,侍巾帷房”等句,故本殘片正面之文字當定名為“千字文殘片”。
6. 大谷3930+10236+10378(A)+10378(B)
(1)大谷10236號,殘片,《集成Ⅳ》未提供圖版,《釋文》云第1行存某字習字3個,第2行存“本本”2字,第3行存某字習字1個。本殘片《總目》未著錄;《集成Ⅳ》定名為“習字斷片”,并指出與大谷10378號同卷[4]130。
(2)大谷10378號,殘片,《集成Ⅳ》未提供圖版,該號由2殘片構成,《釋文》以A、B區分之。《釋文》云大谷10378(A)第1行存“本”字1字,第2行存“本本”2字;大谷10378(B)則僅存一文字殘跡,《釋文》云是由大谷10378(A)第2行第1個“本”字左上方脫落的。上述兩塊殘片,《總目》未著錄;《集成Ⅳ》擬題“習字斷片”,并指明與大谷10236號為由同一文獻的不同殘片[4]150。
按:IDP數據庫載有上揭3殘片之圖版。據之,可知3殘片之“本”字,與大谷3930號“千字文習字斷片”之“本”字酷似,經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大谷10236號第1行末尾的“本”字所缺的下半,恰好位于大谷3930號第3行之行首,顯然四者來自同一寫卷,可以綴合(圖5)。由此,大谷10236、大谷10378(A)、大谷10378(B)自然亦當定名為“千字文習字斷片”。
7. 大谷4138
殘片,《集成Ⅱ》未提供圖版,《釋文》錄文為“ 大十 ”,本殘片《集成Ⅱ》擬題“性質不明文書小片”[2]207,《總目》題名“文書殘小片”[3]237。今據IDP數據庫之圖版,可知本殘片所存乃“本”字殘跡,《釋文》所錄“大十”2字,非是。又,本殘片與上文論及的大谷3930+10236+10378(A)+10378(B)“千字文”習字殘片之“本”字形體甚近,似出于同一人之手,或即由同一寫卷割裂而來。然因本殘片與上揭大谷3930、10236等殘片無法直接綴合,故暫且存疑。今附該號圖版(圖6),以供參看。
8. 大谷10506、3605
大谷10506號,殘片,《集成Ⅳ》未提供圖版,《釋文》云存“宜”字習字1行、“令”字習字1行和已漫漶的某字習字1行。《集成Ⅳ》題作“性質不明文獻斷片”[4]165,《總目》未著錄此件。今據IDP數據庫所載之圖版判斷,本殘片與大谷3605背面“千字文習字紙”所抄之“宜”、“令”字形一致,當出自同一人之手,或即同一寫卷之裂。大谷3605背面之文字《集成Ⅱ》題作“千字文習字紙”,那么,本殘片亦可定題為“千字文習字紙”。今附二者圖版(圖7、8),以供對照。
9. 大谷3602、3604與1451
(1)大谷3602號,殘片,首尾及上下皆殘。正背兩面書,正面存“之”字習字2行;背面存“無”字習字2行,其中,第2行僅存右端殘跡。《集成Ⅱ》定名為“千字文習字紙斷片”[2]130,《總目》題“《千字文》習字殘片”[3]191,均是,然未進一步探究與其他殘片之關系。今察大谷1451號“千字文習字”亦有“之”字,雖僅左半可見,但憑此我們足以判斷,其字形與本殘片正面所抄“之”字相同,二者當出自同一人之手,蓋由同一寫卷割裂而來。
(2)大谷3604號,殘片,首尾及上下殘。正背兩面書,正面存習字2行,抄“東”字和“宮”字;背面抄“所”字2行。《集成Ⅱ》定名為“千字文習字紙斷片”[2]131,《總目》題“《千字文》習字殘片”[3]191,均可,然亦止步于此。今將該號背面之“所”字,與大谷1451號“千字文習字”之“所”字相比對,我們可以發現,二者同形,當出自同一人之手。
如上所述,上揭大谷3602、3604、1451號“千字文習字”內容相合、書跡一致,三者出自同一人之手殆可無疑,抑或同卷之裂也未可知。今附三者圖版(圖9—11),以供比勘。
上揭對諸《千字文》殘片的認定、辨析,使這些《大谷文書集成》未定名或未能準確定名的《千字文》殘片的得以確認,我們對于大谷文書中的《千字文》寫卷有了更為全面的把握。就它們與其他《千字文》寫卷關系而展開的探討,則使我們對于大谷文書中的《千字文》的抄本體系有了更為明確的認識。這些均為大谷文書中的《千字文》的整理提供了新的信息,為大谷文書中的《千字文》的整理添磚加瓦。同時,我們的研究加快了大谷文書識別整理工作的進程,相關的成果可以為大谷文書收藏單位——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館藏目錄及其他吐魯番文書目錄類書籍所采用,提高這些目錄的指向性與有效性,為廣大學者更為方便有效地利用大谷文書提供幫助。
參考文獻:
[1]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154-166.
[2]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Ⅱ)[M].京都:法藏館,1990:117.
[3]陳國燦,劉安志.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184.
[4]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Ⅳ)[M].京都:法藏館,2010:139.
[5]龔抗云,李傳書,等,整理.毛詩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842-843.
[6]小田義久.大谷文書集成(Ⅲ)[M].京都:法藏館,2003:135.
① 大谷3601號正面存漫漶文字1行,《集成Ⅱ》錄作“ 須□□火 ”,張娜麗認為是“ 海咸河□淡 ”。今見照片,張氏之判讀與原卷字形有差距,故未予計入《千字文》寫卷總數。
② 《文獻》所載綴合圖,大谷3550、大谷3313號之位置排列未為盡當,且大谷3313號與大谷3981號之序號誤倒。
① “矢”《廣韻》音“式視切”,書母旨韻,“始”《廣韻》音“詩止切”,書母止韻,唐五代西北方音“旨”、“止”二韻相混,遂致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