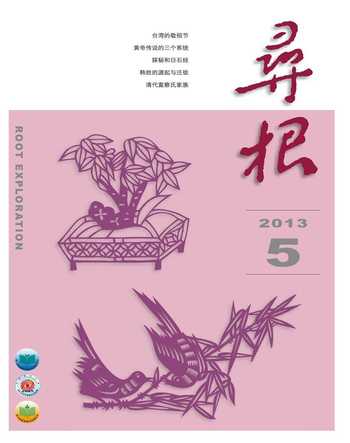走近丙中洛
沈堅



從地圖上看,丙中洛的位置就在云南省的西北頂端,再往北不遠便入西藏了。
游丙中洛,是當時我們整個怒江行游計劃的一部分。從六庫沿怒江筆直北行,中經福貢,抵達貢山。丙中洛所在的貢山,是云南西北端最邊遠的一個縣。縣城茨開鎮極小,僅一條縱街,跟怒江平行,卻五臟俱全,集中了必要的機構、商鋪、飯店、娛樂場所等。
貢山是個多民族地區,傈僳族居多,還有怒、獨龍、納西、白、回、藏、漢等族,正式名稱是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屬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所轄。來到這里,很快就會感受到一陣濃濃的民族風情。由于山隔水阻,人群的交往自然比不得平壩地區,少數民族群眾莫說中老年,即使不少年輕人,也還不諳漢語,只能以本族語言或通用的傈僳語交流。我們在茨開鎮的基督教錫安圣堂偶遇一群山區來的、去參加教堂舉辦的吉他訓練班的傈僳族小伙子,用漢語問了他們半天,竟無人能聽懂。然而他們卻學習西方傳入的洋樂器吉他,用以為基督教唱詩活動伴奏。基督教同當地民族的關系,倒是十分近切的。20世紀初,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便由一些來自內地或緬甸的西方傳教士傳人了怒江地區,相繼在部分少數民族中傳播開來,其影響之大,超乎我們的想象。據近年所作的調查,在有的傈僳族村莊,信奉基督教的人口甚至在村民總數的70%以上。
從貢山到丙中洛沿途,景色宜人,而最動人心魄的景致,便是日丹村附近的怒江第一灣。過了怒江第一灣,不多遠便駛抵丙中洛村頭了,抬眼可見一座高峰拔地而起,當地人稱貢當神山。丙中洛,在藏語中即意為“箐溝邊的藏族寨子”,四面青山環抱,傳說共有十大神山守護著它,東與響朗臘卡山和碧羅雪山隔江相對,西靠高黎貢山主峰、海拔5128米的格瓦卡普峰,南為貢當神山和日當坡,北邊又有石門關峭壁,形成“雪山為城,江河為池”的奇特自然景觀,有“又一個香格里拉”之稱。
別看村子不大,丙中洛卻“三教并存”,互不排斥,居民有信仰喇嘛教的,也有皈依天主教、基督新教的,甚至還有人依舊崇奉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神山崇拜則應是喇嘛教中保留的原始苯教的遺風。丙中洛一帶有喇嘛教寺廟,如普化寺、飛來寺、婁扯寺、香巴拉宮、巴瑪拉宮、福祿拉宮,有天主教的青拉桶教堂、捧當教堂、仲底教堂、白漢洛教堂,還有基督新教的普格勒山教堂等。
聽說丙中洛以北7千米處有石門關景區,不通汽車,于是我們決定步行前去。那是個多云天氣,即使陽光躲在云層背后,卻因海拔高,還是把人薰烤得夠嗆,加之爬緩坡,不多時,我們便一個個氣喘吁吁、面紅耳赤起來,臉上泛出當地人那樣的“高原紅”。一路沿怒江邊悶頭走路,不時可聞激越的水流聲響。
一直走了大約一個半小時,才到達石門關。這里隔江聳峙的兩座高大山崖,壁立千仞,幾達90度,極其雄偉,儼如兩扇天然關門,控扼著滔滔怒江。我們知道,過石門關再往北行,還有一個村子秋那桶,離西藏邊境就不遠了。
在石門關一帶的巖崖上,我發現了不少由遠古萬年巨樹的倒木演化成的巖石(硅化木),樹徑竟有十來米,令人咋舌。其植物紋理遺痕十分清晰,取其碎片,以手剝之,松脆易折。其成因可能同青藏高原喜馬拉雅造山運動有關,橫斷山脈的聯動抬升,或許導致了許多遠古巨樹被坍塌的巖流所吞沒,高溫高壓之下漸漸石化。又因江流切割和山體錯動抬升的劇烈運動的共同作用,這些古木形成的巨巖又在一些地段頻頻出露。
在從石門關返回丙中洛的途中,我們順便走訪了幾個小村,在重丁村(當地人稱甲生村)看到了一座天主教堂。整個建筑刷成白色,混凝土結構,拱門前留著一個廊廳,上方筑有鐘樓,橫一塊匾,書有“天主堂”字樣,頂端矗著十字架。風格簡潔,活脫脫一個鄉村教堂,只是門關著,無法進去看個究竟。
然后,我們又行至附近村落尋找喇嘛教的普化寺。在藏族老鄉的引領下,很快找到了一位怒族管寺人,帶我們入內參觀。讓人感慨的是,即使地域如此偏遠,該寺于“文革”期間仍未逃脫厄運。如今見著的土坯墻磚木結構建筑,已是恢復重修之后的了,顯露出簡陋的痕跡,自不能同那些金碧輝煌的藏傳佛教寺院相比。不過,普化寺的木質門廳留存下來的藏式彩繪和裝飾,依舊古樸如初,含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寺前空場立有幾根木桿,上纏白布條,是為經幡也。普化寺外觀雖不起眼,但聽管寺人說,每逢宗教祭典,四鄰八鄉信眾云集,還是不乏熱鬧景象的。
山環水繞的丙中洛,像個嬰兒似的安臥在大自然的懷抱里,久久隱匿于怒江大峽谷的深處,不為人識,不為世擾,難得天地之間一桃源。丙中洛的人們在四圍神山的護佑下,與世無爭,和諧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肉大家吃,有酒大家喝”,“路邊分肉,見者有份”,這種原初狀態下的生活習性和觀念,使它曾經是一塊未經現代文明侵蝕的純樸自然的凈域。然而,隨著時移勢易,電視、手機、互聯網這些對外窗口的打開,隨著愈來愈多的年輕人紛紛外出闖世界,隨著外面人流和躁動的持續涌入,丙中洛將如何應對這一切?它的山河草木、空氣流水,還能依舊靜謐潔凈嗎?它的生活品味、脈動節律,還能安之若素、一如往昔地前行嗎?
(題圖:俯覽丙中洛)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