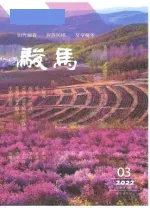本該霉爛在那片林子里的事情
劉長慶
呼倫貝爾人,內蒙古作協會員、呼倫貝爾作協理事、哈爾濱鐵路局作協理事。中篇小說《草地狼》《山隼金羽》《興安之巔》在《青年文學》《駿馬》《興安杜鵑》等雜志發表。曾獲呼倫貝爾市文學藝術創作政府獎(駿馬獎)。著有小說集《草地狼》。
進入獵場,瞎蠓和大個兒的紫頭蒼蠅迅速均分七組,追隨被太陽暴曬的獵手們,一路纏繞踅旋,伺機還要狠狠地叮上他們一下子。蹚開一米多高的荊棘叢,在周邊攪鬧不停的嗡嗡聲中,繃緊神經,克制所有干擾地悄然潛入,獵手間的橫向間隔在百米開外,搜索中保持圍獵陣型,警覺觀察,細心聆聽,要不是有這個神癮,這種罪也實在不該是人愿意受的。
圍獵是俄羅斯貴族打法,后來他們走了,沙沙、多尼、烏爾加,聊起當年的獵友,張志砧八十歲的老爹還能講得頭頭是道。在鐵路,無論從事什么工種,都不可能扔了行當,鉆進林子好幾天,這種多見于禮拜天乘林區小火車抵達獵場的圍剿,全當是獵手的節日。我是去年仰仗張志砧在其中的威望入伙的,當時,傲慢的老家伙們只肯對我父親留下的那桿五連發的比利時老槍充滿敬意,幾乎視我為無物。
狍子六月皮毛起紅杠,活動范圍貼近水源,46號主峰以南的各路狍群慣于黎明下山,飲罷綽爾河谷溪流,整個白晝都不肯隱歸山林,它們趴在漫灘以外的半岡,寬闊的溝底,一叢叢密匝的小灌木,谷口涼風襲來,嫩葉翠綠芬芳,瞎蠓蚊蚋相對也少,是理想的夏日行宮。
獵手每腳落步都擔心聲音過大,偽裝得好時,貼近狍群三十米以內,能聽到灌木叢里活潑的狍子崽兒撒歡的嬉戲聲。我始終處于扇形編隊的最邊角,半岡以下貼近河谷的一邊,驚起的狍群多半沖上山肋或回身后逃,奔往河邊的概率比我開槍的幾率都小,多尷尬的位置啊。
貼近前方一排幾十棵小白樺形成的林子時,槍響了!張志砧老爹給他裝的子彈從12號虎頭立管里擊發,嘎嘎脆,我聽得出來。如果不搶在狍子起跑時屁股上翹的幾個躥高打倒它,它馬上就會拉開矯健的身姿,借助灌木叢的遮蔽,瞬間逃到射程之外。
“砰砰!”這是鐵路二中吳佩玉老師打16號彈的鷹牌平管的聲音。隨即他向被樺樹隔住視線的我吆喝:“劉長慶!開槍!”
容不得眨眼,一對兒金紅的狍子沖進了林子!蹽開的四蹄不再有乍起時的彈跳,公母昂揚的頭顱形同交頸,看似輕車熟路,飄逸的脊背在小灌木的葉梢上忽閃。獵場里的雙管獵槍依然雙擊不停地射擊炸了窩的狍群。沒人瞧得見,反倒放得開了。我側閃一步,給目標一個略寬的林間縫隙,瞄準狍子的脖頸打了一槍。霰彈讓前方二十米開外的灌木枝梢碎葉旋飛,母狍子似乎驚恐地向前絆了一下,但奔跑的速度絲毫未減。真是隔枝不打鳥哇,這一槍沒抱希望。狍子闖出樺林,頓使我眼前開闊,迅捷地勾響扳機。子彈雖未受矮樹梢子影響,卻又沒打中。領跑的大公狍身形矯健,它率先直奔半岡以下的一條堿草叢生的低洼山地,拉開的距離看似已超出霰彈的有效射程,一次沖騰就接近十米的跨越,幾步就會鉆進小灌木向小喬木過渡的河谷,一切也就結束了!
我急瘋了!動用了最后的不使情緒失衡的耐性,和平日里反復演練揣摩過的速射的動作感知,克制飛馳的獵物因瞬間改變的距離而瞬間造成的心理壓力,穩穩地向凌空上躥的大公狍子的腦袋打了最后的一槍。
“嘎——”
這一槍余音泛濫,整個地球仿佛都被攪亂得緩滯了自轉!我再切實不過地感覺到從槍口噴薄出的火藥如何緩慢地推迭正面的空氣,繼而形成的慣性撞痛了我瘦削的肩胛;辛辣刺鼻的硝煙,火狐貍放屁般蕩滌,將大瞎蠓驅離并定格于這一范疇之外;從槍膛蹦出來的那枚銅質彈殼,一圈圈翻轉,在我眼角的余光里款款下落;還有那只被霰彈穿透了頸椎的大公狍子,我全過程地看見了它在空中完成了優雅的死亡轉體,一屁股砸進了洼地的水坑,把被正午陽光曬熱了的一汪溫水,盡數地拋向了熱辣辣的天空。隨后,它試圖掙扎著爬起來,但即便強悍的四蹄已經撐起了整個身軀,腦袋卻像與大地焊接了一般的牢牢粘連。環繞水坑的長堿草,掛滿了從坑底擠壓翻掀出的腐爛的敗葉和黏糊糊的蟾蜍卵;更往上的天空中,一對赤麻鴨舉展著沉重的翅膀,笨拙地拔高。一切都結束了!
慢鏡頭似的過程里,大公狍子成了我的獵物,我也以為自己由此成了一個真正的獵手。
吳佩玉不再用獵刀豁開彈孔,挖出并炫耀那粒因擊發和空氣摩擦造成瞬間高溫而凝固了一層黑血漿的,我用內燃機車保險電阻熔制的軟鉛彈!他憑吊似的拄槍兀立,撓撓腦門長滿粉刺的少白頭,問張志砧:“你前年打那個,有它大吧?”“骨架差不多,沒這個壯。這家伙,跳起來的時候,我當是頭鹿吶!”
接下來的跋涉,沒再蹚起目標,直到下午,施宏圖才打了只小角不超三寸的二歲狍子,我那天一雪前恥,心花怒放。二十歲以前,偶有得意忘形之際,不惹出點兒亂子是不甘心的。
我們前往峁嶺養路工區,在那里搭乘返程的小客車。途經知青的撂荒地,瘋長的蒿子遠大于種植的密度,沒有比這種堿蒿揮發的氣味更惡心人的了,大家一路甩不凈噴嚏、眼淚、哈喇子,好歹逃離這要命的熏嗆,卻發現以往的休息地、知青點以及房后的山肋上,縹緲著夏季水分充盈的樹葉燜火時特有的藍煙,升騰繚繞。
顯然,巴氏桿菌的蔓延讓養鹿人不得不在此暫且停留,從木障子上曬著的幾張半干皮子斷定,趕鹿人目前的損失還不是很大。被隔離的病鹿們分趴在當年用錚錚誓言培植的青松下茍延殘喘。臨時的家,大人在后山照不了面,連大狗似乎都去應付局面了,半塌的狗窩里酣睡著一堆黑白花居多的肥胖狗崽兒。沒人肯向一個多說五歲的小女孩打招呼,滿院子看家的只有這么一個小童,而她亦對這伙帶槍的人視而不見,只管把小手里緊攥的一把馬蘭草在泥濘的八瓣蹄窩子上沒橫沒豎地插著。
從那口即使在夏季底層也掛冰溜子的轱轆井里搖上煞涼的水,暢飲,灌壺,痛快地洗臉洗頭,給暴曬了一天的身體降溫。距鐵路很近了,大家習慣在這里分解獵槍,裝進槍衣。
剛點上煙,吳佩玉就詭異地湊過來借火。“噯,把那個狍崽子抱走吧?”他向我斜一眼。
我這才看到那個小家伙。哈哈!它太小了!小到也只能用小時來估算它出世的時間,要是用天算,多說是主人昨天早晨從林子里抱回來的。它安靜地趴在敞開的門后一副扭曲了的馱架旁邊,偏墜的太陽,照耀它梅花鹿一樣美麗的斑點,周身散發著似錦的胎光。
剛下生的小狍子,不經一場雨淋,就不會奔跑。去年帶小外甥打野鴨子,也撿過一個,當時我倆走在帶套子的馬車軋爛了的山道上,各踩一條車轍侃侃而談,它就趴在那兩條坑坑洼洼的深溝中間的草窠里,不經意間,我和小外甥都擦身走過好幾步了,才不禁相視大笑,回身就把它抱了起來……
我那年超不過二十歲,一肚子花花腸子,一腦子的歪門邪道,無論按當時實際的場景還是今天形成文字的過程,都不能把以下行為抵賴于吳佩玉的蠱惑,一眼看去,我便心生攫念!
打量整個院子,兩堆驅散蚊蚋的青煙蕩滌飄渺,與半山腰溝塘子里的煙幔遙相呼應。敞開的房門,屋子里灰暗到勉強看到灶臺上的一只鋁壺,窗是關的。從門框扯出的知青晾衣服的八號鐵線,擰牢的另一端已深嵌入那棵松樹的樹干,幸好還沒被勒死。長長的拉線只掛了根紅領巾似的布條,難道還有更大些的孩子?如果有,肯定不例外地去后山啦!況且,馴鹿脖上有時候也系過差不多的紅繩,我見過的!小女孩依然蹲在那里,心無旁騖地做著自己的事情,被太陽暴曬又蹭了些許泥巴的皮膚照樣粉白嬌嫩。她穿一件肥大的篩網般粗糙的硬布坎肩,看上去很是辟邪,到此也沒有一只瞎蠓打擾過。尤其是那雙樺樹皮縫制的小拖鞋,得體又合腳,以至于三十年后我幾乎走遍了呼倫貝爾林區,在放養馴鹿或狩獵部族的各類生活物品乃至工藝品展示里,再沒見到過這個貼切到足以令心失落的文化物件。小女孩自始至終都沒抬眼皮,跟頭發一樣反射出淡淡栗紅色光澤的細密的長睫毛,一直向腳下那一小塊意猶未盡的區域眨動,讓人沒法看見她的眼睛。被隔離的病鹿情況的確很糟,它們眼球突兀,目光呆滯。挨近了也感覺不到以往那種熱烘烘的反芻。嘴巴和鼻孔誕漓出血色的粘液,不知怎么,公馴鹿皮下組織布滿紅疹的腫脹睪丸,一下子讓我聯想到了吳佩玉的爛腦袋。
沒時間開玩笑——該下手啦!先要避開張志砧,他總是那么循規蹈矩!
可憐的小狍子啊,快讓我帶你離開這瘟疫橫行的鬼地方吧!森林鄂溫克只跟馴鹿親,壓根兒就不拿你當個稀罕物!你將很快被傳染疾病,早早完蛋!走吧,你將成為我們的明星!
我只等獵手們收拾利索,陸續動身離去時,掏出獵袋里的大雨衣,往趴得老老實實的小狍子身上一蓋,卷個滾兒就夾在了腋下,起身就走。
“啪啦!”那扇窗被充斥了怒火的壓力鼓開,一個字像子彈打上鋼板,鏗鏘飛來:“賊!”
天哪,竟然這么叫我。此前從未有過!盡管鉆進塑料大棚偷過西紅柿,擔當貨物列車運輸的乘務中偷瓜,用小口徑步槍擊斃了咬過我妹妹的狗,甚至敢進院子把它拖出來!在圖書館看紅眼了也不太檢點……可沒有人敢說我是賊啊。賊!這個字瞬間把我狠狠地釘在原地,半步都邁不動了!
那是我活到當時最羞慚的一個面對。她顯然是她的姐姐,那條在鐵絲上飄忽的紅領巾的主人。目光碰撞的一刻,她問:“誰讓你們到山上來的?”這話看似不夠損,實則要人命!簡直就是對森林之子的徹底否定!老子也是有獵槍證的!但一時間又沒法從嗓子眼里掏出什么來回應,我尷尬地解釋:“小姑娘說什么吶——我們是——獵人。”
“獵人?偷東西的獵人?”這丫頭漢話說得特溜,且還咄咄逼人。我站在那兒,被剝蝕得形同夏季里掉光了樹葉且還爬滿了毛蟲的一棵死樹,趕快把小狍子放下來啊,可心都這么想了,人卻一時間麻木得只會賭氣了,我覺得心臟“怦怦”地跳,鼻孔“呼呼”地喘,像染上了巴氏桿菌的鹿。她沒容我把小狍子放下來,接下的做法足夠羞辱我半輩子,她一字一頓地告誡:“把我的小狍子撂地下!”同時悄然抬起手,細瘦的臂彎里現出陳舊的槍托,我立刻確認那是他們當時最普遍用的7.62毫米的后坐力極大的老式納甘步槍。
我從沒被人逼到如此丟人的精神死角,站在這兒的若是她父親,我相信這足以讓我跟他決斗!可在這個年紀不過小學三年級的女孩面前,怎么表達都無法維系體面。
“長慶!快給人家撂下!”張志砧沖來搶雨衣,我使勁一聳,掙開他的揪扯,屈辱的一幕必須要有了。我辣辣的眼睛直盯著她,故作不卑不亢地把小狍子撂在地上,魔術師般地將大雨衣一抖,搭在肩上回身就走。
第二個周末,我從好幾年不曾觸摸的一炮彈箱子的小人書里,挑選出最經典的十本,放入獵袋。可那戶鄂溫克人家,再沒進駐過46公里的知青點。
時隔近三十年,早沒人打獵了。我卻依然對大森林情有獨鐘,在它的氣息里如癡如醉地過活。文友之間那種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常讓我光顧小區拐角的一家山貨店,松菇、柞木耳、樺樹淚什么的,貨真價實又稱心。經營它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士,每次登門都熱情親切,有一次東西給的太便宜了,感激之中想客套幾句,僅憑長相便貿然相問:“你是鄂溫克族吧?”
她哈哈哈哈哈,笑得我一頭霧水,“大哥,你不認識我啦?”
我記人特扎實,所以沒加猶豫,肯定地搖頭。
她依然嘻嘻哈哈地提示:“那你還記得不?森林小火車,46公里,那個知青點!”
我使勁想啊想,越發懵懂了。
她好像格外愿意看我那個囧樣,再加提醒:“你要抱走那只小狍子!”
“天吶!”我使勁地拍打腦門兒,“我想起來啦!”她讓我一下子回到了那一天的羞臊!我大紅著臉,勉強地問:“你就是那個推開窗戶,端著一桿大槍吆喝我的小姑娘吧?”
她再次笑得前仰后合,美妙絕倫地送給我四個字:“那——是——我——姐!”
責任編輯 烏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