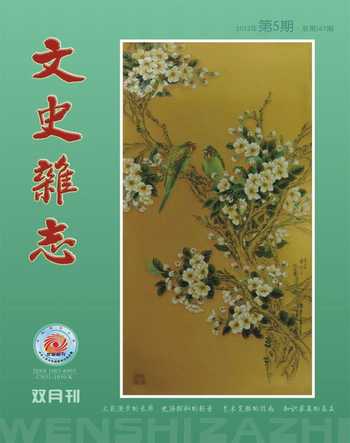一管畫筆寫忠憤
李建友
四川內江籍愛國大畫家張善子,為民族抗戰厥功至偉,英年早逝時,正值中國人民抗戰進入最艱苦階段,其人其事及藝術影響,受戰事和歷史局限,國人知之甚少。關于研究他的專著,幾為空白,實為憾事。
2012年11月,被譽為研究“大風堂的推手”、張大千紀念館原館長汪毅的又一力作《一門虎癡:張善子、胡爽盦、安云霽》(以下稱《一門虎癡》)由四川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將這一憾事彌補。此著立意高遠,史料翔實,以張善子多彩藝術,對抗戰文化的貢獻、國民外交、“大風堂”畫派文脈傳承等為主線進行梳理、整合;以大多為首度公開的450幅圖片和文獻資料加以詮釋。其意在“復原”這位為“國民精神之振奮而付出而大聲吶喊的藝術大師”,復原走過近90年歷史的大風堂原貌。這使得《一門虎癡》具有了包括美術流派、抗戰文化史、近現代中國美術以及內江地域文化等方面研究的權威性、唯一性和文獻性。
世人認識張善子,皆因他的虎畫所產生的氣場太大所至。其實,他是一位用心至深、用情至深,具有全面修養的藝術大師,有“近代黃山畫派始祖”“繪虎大師”“中國真正的愛國大畫家”等譽稱。
張善子創作的抗戰題材作品,除追求其畫作的美感、意境外,大多凸顯的是精神,是一個時代,一個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民族至上的偉大情操。如在《忠心報國圖》中,他通過黑白兩匹駿馬的塑造,展示出生命般的靈動活力和氣吞山河的力量。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在該圖上題寫“寓意精深”四個字以嘉勉。該圖在法國募捐巡展印刷時的說明文字:“駿馬,對祖國忠誠的象征”,亦是對張氏昆仲人生信條及創作思想的最好詮釋。
張善子以大量虎作作為自己傾吐愛國情懷的載體,以虎作寄托精神和心跡,為國家為民族疾呼;以震懾群山之威、長嘯山林之虎,喻示中國人民剛毅意志不可阻擋!其所創作的抗日內容國畫,開美術界抗日宣傳之先河。
作為一個文化人,國難當頭,張善子雖然不能執戈于疆場,但卻堅持將手中的筆變成救國救民族的“利器”,畫出了異彩。其心語“發揚民族正氣、發揮民族抗戰力量”在扛鼎之作的《正氣歌像傳》及系列古代民族英杰畫作中得到最大釋放。其鼓動意識,猶如號手吹起發動沖鋒的號角,震動了國人。當時最高領導蔣中正在該圖上題“正氣凜然”四字,并命其屬下“將其懸掛于中央政校,鼓動諸生”,以正民族之氣。該圖于抗戰時期巡展于全國若干城市,可謂婦幼皆知。該圖被帶到抗日前線戰壕中,供官兵們傳閱,“昂揚了民族精神,甚至對其后于1939年3月國民政府頒發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的出臺,具有先導意義與不可低估的催生作用”。由此,汪毅還感慨:“對中華民族抗戰,我們銘記的不僅有臺兒莊大戰、平型關大捷,還有張善子《正氣歌像傳》的磅薄力量”,“具有協調中美關系和捍衛釣魚島主權的現實意義”。
1938年底,張善子攜畫行走歐美,募捐抗戰,救濟難民,表現出一股中國力量,張揚出中國人的精氣神。他奔走于法國國家博物館。法國總統仰其藝術,親自為他授勛。他走進美國的白宮,參加在紐約舉辦的“世博會”,宣講、募捐、展畫于各大學及社團。他贈《飛虎圖》給美國援華飛行隊,后被美國國家博物館珍藏。當年為巡展而繪制于紐約的另一幅《飛虎圖》,被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經輾轉,現已被成都建川博物館收入抗戰館中。2012年5月28日,美國空軍在華盛頓市郊的空軍紀念碑前舉行了一次特殊的紀念儀式,以紀念援華飛行隊——“飛虎隊”成員幫助中國人民抗戰作出的貢獻。《飛虎圖》及“飛虎隊”銘刻的是中美兩國人民用鮮血和生命鑄成的友誼。當年歐美之行,張善子共募得20萬元,如數匯給祖國,救時濟民。時國民政府和行政院分別為張善子頒令褒揚。在民國史上,獲如此頂級的獎勵,在畫家中堪稱第一。張善子被譽為“第四戰場——國民外交斗士。”
汪毅《一門虎癡》出版后,社會反響強烈。分別由四川省社科院和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正在編纂的《四川抗戰文化》和《重慶抗戰美術史》這兩部記述抗戰文化的大型文獻叢書的負責人,與汪毅先生達成共識,擬定將張善子作為“中華抗戰美術領軍人物”錄入叢書。之前,重慶市還派專人到內江,尋覓張善子的抗戰文化史料。《重慶抗戰美術史》叢書執行主編凌承緯以《一門虎癡》為線索,與上海有關抗戰文化研究專家討論張善子的抗戰文化貢獻及影響,取得令人滿意結果。為此,《人民日報海外版》《文匯讀書周報》《四川日報》等以及人民網、鳳凰網、中國日報網、中國社會科學網等近百家媒體或發布書訊,或刊評論介紹《一門虎癡》,借以彰顯張善子的藝術貢獻。
1938年6月,中華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張善子任主席和首席常務理事。此度由《一門虎癡》推動的關于張善子史料的深度挖掘,無疑會增加其故里正在打造的“張大千文化產業園”“十賢居”以及準備創建并申報內江市市中區為“中國民間文化藝術(書畫)之鄉”等文化項目的含金量。作為張善子家鄉的讀者,讀《一門虎癡》,總感覺有與一般讀者不同的榮譽感、自豪感。筆者進而建議:將張善子踐行的“勇猛精進”精神,作為今日內江城市精神來定位,來傳承;將他書寫的抗戰文化及典型事例寫進內江中小學鄉土教材。
觀張善子一生,其人文精神、文化意義和影響,完全可以與張大千相提并論。當然,昆仲志向和追求藝術所表達的方法各有不同,但卻殊途同歸。
文化是歷史的積淀,名人紀念館是歷史的立體符號。“文化內江”急切需要包括張善子紀念館在內的重量級文化名人館作支撐。時不我待,論證、籌備、申報張善子紀念館前期工作,是歷史賦予的責任。我贊同汪毅先生的思考:就文化抗戰而言,張善子紀念館的創建,還可作為北京中國抗戰紀念館的補充。筆者建言:可考慮先行在張大千紀念館中增添有關張善子的陳列史料,寓教于后學;同時,廣征史料于張善子及門生足跡所及地,征集包括張善子遺存物、文稿、作品、各地有關紀念張善子的文字及圖片等,以豐富館藏。下一步再將張善子紀念館的新建,放在整個“大千文化旅游產業園”,即張大千紀念館的擴容,張大千博物館、大千巴蜀書畫苑等的規劃來統一籌劃;或擇地建設,獨立成館,形成“雙星(張善子與張大千)拱園”,增加園區吸附磁場。張善子文化抗戰行為本身就是一部愛國主義教育的范本。以建館為契機,將其申報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是順理成章,眾望所歸,亦是家鄉人民期盼之事。這是張善子留給家鄉最寶貴的財富。要珍惜并利用好這一資源, 以鞏固內江深厚的文化根基。建造張善子紀念館,也是對歷史的一種尊重和肯定。
值得欣喜的是,就汪毅先生的建議,內江市政協主席陳宗淑已在張大千紀念館內設張善子紀念館一事作出批示,愿意“積極促成此事”。
1956年,張大千與畢加索會晤,已成為東西方藝術史上的一座永恒的心靈“紀念碑”。若能將它以雕塑或其他藝術形式記錄下來,其凝固的是包括內江人在內的中國人的寬闊胸襟以及與世界和諧共存的良好期盼。
《一門虎癡》所載張善子之高足胡爽盦先生亦以畫虎名世。大千先生曾題贈其畫:“滿紙生風,虎有生氣”。胡氏堂號曰“嘯風堂”。1988年10月,胡氏于逝世之前,又親自將愛徒安云霽(他也以畫虎名世)的堂號定為“續風堂”。
《一門虎癡》收有“大風堂”三代佳作多幅。山君之威,震懾四海,國畫藝術,世代留香。此“大風堂”之所以不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