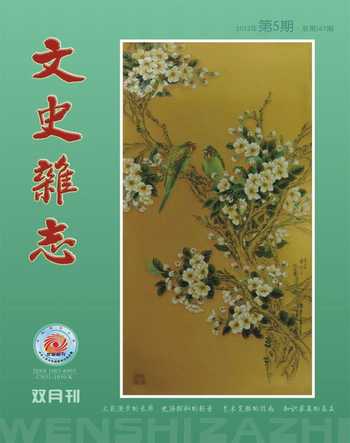漫談孫思邈的養生學
扶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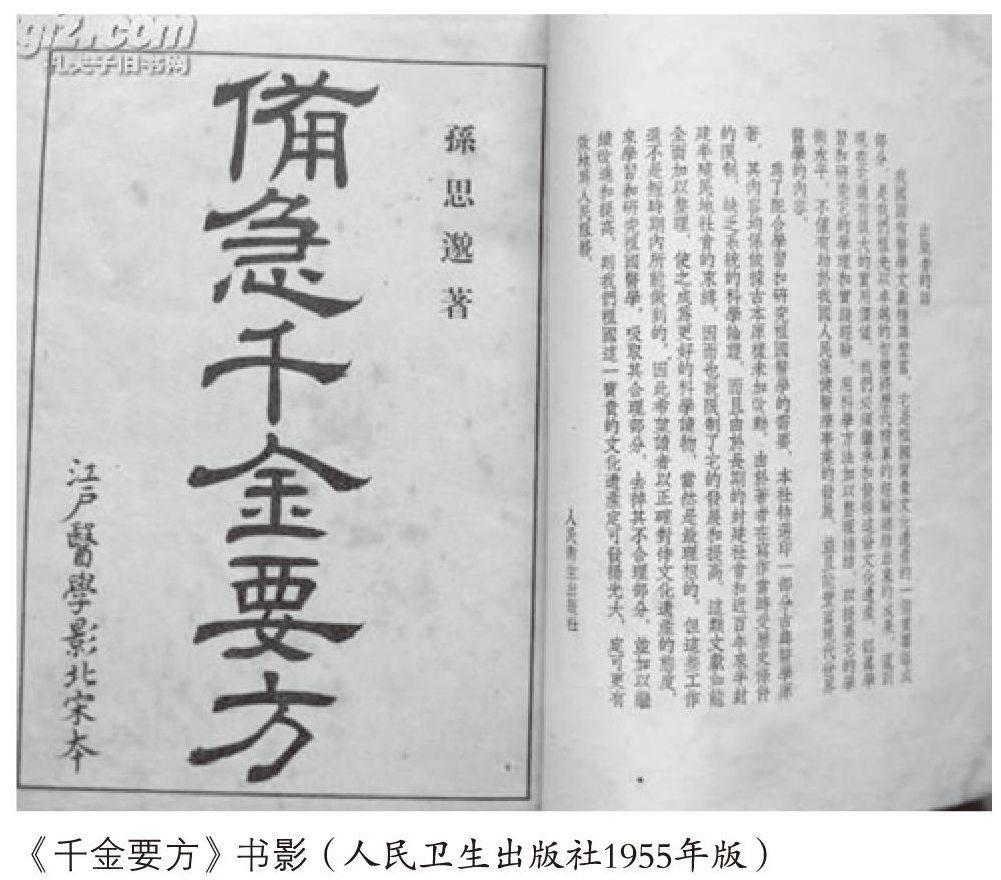
唐代著名道士、醫學家、藥學家孫思邈(公元581—682或公元541—682)不僅崇尚老莊,擅長陰陽、推步,妙解數術,而且兼通儒學與佛典。研究者多認為他以道融儒、釋,順應了唐代三教合一的思想潮流——這從他的《千金方》中可以看出。不過,他終究是從孔、孟之道開始發蒙起家而出入道、佛的。他之所以成果輝煌,且還活到100歲以上,其間儒家的“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應該是一個重要支撐點。他在《千金要方·大醫精誠》里說:
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謂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
在這里,孫思邈提出了作為醫生必須恪守的起碼道德準則,為后世醫家所普遍遵循。而他自己則是身體力行,率先垂范,所以1300多年過去了,還為人們所景仰,成為一位著名的世界文化名人。他的慈悲、智慧、大行、光明的一生,包括上面所引《大醫精誠》里的那段“人格宣言”,兼容了儒、釋、道三家人格思想的優秀成分,表現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為社會、為蒼生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崇高情懷;倘僅從儒家角度去看,則展示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象傳》釋《乾》卦)的奮發圖強、勇猛精進的精神風采。
儒家學說本不以養生—長壽為專務,可是發展到唐代,它的某些積極部分,如“浩然正氣”“自強不息”等,卻被作為道士兼醫家的孫思邈以儒、釋、道三教雜糅的方法圓融進獨具魅力的孫氏養生學。孫思邈同傳統儒家一樣,也將道德品質思想情操的修養看成是第一位的東西。他在《千金要方·養性序》里說:
養性者,不但餌藥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備,雖絕藥餌,足以遐年;德行不充,縱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壽。
在孫思邈看來,倘要身體健康,延年益壽,首先要心地端正,德行純正,摒棄一切名利觀念,方可有所作為。他引《史記》說“病有六不治”,將“驕恣不論于理”、“輕身重財”列入前二“不治”。(《千金要方·診候》)這也是他之所以要在《千金要方》開篇即列“大醫習業”與“大醫精誠”二篇的道理。在“德行”這一點上,無論行醫者還是養性者,皆當首具必備。在此基礎上,孫思邈在《攝養枕中方》等篇里提出“十要”“十二少”并忌“十二多”等養性攝生之法。
所謂“十要”是:“一曰嗇神,二曰愛氣,三曰養形,四曰導引,五曰言語,六曰飲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醫藥,十曰禁忌。”
所謂十二少是:“常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他還明確指出“行此十二少者,養性之都契也”。
所謂忌“十二多”,是與提倡“十二少”相對應的,其稱“十二多”為“喪生之本”。這就是:“多思則神殆,多念則志散,多欲則志昏,多事則形勞,多語則氣乏,多笑則臟傷,多愁則心攝,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忘錯昏亂,多怒則百脈不定,多好則專迷不理,多惡則憔悴無歡。”
孫思邈是積極提倡“抑情養性”的,要求不能“馳騁六情”,“追名逐利”,認為這是百病之源。他提出的“十二少”和“十二多”法則,總起來叫“屏外緣”或叫“自慎”;說養生之道,應以自慎為首。這都是談的精神養靜和形體養靜。但是,他也在《千金要方·道林養性》中指出:“養性之道,常欲小勞,但莫大疲及強所不能堪耳。且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運動故也。”看來,他是提倡動靜相兼或動靜相宜論的。因此,他把“動”與“靜”的兩種方法結合起來,貫穿于自己的養生理論與實踐的系統之中,指出適度運動的必要性,而且任何一種方法都要注意節度,不可隨心所欲。他在《道林養性》里繼續寫道:
養性之道,莫久行、久立、久坐、久臥、久視、久聽,蓋以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立傷骨、久坐傷肉、久行傷筋也。仍莫強食,莫強酒,莫強舉重,莫憂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小懼,莫跳踉,莫多言,莫大笑,勿汲汲于所欲,勿悁悁懷忿恨,皆損壽命。莫能不犯者,則得長生也。
這些話可謂金玉良言,至今還為世人所遵循不移。
孫思邈從“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的自然現象里體悟出“生命在于運動”的道理,為此還向人們推薦《天竺國按摩法》《老子按摩法》等練功方法,以舒筋活脈,驅邪除瘀,養氣補神,強健體魄。
相傳孫思邈著有《孫真人枕上記》、《孫真人養生銘》(又作《孫真人銘》)以及《長壽歌》等,均為養生歌訣。其《養生銘》唱道:
怒其偏傷風,思多太損神。
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侵。
勿被悲歡極,當令飲食均。
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
亥寢鳴天鼓,晨興漱玉津。
妖邪難犯己,精氣自全身。
若要無諸病,常當節五辛。
安神宜悅樂,借氣保五純。
壽夭休論命,修行在各人。
若能遵此理,平地也朝真。
其《長壽歌》則云:
清晨一盤粥,夜飯莫教足。
撞動景陽鐘,叩齒三十六。
大寒與大熱,切莫貪色欲。
坐臥莫當風,頻于暖處浴。
食飽行百步,常以手摩腹。
……
他的《枕上記》則在重視自我保健之外,更強調對精神的調攝。孫思邈的這些養生歌謠的一個最光輝的亮點是提出“壽夭休論命,修行在各人”的思想。孫思邈幼年體弱多病,曾遍訪醫門,以致“湯藥之資,罄盡家產”,可最終卻登攀上期頤之顛。孫思邈在《千金翼方》里還特列出《養老大例》篇,指出:
人年五十以上,陽氣日衰,損與日至,心力漸退,忘前失后,興居怠惰,計授皆不稱心,視聽不穩,多退少進,日月不等,萬事零落,心無聊賴,健忘瞋怒,情性變易,食飲無味,寢處不安,子孫不能識其情,惟云大人老來惡性不可咨諫,是以為孝之道,常須慎護其事,每起速稱其所須,不得令其意負不快,……老人之性,必恃其老,無有藉在,率多驕恣,不循軌度,忽有所好,即須稱情,即曉此術,當宜常預慎之。故養老之要,耳無妄聽,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心無妄念,此皆有益老人也。
孫思邈認為,養老是期頤天年的重要一環,因此要求晚輩們要了解和體諒長輩的生理、心理變化,在日常接觸與交往中,在飲食起居上,對長輩以特別關照。而作為老者本人,也要正視合乎自然規律的身心變化的特點,進行恰當的自我調養。
孫思邈十分推崇“食養”(也稱“食治”“食療”),說這對老年人尤為重要。為此,他在《千金要方》里列《食治》,在《千金翼方》里列《養老食療》,以專門論述。他在《千金要方》里開出的補益五臟和治療各種疾病的常用食物(包括果實、蔬菜、谷米、鳥獸等各類)即達162種,但多簡便易得。孫思邈在《千金要方·食治》里認為,食治不是要吃得多或吃珍稀食物,而在于食物能否有利于人體需要,有利于養病或養老。他還說,醫生不能動不動就給人下藥,“當須先洞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后命藥”。
主要參考文獻:
1.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年版。
2.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年版。
3.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