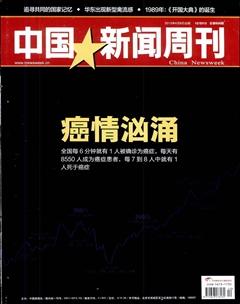馬和勵:“決斷式”發展型政府存在弊病
蘇潔
中國的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讓數億人擺脫了貧困。“政策優先”為社會發展掃清了很多障礙,但也并非完美。巴西的經濟增長不如中國,但巴西在社會發展方面卻取得了很大進步
3年后,馬和勵再次回到當年任聯合國駐華大使的辦公室,開玩笑說“又回家了”。2013年3月29日,馬和勵在辦公室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此時的他,是聯合國人類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局的負責人,而此次中國之行,他帶來了《2013年人類發展報告》。
在這份被命名為《南方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類進步》的報告中,中國以南方國家“領頭人”的角色被重點提及。“中國等南方國家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使本國的人均經濟產出翻了一倍。如果說工業革命改變了一億人的命運,現在是數十億人得到了新生。”馬和勵興奮地說。
在中國生活過8年的馬和勵,不僅見證了中罔的發展,更是“拖家帶口”參與到了其中。
2009年,在第二屆中國綠色發展高層論壇上,作為綠色經濟倡導者,馬和勵和成龍、厲以寧等一起獲得了“中國十佳綠色新聞人物”的稱號,并成為獲得該獎的唯一一個外國人。而馬和勵所為并不復雜:在行業中推動淘汰白熾燈,使用綠色照明。
馬和勵的妻子馬嘉婷,在香格里拉成立了云南山地遺產基金會。而他們的兩個女兒薩拉和艾黎亞則開辦了香格里拉農場,開發有機蜂蜜與咖啡,推動少數民族文化融入可開發的商業鏈條。
馬和勵還有個兒子,前一段時間參加了電視相親節目《非誠勿擾》。雖然因為性格靦腆遭到滅燈,但在馬和勵眼里,中國的方方面面,已經完全融入了他的家庭。
說話的時候,馬和勵總是微笑著。對于這個巴基斯坦人而言,鄰國中國的發展,也是惠及周邊國家的好事。
中國和印度將為亞洲貢獻75%的中產階級
中國新聞周刊:報告提到,南方國家作為一個整體,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而這種歷史性變革,正在創造一種新的全球化模式。如何定義新的全球化模式?
馬和勵:南方國家的崛起帶來了全球再平衡。目前,中國、巴西、印度這三大經濟體的經濟總產出,已經和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六個傳統北方工業強國的GDP總和差不多,這是100多年來的首次。而隨著貿易、旅行、通訊等交流的日益頻繁,國與國之間的人口流動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種交流已經遠不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移民,而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移民數量的大增。在南方國家移民寄回自己國家的匯款中,有一半是由生活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寄出的。另外,便捷的互聯網時代,也培養出了更具國際化的新興中產階級。到2030年,全球80%以上的中產階級將生活在南方國家,他們是推動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中國新聞周刊:80%的中產階級在南方國家,這個數字還挺引人注目的。但如何界定中產階級,他們有什么特點?至少在目前的中國,很多人收入不錯,但生活成本高、壓力大,他們并不認同自己是中產階級。
馬和勵:(笑)你身邊有多少人在用手機,用互聯網收發電子郵件?
中國新聞周刊:幾乎所有人。
馬和勵:這就對了。可能新興中產階級對自己還不夠自信,但廉價易得的科技,以及發展中國家“薄利多銷”的新商業模式,在未來數十年,能夠培養出很大一批中產。另外,人們的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這些都是中產階級形成的基礎。當然,如何為這些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更多工作機會,成為國家的緊迫任務。到2025年,年收入超過2萬美元的家庭會有10億戶,而他們中有五分之三是來自南方國家。作為人口大國,中國和印度將為亞洲貢獻75%的中產階級。
中國新聞周刊:一個不可否認的現狀是,南方國家并沒有因為“南方崛起”而在國際社會獲得相應更大的話語權。比如中國,盡管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還不及法國和英國。你如何看待這一現狀,如何更好地平衡這種關系?
馬和勵:不僅世界銀行,很多國際機構,包括聯合國都面臨這個問題。有一種說法,我們在用20世紀的機構應對21世紀的挑戰。去年的聯合國大會上,南方國家就提出要求,希望讓非洲、拉美、印度等國在安理會獲得常任理事國席位。目前看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力度都比較小。
GDP不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的最好指標
中國新聞周刊:收入能夠衡量一個人是否是中產,那經濟增長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衡量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
馬和勵:不能說GDP完全沒有用,但GDP真的不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的最好指標。美國前總統肯尼迪50年前曾說過一句話,“GDP衡量了一切,卻衡量不了對人最重要的東西。”當年印度洋海嘯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但對亞洲經濟增長并未造成太大影響。損失的是居民的住所和財產,沒有傷及地方經濟再生能力。但是你能說海嘯后的居民過得好嗎?而我們采用人類發展指數,可以更多元化地衡量一個國家地發展:國民預期壽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國民收入。一個國家的發展,歸根結底是人的發展,不是政府,也不是公司。
中國新聞周刊:在談到企業發展對國家的貢獻中,報告特別提到2012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球500強公司榜單中,中國企業有73家,成長迅速。不少中國企業通過跨國并購方式完成擴張,比如聯想并購IBM,吉利并購沃爾沃。很多人評價這種“蛇吞象”的方式風險很大,你認為這是擴張企業實力的捷徑嗎?
馬和勵:這種收購常被視為南方企業的愛國之舉。僅2011年,中國就有200起并購案,共花費429億美元。這種交易能否提高短期盈利能力或者創造價值,目前仍很難說。但從直接效果上看,收購遇到瓶頸的北方老牌公司,有利于擴大南方公司的知名度,為進一步打開全球市場,或者進入一個成熟市場開辟道路。另外,技術的轉移、成熟的風險管理等,也是并購的性生收益之一。
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增長不是正常現象
中國新聞周刊:報告特別提到政府在中國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決斷式”的發展型政府,讓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歷了“復雜而徹底的變化”。你擔任聯合國駐華大使期間,應該也接觸過不少中國官員,對他們總體是什么印象?報告提及中國官員“更注重結果”,你如何看待這一描述?“注重結果”滋生的腐敗問題,又該如何處理?
馬和勵:—個“決斷式”政府的優勢在于,可以非常高效地推行相關政策,并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改革成就,這一點在我接觸的官員身上就有體現。
同時,中國政府也提出“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等理念,這些概念不僅能更好地將培養國民個人能力和社會發展融合,甚至被其他發展中國家借鑒。注重結果并非沒有弊病,關鍵在于如何將危機轉化為機遇。至于腐敗的問題,最直接的方式是加大懲罰力度。
中國新聞周刊:盡管經濟發展迅速,但中國在人類發展指數上的排名只處于世界中游水平,你認為中國的短板在哪里?另外,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增長,是否是一個國家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
馬和勵:我不認為這是一種正常現象。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應該和國家一段時間的目標和政策傾向有關。巴西的經濟增長不如中國,但在社會發展方面卻取得了很大進步,比如他們的學校教育、掃盲項目都很成功。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促進了經濟發展,讓數億人擺脫了貧困,這是舉世矚目的成就。“政策優先”為社會發展掃清了很多障礙,但也并非完美。比方說,中國在醫療衛生領域的成就,大部分是在1950年到1980年間取得的。1980年以后,由于按服務收費模式的推行,農村和城市的醫療水平差距在不斷擴大,很多窮人負擔不起高質量的醫療。
中國新聞周刊:對于互聯網的發展,可能中國百姓的直接感受是可以利用網絡更自由地表達了。你認為互聯網在中國人參與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馬和勵: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是令人欣慰的。尤其是社交網絡等公共輿論平臺的出現,讓很多年輕人自由表達,甚至培養了他們的政治意識。社會媒體應該在國民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成為政府和國民互動的良性橋梁。有時候,社會媒體可以引起政府對更多社會問題的重視。比如在2011年動車事故的時候,中國人民就一直通過網絡表達對安全的擔憂,進而推動了政府作出一定的改變。
現金轉移支付在中國有發展空間
中國新聞周刊:巴西、印度等國實行的現金轉移支付計劃,是發展中國家率先實踐提高人類發展政策的范例,你認為同樣的政策在縮小中國貧富差距方面是否可行?
馬和勵:現金轉移支付計劃在巴四、印度等國也有不少問題,但有針對性的政策的確在縮小貧富差距方面很有成效。巴西等國將現金轉移支付給貧困家庭,通常有足條件的。比如說預先規定要投資于孩子的人力資本,或者對孩子的健康護理等。他們做的規模比較大,有些項目能夠覆蓋100多萬家庭。
目前中國的現金轉移支付計劃更多是比較零散的,比如農村孩子的營養餐計劃等,有待進一步觀察效果。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也在中國推行一些有條件的轉移支付項目,還是有很大發展空間的。很多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循序漸進往往能更好地把握正確方向。
中國新聞周刊:有分析預測,到2016年,中國將成長為世界第一本經濟體,到時候會對世界格局產生什么影響?對中國自身又意味著怎樣的挑戰?畢竟提高人均收入依然是一個嚴峻的問題。
馬和勵:中國成長為世界第一個經濟體只是時間問題,這將惠及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但我們關注的可能不僅僅是第一第二的排名,而是人的生活有沒有隨之變好。
過去50年,美國經濟發展很快,但快樂指數并沒有因此提高。如果經濟發展了,生活更復雜了,這恐怕不是幸福。如果你每天上班要兩小時,下班要兩小時,一天有4個小時用于通勤,你會覺得幸福嗎?再比如在一些傳統國家,婦女地位很低,她們對現狀并沒有抱怨,但不意味著這是幸福社會。
中國在過去幾十年發生了巨變,有些地方很發達,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個發達國家媲美,但很多農村地區卻比較落后。人們都往城市跑,或許應該降低城鎮化門檻,讓更多的人在當地就業。我想中國政府很清楚問題的所在,也能夠找出合適的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