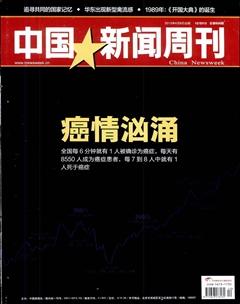《愛》:愛與死哪一個更冷
楊時旸
衰敗是突然到來的。
前一天,艾瑪還是位優雅的老人,與丈夫喬治一起穿著大衣去音樂廳,他們有節制地鼓掌,認真地探討藝術,放松地談論家常。第二天,一切都變了。艾瑪的大腦瞬間短路。頸動脈的血栓宣告了注定的命運——她的半邊身體癱瘓了。
故事由此開始,折磨就像逐漸被推高的音量,一點點演進,有著自己的節奏,慢慢摧毀著艾瑪的身心和丈夫喬治的希望。
電影《愛》中幾乎所有場景都發生在那座巨大而沉悶的宅子中,這對夫妻在其中生活了一生,到處都是沉穩的細節,堆著器皿的廚房,擺滿書籍的客廳,掛滿相框的墻壁,這一切是相濡以沫的證據也透露著衰敗的氣息。導演邁克爾·哈內克幾乎把那座房子演繹成了一座監獄,從此艾瑪與喬治受困其中。喬治站在窗口抽煙,妻子疼痛的呻吟和求助的呼喊就像一根牽扯著他的看不見的繩子,敞開的窗子只有一只鴿子飛進飛出,那是自由的象征,反襯著受困于那所宅邸的老人。
艾瑪再也無法優雅地走路。但她仍然抱持著抗爭的態度,她用左手吃飯,堅持自己讀書,樂于談論自己星座的運勢,她用這種方式爭奪正在緩慢流失的尊嚴。尊嚴幾乎是這部電影的隱性主題,它與愛、死亡一起成為了兩位老人在生命盡頭必須面對的真相。這些宏大的詞語原本只供給于抽象地敘述,但此時卻成為了生活中最真實的細節。
他們幾乎不再談論音樂和藝術,他們說起朋友的葬禮,探討儀式上的肅穆與荒唐,就像談論著自己即將到來的注定的結局。艾瑪在走廊操控著自己的電動輪椅,如同孩子得到了新玩具或者一個年輕人試駕一輛嶄新的汽車,她在病痛中又一次用這樣的方式保持著殘存的尊嚴,以及一種不至于那么不堪的與生活共處的方式。但是這一切太過脆弱,很快就被打破。已經成為鋼琴演奏家的學生來探望,之后寄來一封信,他祝愿兩位老人的生活重回正軌,這個善意的祝福,在艾瑪聽來就像一個惡毒的宣判,認定自己的生活已經脫離常態,更何況信中流露出拼命掩飾的憐憫。
一切繼續衰敗下去,迅速而決絕。如果在那之前,艾瑪仍努力維持著生的尊嚴,那么此時喪失了語言功能和自理能力之后,她的向死之心同樣是尊嚴的表達。
對于電影來說,這并非新鮮的主題。重要的是導演邁克爾-哈內克絕不想將這樣的場景進行戲劇性敘述,他沒有增加戲劇沖突,也拒絕讓作為丈夫的喬治陷入內心掙扎。他以緩慢而平靜的視角拼貼出生活中的一幕幕場景,安寧得近乎死寂。喬治以認命的姿態服侍著妻子,就像這一切都會永遠持續下去一樣。但是邁克爾-哈內克還是終結了這一切,喬治坐在床邊纏綿地安撫喊著疼痛的妻子,妻子漸漸平靜,他本該欣慰,但老人卻抽出了枕頭決絕地壓在了艾瑪臉上,沒有遲疑,沒有悔恨。然后他平靜地面對自己制造的結局,他買來鮮花,一點點修剪,把花瓣灑落在妻子僵硬的身體周圍……
這是一個有著殘忍底色和極端結局的故事,但是導演邁克爾·哈內克以反高潮的方式緩慢敘述著,拒絕任何起伏與波瀾。這似乎才是生活原本應有的面貌,沒有鋪墊和掙扎,沒有計劃和步驟,在毫無戒備的時候,一切突然而至,就像疾病曾突然降臨在艾瑪頭頂,死亡也如是。喬治給予了妻子無微不至的照料,那是濃濃愛意,最終他殺死了妻子,同樣出于濃烈的愛,只不過這個選擇滲漏著死亡的冰冷。但這或許是唯一一個不那么壞的選擇。此時的愛如此沉重不堪又徹骨寒冷。當必須選擇一個深愛之人的掙扎與離去,愛與死,是否會合二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