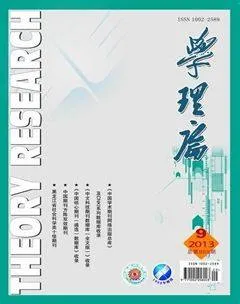錯位的焦慮
唐欣
摘要:近年官場小說權力敘事中的焦慮狀態引人矚目,并突出地以一種“錯位的焦慮”呈現,它是社會轉型期的癥候反應,既表現為傳統權術文化與現代政治文化的融合,也表現為權力與利益所展開的惡性角逐,這種權力敘事的書寫顯示出官場小說尚缺乏深邃的人性關懷。
關鍵詞:官場小說;權力敘事;錯位的焦慮
中圖分類號:I206.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7-0175-02
官場小說創作近年來呈現出蓬勃之勢,其中較有意義的,當屬那些在權力敘事中體現出“前現代”、“現代”乃至“后現代”諸種文化的交錯情狀以及對于主體的欲望焦慮展開話語想象的作品。在這些官場小說中,“錯位的焦慮”引人矚目,這是社會轉型期的一種癥候反應,具體表現為“前現代”的倫理關系網絡與現代科層體制交錯之間產生的失范現象與主體的權欲焦慮。
首先,在近年官場小說中,一些傳統文化特質衍生了現代公共權力運行機制中的倫理化癥候。梁漱溟先生曾說:“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倫理本位者,關系本位也。”[1]79由于轉型期的社會形態,現代科層制度與傳統倫理文化之間相互滲透,呈現出某種共時性。而制度的欠完善與權力資源的有限性,使得古代的倫理傳統與發達的權術文化趁機長驅直入,公共權力的庸俗化在官場中人的心理上則直接表現為一種錯位的欲望焦慮,它導致了人的行為乃至精神的變異,官場小說的權力敘事對此予以充分展示。例如許多官場小說中被濃墨重彩地予以反復表現的“圈子”問題,正是所謂的“圈子”使得《滄浪之水》中的池大為進退失據、《抉擇》中的李高成舉步維艱,卻也使《國畫》中的朱懷鏡如魚得水、平步青云。這種以一兩個權要人物為核心所締結的政治關系網絡往往盤根錯節,在官場小說中,它既可以令人飛黃騰達,又有著巨大的殺傷力。這種官場現狀古亦有之,我們的時代決不獨善。然而,它在當下具有如此大的誘惑力乃至殺傷力,卻與現代與傳統相交匯的轉型期社會體制密切關聯。
在傳統倫理與現代體制相交織中,公共權力的運行尚處于不完善狀態,由此而衍生了官場中的種種“怪現狀”,它首先以“倫理化”的關系網絡締結為主要表征,并進一步促使中國極其發達的傳統權術文化與現代政治文化相融合。如《羊的門》中對于呼天成所精心營構的“人場”的神奇書寫。其中“人場”的建構與呼天成善于看人、用人、栽培人的權術運作密切相關。傳統的權術文化已然凝聚為人生的一種“大智慧”,然而正是因為公共權力運行機制中聚集了太多這樣的“聰明人”,我們國家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是以整個社會的進步為代價的。對于這一點,官場小說作品往往缺乏銳利的目光與深刻的質詢。
其次,傳統文化的負性因子與現代觀念對于私欲的肯定、市場倫理對于財富的認同相結合,直接導致了官場小說權力敘事中圍繞著權力與利益所展開的惡性角逐。由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我國的現代化實踐不僅立足于改善“后發”國家嚴峻的發展問題,同時也將“人”的話語再度置于了文化的中心,其中包括對人的世俗物質向往的肯定,也就是說,私人的權益在一定程度上被認可。這種禁忌的松綁,“徹底打碎了‘大公無私的意識形態神話,極大地激活了人們在征逐個人欲望和利益方面的想象力”,它與市場的財富標準相合謀,從而在尚處于改進過程的不完善的舊體制中,“鉆新觀念的空子,共同促進了一個作為改革開放的負面效應存在的權力私有化進程”[2]63。而人的私欲之閘一旦打開卻又缺乏與之相應的價值倫理與理性約束,就會“撒旦起舞”,特別是在擁有公共權力的官場,則更容易出現權力與利益的惡性角逐。
誠然,這種現象在我國古代早已有之,然而對于人的世俗欲望的正面肯定則是一個現代事件。如孔子講求“克己復禮為仁”,宋明理學又宣揚“存天理,滅人欲”,傳統儒家文化是以克制乃至泯滅人的欲望為前提的。雖然封建社會文化往往呈現出與其宗旨相反的一面,卻也會為利益蒙上一層“道德”的面紗。如“禮尚往來”的勸喻中為人際關系中的利益交換賦予一種道德含義;“千里做官只為財”則說明中國人心靈深處對于為官的一種世俗看法與道德寬容;“法不責眾”的統治策略則既使人們犯罪時有了從眾的心理基礎,又使得社會懲罰失去了約束效力[3]125。而封建時代的官場則是徹頭徹尾的“官本位與錢本位合一的雙本位結構”[4]1。它直接導致了古代“貪瀆文化”的產生。正是基于這些傳統文化慣性與心理因襲,當私人權益在現代社會獲得其存在的合理性,并進一步集中浮現于公眾的感知與關注領域,乃至驅使握有權柄者對于私利的征逐時,并沒有遭遇到“文化上的反抗”。特別是在社會的過渡轉型階段,市場經濟以“人的不加限制就會膨脹的內在貪欲”為“動力機制”,“從前被層層疊疊意識形態所掩蓋起來的私欲,如今獲得了人性的美名”[5]85。而社會體制的不完善,使得私欲的解禁及其與權力的勾連對社會心理產生了巨大的輻射作用,并進而改寫了人們的一些基本價值立場。如劉醒龍的《痛失》、李唯的《腐敗分子潘長水》等,這些官場小說在權力敘事中典型地表現了社會轉型中圍繞著權力與欲望而產生的人性嬗變。
官場小說對于權力與利益惡性角逐的書寫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小說中就已隱約出現,如《喬廠長上任記》中,喬光樸由于對時下“關系學”的缺乏理解,在郗望北的點撥下無奈地默許用送禮等不正當手段去打通關節。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劉震云的官場小說中,無勢的小人物如小林者,也已經開始偷偷品嘗小權力所帶來的大實惠了,比如僅僅“幫忙問一下”就可換來嶄新的微波爐進而享受到烤雞的美味。及至世紀之交,以王躍文的《國畫》為代表的一類官場小說,則更以赤裸裸的形式進一步予以充分表現。官場小說中權力書寫的變化誠然有文學規律的作用因素,然而卻也清晰地勾勒出時代轉型的粗線條及社會價值倫理的嬗變。例如田東照的《跑官》、《買官》系列作品,畢四海的《財富與人性》等小說中所表現的那樣,權力與金錢的角逐加速人性的異化,而人性中貪欲的放縱又使其變本加厲地追逐權力與金錢,從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對社會與人性都構成了巨大腐蝕。
特別是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資源的有限性,人們被市場所喚起乃至激發的無數欲望在短期內注定無法實現。而由于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目前尚不具備,公共權力機構在資源配置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使得其成員容易成為“利益集團尋租的獵物”,如市委書記陸宇浩兒子婚事中的波瀾(田東照《賣官》),投機商人金啟明的神通廣大(周梅森《絕對權力》);而某些喪失政治信仰的人又急于獲取私人財富,從而使得其手中握有的公共權力變質為致富的工具。在國際經濟學界,這種現象稱為“尋租”。如地委書記秘書孟維周的墮落過程(王躍文《朝夕之間》)、商人金啟明對副市長趙芬芳進行的政治投資(《絕對權力》)。而對于公共權力機關中的某些汲汲于官者而言,權力資源也是有限的,這種有限性使得大量受阻的權力欲望在其內心積壓,形成無以排遣的權力焦慮,其熾烈欲求有時便會期望通過非法的手段去實現,如田東照作品中的“跑官”現象。總之,我們看到,在官場小說的權力書寫中,人的無限欲求與滿足這種欲望的有限資源之間總是存在一種內在的緊張。而社會的轉型過程就是一個財富與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市場運行的巨大力量恰恰在于,它把諸多復雜多元的關系簡化為一個原則,即個人效用的最大化,一切以交換價值取向為根本,以成本的最小化換取利益的最大化。這是工具理性意識的惡性膨脹,而它所直接誘發的權錢交易行為,又進一步刺激了“官本位”意識在現代的畸形演變。如來路不明的袁小奇之迅速崛起(《國畫》)、不法商人舒培德的財源滾滾(《朝夕之間》)等,他們的興旺發達與某些官員的平步青云之間構成微妙的因果聯系,官場小說對此有著充分揭示。
在這些官場小說中,雖然作者為社會提供了“一把把化驗單,一張張透視底片”[6]690,然而,作家的責任卻遠遠不止這些。正如卡西爾所指出的:“事實的財富并不必然就是思想的財富。除非我們成功地找到了引導我們走出迷宮的指路明燈。”[7]30在傳統與現代相交錯的轉型中,對于文化的審視與人性的探詢,官場小說在題材上可謂是占盡了先機,然而它們卻不同程度地表現出歷史理性的匱乏與人性目光的短視,這是當下官場小說寫作必須直面并予以解決的問題。
參考文獻:
[1]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
[2]張業松.個人情境[M].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97.
[3]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M].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4]楊林.中國古代官場病[M].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5]曹錦清,陳保平.中國七問[M].北京:中國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6]王躍文.拒絕游戲[C]//國畫·代后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7]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甘陽,譯,南京:譯文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