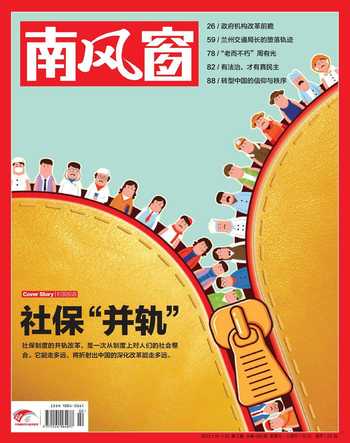開放的辯證
李北方
當下的中國社會許多人有一種誤解,認為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不開放的,是封閉的。在多年來的社會輿論和歷史解讀中,以這種方式描述改革開放前的觀點并不鮮見。
關于對外開放,有兩個有所交叉的維度可以討論:第一是開放的對象,即向誰開放;第二是開放的向度,即開放(開放意味著交流)是單向的還是雙向的。
對外開放也是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有機組成部分。當時的大環境是冷戰,中國的國際空間是逐步拓展的。到了1976年,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達113個,英國、法國、原西德、西班牙、日本、澳大利亞等均在此列;與美國交往的大門也已經打開,距尼克松訪華已經過去4年了。
第一階段的開放的對象以非西方國家為主,這也是由特定的歷史背景決定的。如今,中國的建交國達到165個,在對外開放的范圍上更廣泛了。如果以貿易量作為衡量開放程度的指標的話,那么在第二階段的開放度大大加強了。在對外貿易的比重中,與西方國家的往來占了絕大部分,可以說,開放的對象發生向西方國家的偏移。但兩個階段的開放之間存在著不可分隔的連續性。
在開放的向度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的理解也有所不同。第一階段的開放當然包括商貿往來,一個例子是,創辦于1957年的廣交會一直是中外互通有無的平臺,即便在“文革”期間也未中斷過。同時,開放還包括對第三世界的無私援助,1971年“非洲兄弟把中國抬進聯合國”就是這個層面的交流結出的碩果。
相比較之下,第二階段的開放表現出更純粹的經濟關系,中國通過加入WTO等方式融入了全球資本和貿易體系。隨著國力的增長,中國不僅吸引外資,也走出去,對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地區進行投資。中國在國際上以發展中大國的形象出現,即在經濟關系中進行自我定位,淡化意識形態色彩。相應地,國際主義的一面淡出了歷史舞臺。
未來的對外開放應該是全方位的開放,外部世界不等于美國,亞非拉國家的優秀文明成果和發展中的經驗教訓同樣值得吸取;未來的對外開放應該是雙向的,中國應該改變與西方交流中被動姿態,形成并輸出自己的影響力和價值觀。
對外部世界的認識也經歷了改變。改革開放后,與經貿關系往來的重心轉移一起,開放變成了對西方的開放,又逐漸變成了對美國的開放。雖然中國與亞非拉國家的貿易額在對外貿易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大大下降,但頻繁的交往仍是存在的,可是這些地區卻從中國對外部的理解中隱匿了。
改革開放前,中國引進外來的技術和文化,中國的文化也同時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影響,不僅是對第三世界,對西方國家的社會變革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即在開放中形成的交流是雙向的。但逐步地,對外開放的雙向性失去了,在“與世界接軌”的名義下,中國成了文化意義層面單一的接受者,仿佛一切都要按照美國的標準進行改造。甚至在西方的文明、社會經濟體制遭遇空前的大危機之時,“與美國接軌”的思維也沒有被撼動。與此同時,中國也希望通過建立孔子學院等途徑對外輸出文化,但效果并不理想。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完整地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述。借用這個視野,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兩個歷史時期在對外開放方面的得失,用以豐富對未來的理解。基于此,我們可以提出兩個初步的思考:第一,未來的對外開放應該是全方位的開放,外部世界不等于美國,亞非拉國家的優秀文明成果和發展中的經驗教訓同樣值得吸取;第二,未來的對外開放應該是雙向的,中國應該改變與西方交流中被動姿態,形成并輸出自己的影響力和價值觀——這有賴于中國的道理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