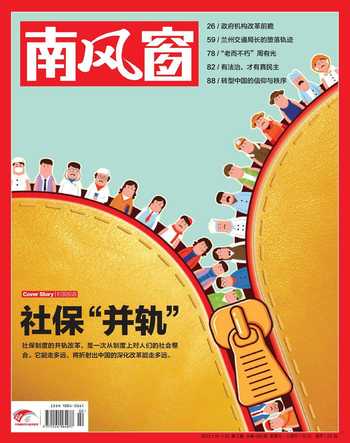灰色上海時期我的父親李健吾
我非常喜歡傅葆石先生的《灰色上海》這本書,并不是因為他正面評價了我的父親李健吾,而是他選擇的寫作角度:從完全個人的道德角度來觀察個人的表現和行為,這是我們以前十分缺失的。為此,傅葆石先生選擇的是一些無黨無派的人士,可能還是被視為“右”的人,在艱難生存的日本鐵蹄下的上海,因內心道德的底線不同,會有不同的表現和行為。他不是僅僅描述那個年代的文人萬象。
我想在這里說說一個有良心的普通文人,我的父親,在上海時他能做的一點抵抗,也理解,為什么傅葆石先生選擇他作為上海孤島時期抵抗者的代表。

李健吾筆名劉西渭。近代著名作家、戲劇家。從小喜歡戲劇和文學。1930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文學院外文系。1931年赴法國巴黎現代語言專修學校學習,1933年回國。歷任國立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上海孔德研究所研究員,上海市戲劇專科學校教授,北大文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著有長篇小說《心病》等。譯有莫里哀、托爾斯泰、高爾基、屠格涅夫、福樓拜、司湯達、巴爾扎克等名家的作品,并有研究專著問世。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議組成員、法國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
“一個有良心的小民”
應該說,在1937年之后,學校帶著老師和學生從北方轉移到上海,然后跟著政府的撤離,大部分都去了大西南,也就是重慶、云南、貴州等抗戰的大后方。當然,有一部分青年轉移到了陜北。在上海,開始還留下相當一部分文化人,如巴金、鄭振鐸、王辛迪、陳希禾等,還有許多地下黨的工作人員,如阿英、夏衍、于伶等。他們編刊物,演街頭戲,號召群眾起來反抗。也就是在那時,父親,這個從1935年以來一直是個教書匠和伏案寫作的人,終于有機會走進了大社會,成了當時話劇活動中極為活躍的人,包括為出版《魯迅全集》籌錢,親自編劇,參加演出。他還利用自己的法國留學生和法國文學著名翻譯的身份去法國使館活動,使地下黨員領導下的上海劇藝社取得合法身份。他這時感到,自己雖未去內地,可內心還是充實的。也是在這個時期,他回憶起了自己早逝的父親,一個血性的漢子,反清反袁,帶領民軍走在戰場第一線,他開始著手寫《草莽》。
從1942年起,上海的形勢越來越混亂,特別是1943年之后,英法租界都向日本屈服,整個上海全在日本和汪偽的手中。活動愈發無法進行下去,不少人早早躲進書齋,或離開了上海。許多副刊停了。巴金早于1938年就去了西南。按照黨組織的要求,夏衍、于伶等地下黨員于1942年都去了香港。
上海成了真正的孤島,徹底淪陷。一個普通老百姓,養家糊口總是必然的,再說,從13歲就是孤兒的我父親,對這個家是很珍視的。他自己的過去,他不能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他不能拋開妻女,奔赴大后方。他留在上海,沒有正常的工作,生活來源不固定,當時想要堅持道德底線確實艱難。作為始終不在任何組織內的人,孤孤零零,不想妥協,還想抵抗,是非常不容易的。清苦、寂寞,但是,他堅持著。開始他在上海劇藝社還堅持活動,他不僅積極參與,幫助張羅,還將母親陪嫁的一點點首飾變賣了,給劇藝社作經費。之后,他參加了苦干劇團,用改編外國名劇的方式提供劇本,和同樣留在上海的朋友們(基本上都是無黨派人士,如黃佐臨夫婦、陳希禾等)組織和參與了大量的演出活動,在許多劇本中都在暗示觀眾,應該選擇不妥協,選擇抵抗。當然,也參加一些純商業性演出,為了弄點錢。
他曾自稱“一個有良心的小民”,良心讓他絕不接受為日本人服務。1942年,在收入貧乏的情況下,他堅拒了周作人邀請他去北大任系主任的邀請。那時,我們住在徐家匯,多福村的一個小弄堂里,緊貼著上海殯儀館。我們家是三房客,也就是一個小三層樓最底層的兩間屋(廚房、臥室兼寫字間),前門對著弄堂,后門是上二樓的正門,二房東在二樓。我清楚記得,父親常常在傍晚到小菜場去撿人家賣剩下來的小菜,有時還能帶回一條沒有賣出去的魚—那是大事,媽媽是無錫人,愛吃魚。演出活動之余,他總是伏案,我記得他曾經在讀蕭乾的《八月的鄉村》。蕭乾本人當時在陜北。他很喜歡這篇文章,準備寫書評。
他不是國民黨員,不是共產黨員,他只是一個中國文人,照我母親的話,一個書呆子。他真正顯示出了他內心道德的力量。
為了劇團,1944年父親改編完成了《金小玉》的話劇劇本。劇本表達了歡迎國軍歸來的情節,演出在當時轟動了整個寂寞的上海。這就招來了日本憲兵的注意。一場驚心動魄的抓捕活動就在我的眼皮底下發生。
直面日本憲兵
1945年春一個深夜,后門被沖開,一批人蹬蹬上了二樓,我父親以為來了強盜,從前門出去叫來了警察,小弄堂里堆滿了人和車。據說警察一眼就辨認出那些車全是日本人的,立刻就呆在弄堂墻根不動了。
日本憲兵做夢也想不到,一個大劇作家,會住在樓下,只是個三房客。他們回身進了我們的廚房,我醒了,嚇得一動不動,假裝還是睡著,把手搭在身邊熟睡的二妹和弟弟的身上,10個月大的三妹在兩張大床之間的搖籃里。媽媽在忙碌著,她趁日本人在廚房的柜子里翻騰時,匆匆地把父親書桌上的書,特別是《八月的鄉村》塞進了我床下的鞋子里。接著日本憲兵就進了我們的臥室兼小書房,一邊在書櫥里翻找,一邊詢問我母親父親在哪里。母親回答,沒在家,沒回來。最后,那位笠原“大佐”(編者按:笠原幸雄,日本11軍司令)讓其他人退出,自己坐在床邊,吹滅了蠟燭(當時,整個晚上都是燈火管制),他說:“我們先睡覺!”就在這時,父親拍門而進,他張嘴說:“你們要抓的是我,帶我走吧!”就這樣,他被捕了。母親癱坐在床頭,吐了一地。
父親在憲兵司令部里,受盡了折磨,冷水從頭上,從身上直直地灌入嘴里和鼻子里,直到血涌了出來。那個笠原“大佐”用要他留遺書威嚇他。他費力地說:“告訴……孩子……們,爸……爸死……得慘,他……是個……好人。”
一個好人,這是我父親刻在我心上的話。
是他的朋友和同學出了大錢把他贖了出來,但是他必須每周一次去面見笠原“大佐”報告行蹤。對這他不能容忍。過去7年,他沒有妥協,這時,直面日本憲兵,他絕不能委屈求全,他決定離開上海。一個黢黑的夜里,在朋友們的幫助和接應下,他離開了上海。幾天后,我母親牽著我的小手進了我學校的校長辦公室。當時大考結束,校長見到母親,高興地對她說:李維音這次考得很好,我們決定給她全額獎學金。我母親靜靜地回答:我們是來退學的,我們準備去無錫鄉下。校長說不出話來,戰亂時期么!我母親離開了校長辦公室,我難過地跟著,真正體會了什么是國難。國難啊!
兩天后,嬌小瘦弱的母親抱著三妹走在前面,小弟和二妹在后面跟著。我,一個不到11歲的小姑娘,家里剩下的唯一勞力,拎著兩只箱子,走在最后面。我們出了上海,登上一只逃難的破船,一路上聽著后面的槍聲。母親因暈船,嘔吐著。我們是去和父親會合,一起走向完全不熟悉的安徽山區,那里沒有日本侵略者!
父親為了保護妻子,挺身進屋就擒,在獄中,忍受折磨和威嚇,沒有提供一個朋友的名字,出獄后,他拉扯著家小,千辛萬苦,走向了后方。他不是國民黨員,不是共產黨員,他只是一個中國文人,照我母親的話,一個書呆子。他真正顯示出了他內心道德的力量。
同樣是道德力量的促成,他把他老師用英文寫就的戲翻譯成中文,也就是《委曲求全》,使之公演,然后把版稅和演出費全部寄給了窮困潦倒的王文顯先生,自己分文不取。
遺憾的是,從1948年下半年開始,從延安到上海,進了一批文人,他們開始批判以沈從文伯父為代表的“京派”(他們的作品被革命者視為過于純文學型,小資或純資),我父親就是被批判的人之一。之后,我父親一直被視為“右”,特別是《金小玉》盼的是“國軍”,更是十足的把柄。可是他有自己的原則,在抗日勝利后回到上海,政府里的同學讓他到上海文化局工作,他一看盡是干“文禁”之類的事,干了一個月就告病假,然后就溜了,又進了教室和書房,教書和翻譯。
他熱愛這個國家,歡呼著解放,總想跟上步伐,卻時常被排斥。但不論在何時、何種壓力下,他堅持道德底線,忍受被貶,不做不該做的事,不說瞎話(甚至會說些不待見的傻話),不求虛榮,不出賣朋友。
今天,個人的道德重被提起,特別是傅葆石先生選擇了那個能考驗個人道德的年代,這就是《灰色上海》的特別之處。我感謝他正確評價了我父親,恢復了那個年代的歲月,同時深深地感到,如果一個人道德底線缺失,僅僅是他個人為人民所不齒,不足掛齒,可是當有一大批人缺失道德底線,那么對社會的摧毀性就是巨大的。想想今天的官場眾生相和民間種種糾紛,是到了重提時代轉折期個人道德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