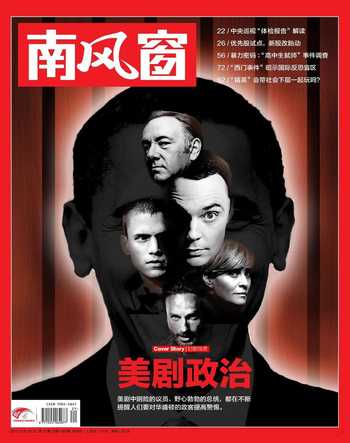民營銀行熱的冷思考
譚保羅

自從“蘇寧銀行”的名稱在9月初獲準預登記以來,民營銀行“預登記熱”儼然被誤讀成為了“開辦熱”。事實上,目前還沒有一家“銀行概念股”企業拿到過銀行經營許可,而預登記的銀行名稱在有效期后也將失去效力。
不論是為了炒作,還是企業家果真有振興民間金融的企圖心,本輪申辦熱無疑再次將中國銀行體系的改革推向了前臺。利率市場化改革方興未艾,那么必然要有金融機構準入的自由化與之配套。
如果監管最終放行,那么民營銀行必定會成為一個利益的棋盤。包括“求資若渴”的地方政府和其他“居心各異”的市場主體都將被卷入其中,改革的收益和風險并存。但風險并不是拒絕民營銀行存在的理由,相反,風險是重新檢驗中國金融和商業智慧的試金石。
“預登記熱”
9月底,這是溫州傳統的入秋季節,氣候轉涼。楊嘉興的心情就像這天氣,從火熱歸于平靜。作為聞名遠近的“銀行家”,面對9月份各地興起的“民營銀行熱”,他卻告訴《南風窗》,“等看看再說。”
1986年,41歲的楊嘉興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民營金融機構—溫州鹿城城市信用社。2012年溫州金改啟動后,68歲的他向溫州市有關領導報送了創辦溫州農村發展銀行的申請,計劃注冊資本金20億。但這份申請并未得到滿意答復。去年秋天,他在失望之下撕掉了申辦這家民營銀行的材料。
“目前還沒有實施細則,有法可依辦事情才有價值。”楊嘉興說,國務院提出要對民營金融機構進行支持,這是“東風”,但這還不夠,要有具體的實施細則與監管標準出臺,自己才會考慮重啟申辦。
“僅僅是名稱預登記,有炒作成分。”9月27日,溫州市金融辦一位人士對“民營銀行熱”進行了委婉的批評。該人士對《南風窗》說,國家工商總局僅僅是對企業報送的名稱進行預登記,并非銀行將要注冊成立。預登記存在有效期限制,過期即可能作廢。目前,監管部門還沒有正式細則出臺,現在談為時過早。
把本輪民營銀行“申辦熱”稱之為“預登記熱”更為符合實情。按照規定,工商部門對企業名稱預登記的審理較為寬松,只要申請基本都能通過,這是9月份一下子登記了近20個銀行名稱的原因。申辦民營銀行最關鍵的步驟是從銀監會等金融監管部門獲得銀行金融業務的許可證,然后才回到工商部門申請營業執照,最終注冊成立。
在業界看來,本輪“預登記熱”可以做兩種解讀。一是民企看到中央支持民間金融發展大風向之后進行“名稱卡位”;二是基于利益的炒作,而此種解讀可能更符合這些“涉銀”民企作為A股上市公司的身份。近日,多家傳出將籌辦民營銀行的公司的股價都出現大幅上漲,部分漲停。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更公開對“格力涉民營銀行”的消息提出批評,認為這有助于股市炒作者獲得不公平利益。
實際上,本輪“預登記熱”之前,在國內民間資本較發達的地區,民企申辦銀行已間歇性地熱了10多年。在溫州則已經是第三波。少為人所知的是,早在2002年,溫州便被人民銀行批準為金融改革試驗區,這直接引發了溫州的第一波民營銀行申報熱。當時,最受關注的是“建華銀行”,名稱取“建設中華”之意。此后,溫州又在2005年國務院鼓勵民間資本的“老36條”出臺之際出現了一次申報熱。但直到如今,溫州未有一家民營銀行獲批。楊嘉興說,“零記錄”讓他很失望。
不過,受訪的數位人士都提到了近期正在制定的民營銀行試點相關細則,認為只有這個細則出臺才意味著民營銀行有成立的可能,但這個細則并未得到官方確認。9月26日,一位民營經濟發達地區銀監局的政策研究處負責人對《南風窗》表示,這個“細則”自己尚未聽說,民營銀行問題較為敏感,故不便多談。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相信這個細則正在制定之中。他對《南風窗》表示,溫州人在全國創辦了3.5萬家工廠和6萬~7萬家商貿企業,在海外則有70萬~100萬溫州人在經商。目前,這些外部資本不少都回到溫州沉淀起來。周德文估計,溫州地區的民間可用資金可能達到1萬億。規模之大,超過中國不少省份全省的銀行存款余額。
周德文分析說,本次申報民營銀行的企業主要集中在江浙和廣東,民間資本已經有強大的經濟和政治能量。盡管名稱預登記不代表可以開辦,但這是一次輿論熱,對監管部門的“細則”制定會有積極影響。但他也認為,即便監管放行,最終獲批的銀行也肯定是極少數。
格局失衡
在部分支持民營銀行興辦的人看來,“美國3億人擁有8000家銀行”這個數據被認為是中國應該大力發展民營銀行的重要理由。與之相比,中國的銀行數量的確少得可憐。
關于中國銀行機構的總數,在網絡上很難查到監管部門公布的權威數字,但從官方背景的中國銀行業協會的網站上可以“窺豹一斑”。該網站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9月,協會共有349家會員單位和3家觀察員單位。會員單位包括名稱中帶有“銀行”二字的金融機構,也包括了資產管理公司、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農村信用社聯合社、地方銀行業協會、金融租賃公司、貨幣經紀公司和汽車金融公司等機構。
但市場主體數量并不代表網點滲透率的差距。一項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末,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總數達到20.51萬家。粗略計算后會發現,這等于是說6000多人擁有一個銀行網點,這一數字已達到部分中等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水平。
事實上,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金融機構最為熱衷的擴張方式是縱向擴張,即原有機構擴張網點,代替了新設機構。這種方式的優勢是可以降低監管部門的監管成本,但長期以來則造成了中央和地方金融格局的進一步失衡,因為地方喪失了新設金融機構的機會。
舉例而言,目前各省和市基本上都有一家政府控股的城市商業銀行,但其資產和利潤規模都明顯小于同城國有大行的分行。地方政府迫切希望擴大地方銀行的盤子。但央行、銀監等中央垂直監管部門卻一直嚴格監管。近幾年,城商行異地擴張多次被叫停或收緊便是這個原因。
因此,為了發展地方銀行,各地政府紛紛拉攏民營資本入股。這樣一來,地方商業銀行多數已經變為了“股份制”,甚至帶有濃重的“民資”色彩。
2006年,針對“老36條”頒布引發的民營銀行申報熱,時任銀監會副主席的唐雙寧明確表示,作為中國銀行業的最高監管當局,中國銀監會總的態度是,歡迎民營資本,防止關聯交易、審慎設立機構。
唐還透露了兩組數據。2002年到2005年3年間,據對11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股權結構統計,民營股增加了65.54億股,增長率是144.9%,民營股占比增長了1.24%,而同期國家股、國有控股企業法人股占比分別下降了0.76%、17.19%。3年間,我國115家城市商業銀行的股權結構統計中,民營股占比增長了10.19%,而同期國有控股企業法人股和地方財政股的占比分別下降了4.33%和7.65%。
目前,民營資本在部分知名金融機構已經占據控股局面。以國內最大民營銀行民生銀行為例,其民營大股東通過減持股票套利數億的消息在市場早已見慣不驚。而在江浙地區,一些城市商業銀行其超過半數的股份都是民資,已經屬于民營銀行范疇。
一位民間金融研究人士對《南風窗》表示,從民營資本這些年進入銀行業的情況來看,監管部門嚴管民營銀行并非完全出于制度歧視,很大程度是出于風險考慮。很多情況下,監管對于民間資本其實管的并沒有想象的嚴。以小額貸款公司為例,按照政策初衷,本是為了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和弱勢群體再就業,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少小額貸款公司都一直在“吃大戶”,客戶群體和銀行存在高度重疊。某種程度上,一些小額貸款公司成為了企業之間的放貸和舉債工具,但監管并未“一竿子打死”。
但銀行卻完全不同,因為銀行采取杠桿模式,股東可以以資本金撬動至少4倍以上的公眾存款,風險外溢,這才是最大風險所在。與此同時,一旦民營銀行在各地廣泛建立,必然會受到地方政府的影響,在財稅體制沒有做好配套改革的時候,一遇到地方政府財力吃緊,民營銀行的正常經營可能遇到一些麻煩。
大股東風險
和資本市場的上市公司一樣,中國銀行業存在的最大麻煩同樣來自于“大股東風險”。對銀行來說,壞賬可能減少盈余,但“大股東風險”則關系到生存。
自從上世紀80年代拆分中國人民銀行,成立正規商業銀行以來,中國的商業銀行幾乎沒有發生過因為擠兌而倒逼的情況,但唯一的一個例外是海南發展銀行。
1998年,正常營業才兩年10個月的海發行倒閉清算。海發行成立之時可謂氣勢如虹,其控股方為海南省政府,主要股東多為大型國企。但最終,海發行卻成為了“股東提款機”,股東變相抽資成為這家銀行最主要的對公貸款,這些錢絕大多數成為了壞賬。
對于“大股東風險”,“民間金融家”在海發行危機之前早已做過實驗,并找到解決方案。楊嘉興等8人集資31.8萬元創辦的溫州鹿城城市信用社,除了被稱為中國的首家“民營銀行”外,這家信用社還創造了中國金融史的一個奇跡。從1986年建立到1998年被溫州市政府“收編”組建溫州市商業銀行的12年時間內,這家信用社竟然沒有出現一分錢的壞賬。
如何營造了這個奇跡?楊嘉興有他的“獨門暗器”。成立之時,信用社的8位股東被分為了“A類股”股東和“B類股”股東,前者是有限責任,而后者是“準無限責任”。換言之,如果銀行破產需要清償債務,那么“B類股”股東除了以出資進行承擔責任外,還必須以其他個人財產進行清償。而這些個人財產在入股時就已經列明并且載于章程等法律文件,具有法律的強制效力。
在鹿城城市信用社營業的12年時間內,不論如何增值擴股,這個“AB股模式”始終執行如初。而“B類股”股東全部是持股相對較多的股東,相對而言,“A類股”則股權較為分散,可以稱之為“散戶”。因此,這種類似于“有限合伙企業”的模式增強了對大股東問責機制,和英美商法“刺破公司面紗”的流行做法如出一轍。
除了在前端的公司權益設置上,在后端的具體業務上,鹿城城市信用社也多有創新。比如堅持“貸小”原則,即每一筆貸款控制在5萬以下。這種做法增加了股東“抽資”的成本,也分散了貸款的風險。
楊嘉興頗有感概地說,無論從國家金融改革的大風向,民間資金積累程度還是“民間銀行家”的技術準備來看,民營銀行的成立都箭在弦上。
但對風險的擔憂仍然客觀存在,并制約著改革的步伐。以上民間金融專家分析說,對監管部門來說,風險不外溢一直是監管的重要原則。目前,不少銀行的壞賬率出現了明顯上升,比如溫州就曾出現過大型企業負責人“跑路”的情況。在信用體系尚未完備的情況下,貿然擴圍開放民營銀行很難避免出現相關的問題。與此同時,中國金融業缺乏的不是銀行機構,而是其他金融形式,比如財務公司和消費金融公司,這些公司可以把金融風險控制在一個固定范圍,同時也能起到資金配置的作用,它們可能是下一步的改革重點。
值得注意的是,銀監會在9月底連續發布了兩個“信號”。一是對《消費金融公司試點管理辦法》進行了修訂,增加了出資人類型、降低了出資人持股比例要求,同時還取消營業地域限制和增加吸收股東存款業務;二是公布擴大消費金融公司試點城市范圍名單,新增10個城市參與試點工作,試點城市將達到16個,幾乎涵蓋了國內所有的一線或其他中心城市。
在業界看來,金融消費公司的形式更適合經營耐用消費品的蘇寧云商和格力電器等企業采用,而它們也正是市場呼聲最高的銀行申辦者。不過,金融消費公司的擴容是否監管部門對民營銀行申辦的“替代方案”,目前尚不得而知。
楊嘉興說,銀行的風險到底大不大和民營和公營沒有必然聯系,而和公司治理以及司法環境的關系更大。他打了個比方:民營銀行是汽車,監管部門是交警,維護交通安全的辦法絕對不是不讓汽車上路。
國家工商總局僅僅是對企業報送的名稱進行預登記,并非銀行將要注冊成立。預登記存在有效期限制,過期即可能作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