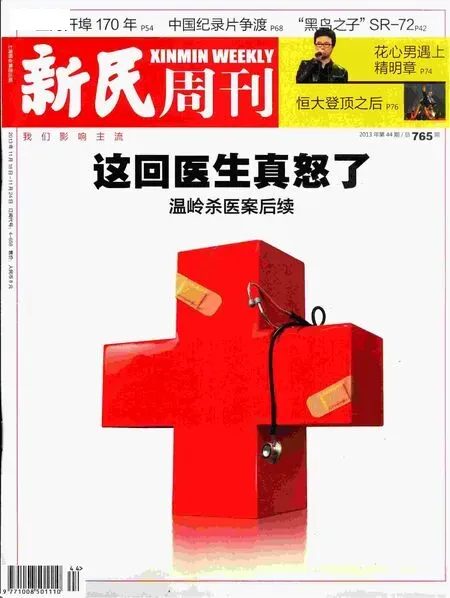穿越在上海百年老醫(yī)院
劉琳 羅莎
30年代。上海。
當這兩個詞搭在一起,好像會產(chǎn)生一種魔力,一個3D聲像的開關即刻被打開了——
酒吧里锃亮的金色小號歡快地吹奏著爵士樂;隨著那扇上了年紀的老轉門一同“轉”出和平飯店,街頭燈紅酒綠,靡靡之音彌漫,百樂門夜總會,仙樂斯舞廳……一路閃退;
推開石庫門房子的窗戶,操著吳儂軟語的太太們稀里嘩啦地搓著麻將,穿著曼妙旗袍的張曼玉拐下二樓亭子間的木樓梯,遠處一聲“篤篤……買糖粥”的吆喝聲傳來;
隨著一聲汽笛聲,上海的早晨從黃浦江上、蘇州河邊蘇醒,老弄堂、匯豐銀行、圣約翰大學,買早餐的太太、跑洋行的買辦、在教會學校讀英文的小姐、從法國留學歸來的少爺,紛紛粉墨登場;
模糊的老照片、發(fā)黃的月份牌、昏暗的煤氣燈、破舊的老爺唱機,還有銹跡斑斑的懷表,一件件撲面而來……
如今,在兩岸三地文化人和文化商人的共同努力下,30年代的上海被美化為上述一段“花樣年華”,甚至被譽為“小資”們最向往生活的全球5個年代之一。
相比于上世紀高貴優(yōu)雅的50年代巴黎、玩世不恭的70年代倫敦、隨意簡約的80年代紐約和熱情性感的90年代米蘭,小資們念想中的老上海似乎更遙不可及,他們說:“只有30年代的老上海,才能夠象征品位、格調、優(yōu)雅、浪漫、摩登、經(jīng)典。”
但,30年代的上海只有活色生香嗎?
“游閑的尸,淫囂的肉,長的男袍,短的女袖,滿目都是骷髏,滿街都是靈柩,亂闖,亂走;我的眼兒淚流,我的心兒作嘔。”這是郭沫若的30年代《上海印象》。
如今盛行的濃濃懷舊風,就像那美顏相機把上海曾經(jīng)的滄桑瞬間魔為幻美。
再來看20世紀30年代中國電影的壓軸之作《馬路天使》。透過那個由吹鼓手、歌女、妓女、鴇母、攤販、流氓、賬房、房東太太、律師等人物形象所組成的底層社會萬花筒,盡管電影的格調如此清新,仍可以清晰地看到30年代上海的真實存在:底層生態(tài)鏈上各個環(huán)節(jié)的相互傾軋、上層社會的壓迫以及民族危機的深重。
30年代的上海并不只有玫瑰色,顛沛流離的亂世更是血色的。連年戰(zhàn)爭,連天愁苦的唯一“好處”似乎是成就醫(yī)技,人間疾苦成了“新生事物”西醫(yī)院在30年代上海的蓬勃發(fā)展的重大機遇。
對一個真正的“老上海愛好者”來說,一場更專業(yè)的懷舊也許應該是尋訪上海老醫(yī)院。抹去被施的脂粉,還原歷史的真實,發(fā)掘上海縱橫170年的每一種魅力。所以,當你徜徉完外灘“萬國建筑博覽會”長廊,千萬請記得拐個小彎,走一走如今依然市民氣十足的山東中路,并請停留在145號。
西醫(yī)在中國:仁濟傳奇
七層高的英式建筑圍成一個半弧,深褐色的外墻上鑲嵌著一排排老式的落地鋼窗。室內壁燈高懸,寬敞的樓梯順著紅棕色的扶手盤旋而上,雕花走廊延伸向病房最深處。電梯每停一層,頂部的指針就移動一格,儼然一派莊重典雅、復古溫馨之態(tài)。
上海山東中路145號,修舊如舊的仁濟醫(yī)院西院2號樓,上海市政府斥巨資經(jīng)過兩年的修繕改建,今年7月剛剛重新投入使用。
這是個很容易被“老上海愛好者”忽略的“懷舊地”,其實更確切地說,很多愛好者對這個重要的“上海景觀”還一無所知。
坐落于此已長達168年的仁濟醫(yī)院,是中國第一家綜合性西醫(yī)院。而其始建于上世紀30年代的西院2號樓,是目前上海存留的為數(shù)不多的最古老的醫(yī)院建筑之一,而且是唯一仍用作醫(yī)療的上海市優(yōu)秀歷史建筑。
說起來,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yī)院的實際年齡其實是169歲。
百度百科也許會告訴你,中國第一家西醫(yī)院誕生于廣州,確實,以“一口通商”比上海“開埠”早幾百年的廣州,早在1835年,美國傳教士伯駕就在那里開出了中國首家西醫(yī)院——廣州眼科醫(yī)局(廣州博濟醫(yī)院前身),因此以精確的細分來說,伯駕在廣州開出的是中國第一家專科西醫(yī)院。從史料看,廣州眼科醫(yī)局第一年接診病人2153人次,1840年因爆發(fā)鴉片戰(zhàn)爭停辦兩年。而以中國首家綜合西醫(yī)院開業(yè)的仁濟醫(yī)館,甫一開業(yè)就贏得了巨大的成功和聲譽。據(jù)記載,仁濟醫(yī)館在開頭兩年的接診病人數(shù)量就驚人地高達1.9萬人次,1844年至1856年,13年間共診治涉及內科、外科、眼科、婦科、骨科、燒傷科等各種中國病患達15萬人次。醫(yī)院還為民眾大量接種牛痘,幫助鴉片上癮者戒毒。這驕人的業(yè)績是廣州眼科醫(yī)局根本無法比擬的。
作為上海第一家、中國第二家西醫(yī)院,仁濟醫(yī)院自創(chuàng)建初期起便幾經(jīng)遷徙,不斷忙于擴張院舍規(guī)模,以滿足病人的就診需求。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2月,上海開埠后僅三個月,英國傳教士兼醫(yī)師威廉·洛克哈脫(William Lockhart)就在上海城內大東門一所租借民宅創(chuàng)立了“雒氏診所”。由于是上海首個西醫(yī)院,加之免費診治,許多無力求醫(yī)的貧苦百姓都前去一試。據(jù)洛克哈脫的《在華行醫(yī)20年》記載:“醫(yī)院一設立,建院宗旨就廣為人知,每日都有大批人群向醫(yī)院涌來,人們喧鬧著,急切地要求就診。病人不僅有上海人,還有許多來自蘇州、松江和周邊其他地區(qū),遠至崇明島。這些人們所表現(xiàn)的信任,即使在我們交流的早期,也顯得鼓舞人心。”
僅開業(yè)的最初8個月,醫(yī)院就接受治療了約8000名病人,其中女病人約占1/5。門庭若市、應接不暇的情形使醫(yī)院不得不盡快搬遷擴建。10月,洛克哈脫將診所搬遷至小南門外新租的四合院平房建筑內,設20個床位。因專為中國居民治病,“雒氏診所”改為“中國醫(yī)院”,又稱“華人醫(yī)院”。
1845年,洛克哈脫又以每畝40兩銀元的價格,租得了今福建路至山東路之間一塊5.5畝的土地,并在這里建成一所外形中式的兩層洋房,定名為“仁濟醫(yī)館”,取仁術濟世之意,亦稱“山東路醫(yī)院”。
1927年,仁濟醫(yī)院收到了英國地產(chǎn)商、慈善家亨利·雷士德的臨終捐贈,分別是1萬兩白銀和四處房產(chǎn)。也是在這一年,仁濟醫(yī)院開始建造新樓,地址就在上海最熱鬧的地段——山東中路145號。最初設計時,這只是一幢五層的建筑。在準備動工時,醫(yī)院董事會臨時決定再加蓋一層,將之前計劃五層擴展到六層,新增樓層用作醫(yī)院永久性的臨床科研部門,這也顯示出當年仁濟管理層對臨床科研的重視和成為臨床科研領跑者的決心。
1932年由德和洋行設計建造的六層洋樓正式投入使用,這所設備先進的現(xiàn)代醫(yī)院正式命名為“仁濟醫(yī)院”。醫(yī)院以“慈善”為名,施診給藥普濟貧病的百姓,求醫(yī)者愈來愈多。在之后80余年里,這棟英式建筑作為仁濟醫(yī)院的大本營見證了它運籌帷幄、獨領風騷的光輝歲月。西院老樓內曾經(jīng)專家云集,學科齊全,特色鮮明,消化學科、風濕病科更是國內醫(yī)學界的佼佼者,形成了集醫(yī)療、教學、科研于一體的綜合性三級甲等醫(yī)院,大量醫(yī)學人才和科研創(chuàng)新在這里誕生。
老一輩的上海人說到仁濟醫(yī)院,總會想起當年山東中路上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大病房”:“落地鋼窗潔凈明亮,鑲嵌木打蠟地板一塵不染。16張病床分成東、西兩排,過道寬敞可開小轎車……”然而,由于年久失修,老病房漸露窘態(tài),多處木地板已經(jīng)開裂,大量增加的病人也導致昔日的“大病房”如同大雜院般擁擠逼仄,被外界笑稱為“螺螄殼里做道場”。
與此同時,原來的醫(yī)療流程也跟不上現(xiàn)代需要。手術室被夾在病房中間,與監(jiān)護室、血庫、病理室隔開,一旦出現(xiàn)危急情況,很難最快時間內把監(jiān)護室的病人送到手術室。結構老化、功能缺失,成為制約仁濟西院緊跟現(xiàn)代醫(yī)療服務發(fā)展步伐的難題。
經(jīng)過兩年的“修舊如舊”工程,如今走入仁濟醫(yī)院老住院樓,仿佛坐進時光機回到了上個世紀30年代上海的老仁濟。復古壁燈、走廊拱頂、雕花護墻、深色地板、落地鋼窗等,將銘刻在老一輩上海人心里的“大病房”還原再現(xiàn)。
再定睛細看其實如舊實新。病房的裝飾設計中,處處顯示出對患者的人文關懷。所有病床之間都裝有隔簾,使患者的隱私得到有效的保護。根據(jù)患者病情的輕重來安排病房,讓醫(yī)療行為對患者的心理影響減至最低。為了解決西院場地狹窄給住院患者帶來的散步不便等問題,醫(yī)院還特意將住院樓陽臺進行了維修和加固,并加高安全護欄,讓患者在住院期間能有一個安全的散步場地。
修繕后的住院樓共有7層,樓內的醫(yī)療功能與內部設施完全按照現(xiàn)代醫(yī)療需求進行布置。每張病床后的多功能床頭設備帶除了常規(guī)的氧氣和吸引閥門外,還安裝了患者信息標志系統(tǒng)和呼叫系統(tǒng),將差錯率降到最低。
除了普通病房外,西院住院樓還設置了手術室、監(jiān)護室、產(chǎn)房等對硬件設備和環(huán)境潔凈度要求更高的治療單元,樓內的10間手術室與監(jiān)護室、血庫、病理室等集中在一個區(qū)域。據(jù)介紹,這些治療單元在設計的時候就充分考慮到了各自不同的醫(yī)療需求,并且安裝了空氣層流設備,確保單元內空氣的潔凈,最大程度地預防院內感染。此外,醫(yī)院還將通過整個住院樓的無線網(wǎng)絡覆蓋實現(xiàn)移動護理和移動查房,使得患者能夠在這古樸典雅的病區(qū)中享受到最先進、最溫馨的醫(yī)療服務。
“醫(yī)務傳教”的探索
作為晚清年代的一家教會醫(yī)院,當年仁濟的社會責任并不是簡單的行醫(yī)治病,還同時承擔了大量的社會救濟與人道主義援助工作。據(jù)《上海仁濟醫(yī)院史略》,直到1905年之前,仁濟醫(yī)院的賬務報表中幾乎沒有醫(yī)藥費收入一欄,因此這家施醫(yī)舍藥的慈善醫(yī)院很多年來一直被上海人稱為“施醫(yī)院”。遇上自然災害,為緩解饑荒,醫(yī)院還多次開設粥房施舍災民。僅1852年饑荒發(fā)生后的10周內,仁濟共施送米飯在34392碗以上。
事實上,“新事物”西醫(yī)院慈善和人道的背后是傳教授道、靈魂救贖的至高目的。1827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傳教醫(yī)生郭雷樞在澳門開設診所(后擴大為醫(yī)院),并建議英美教會應大批派遣傳教士醫(yī)師來華,拓展傳教事業(yè)。1835年,美國傳教士伯駕在廣州開出眼科醫(yī)局后,西醫(yī)傳入中國的速度越來越快,據(jù)統(tǒng)計,1876年在華教會醫(yī)院有16所、診所24所;到1905年,共有3445名傳教士來到中國,其中行醫(yī)者301人,教會醫(yī)院166所、診所241所。
上海開埠后就先后有近十家教會醫(yī)院在此落戶。上海市第一人民醫(yī)院的前身公濟醫(yī)院由天主教江南教會于1864年創(chuàng)辦,其歷史之久遠僅次于仁濟醫(yī)院,而其科室設置之齊全,曾為滬上之冠。瑞金醫(yī)院的前身廣慈醫(yī)院,取“廣為慈善”之意,法文名稱是“圣瑪利亞醫(yī)院”,是一所由法國天主教會在1907創(chuàng)辦的醫(yī)院。
“醫(yī)務傳教”是這一時期教會醫(yī)院的共同使命,他們深信,身體從破損到復原的變化不過是靈魂救贖的渠道而已。通過“醫(yī)務傳教”的辦法在中國人當中首先展示出慈善和人道的德行,并以此為階梯,漸漸引導他們思考這些德行賴以產(chǎn)生的動機和原則。
仁濟醫(yī)院的住院病人雖然每天被要求跟讀《圣經(jīng)》,還要遵守“Lady First”的“新奇”規(guī)定,但醫(yī)藥費全免,沒飯吃的窮人還可領到伙食費,這使得中國百姓無論理智還是情感上都對它無比親近。
不過,在治療過程中,傳教醫(yī)生們發(fā)現(xiàn),中國人在接受了身體的變化的同時,卻并沒有同時接納上帝。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歐洲文化研究院教授何小蓮指出,“有趣的是,當年傳教士醫(yī)師來到中國,藉醫(yī)傳教,醫(yī)是手段,教是目的,但在中國社會,最后深入人心的主要是醫(yī),而不是宗教。”
20世紀初,一項針對45所教會醫(yī)院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數(shù)進行統(tǒng)計的結果顯示,每所醫(yī)院每年平均有18人皈依,這意味著全國在一年當中只有4000多人踏入了教會之門,這個數(shù)字與傳教醫(yī)生所治愈的病人數(shù)字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現(xiàn)代醫(yī)療制度的先驅
“斷肢能續(xù)小神通,三指回春恐未工;倘使華佗生此月,不嫌劈腦治頭風。”這是19世紀70年代前期,一位從江蘇邗江來滬,號“六笏山房主人”的文化人,詠懷仁濟醫(yī)館的一首詩,表示了對西方醫(yī)術的一種驚異。
西醫(yī),作為東漸的西學的一個分支,是蘊含西學信息最為豐富的學科之一。透過西醫(yī),普通民眾從立竿見影般的醫(yī)療效果中,看到了以手術刀、顯微鏡為代表的西方近代技術,而先進的中國人則從中看到了西醫(yī)背后的制度安排,諸如醫(yī)院制度、醫(yī)學教育制度,更看到了由西醫(yī)體現(xiàn)出來的西方精神文明、倫理道德(人道主義),甚至整個西方文化。
中國人普遍接受西醫(yī)的背后,事實上也蘊含著傳統(tǒng)的醫(yī)療體系、衛(wèi)生觀念、醫(yī)患關系的近代轉型,這種轉型直接影響和塑造了今日中國人的醫(yī)療觀念。醫(yī)療空間從醫(yī)家到醫(yī)院的轉換,醫(yī)院制度的逐步完善,新型醫(yī)患關系的建立,新型醫(yī)療制度所體現(xiàn)的人道主義精神,對于中國傳統(tǒng)醫(yī)療體系是一種革新,對于現(xiàn)代醫(yī)療體系的建立則是醞釀和開端。
所以,在近代中國,當仁濟作為一家“醫(yī)院”、作為一個新事物被介紹和引進后,它所體現(xiàn)的現(xiàn)代文化意識就不能不對國人產(chǎn)生深刻而廣泛的影響。
在仁濟洛克哈脫們的努力下,中國現(xiàn)代意義上的醫(yī)院在教會醫(yī)院的引領和示范下逐步生長起來。從19世紀末開始,在中國,“醫(yī)院”已不僅是表面上人們所熟知包括候診室、門診室、住院部、隔離病房、手術室、藥房等在內的醫(yī)療場所,還是醫(yī)學教育和醫(yī)學研究的中心,是醫(yī)學知識的庇護所、醫(yī)學職業(y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機構、醫(yī)學權利的堡壘,是以醫(yī)院為基礎的醫(yī)學教育,以醫(yī)院為中心的醫(yī)學實踐以及系統(tǒng)的病歷記錄機構。
到民國年間,中國醫(yī)事系統(tǒng)已經(jīng)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西醫(yī)的知識、技術、西醫(yī)教育、西醫(yī)醫(yī)院,已成為中國醫(yī)事系統(tǒng)中的主體部分,傳統(tǒng)的中醫(yī)已退居從屬地位。在醫(yī)療行政方面,政府開始效法西方模式,醫(yī)事制度的衍變也逐漸呈現(xiàn)西化的態(tài)勢。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設立了衛(wèi)生司和官醫(yī)院,這是中國近代中央衛(wèi)生行政機構和官方醫(yī)院的雛形。
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十大醫(yī)院之一、當今中國重要的醫(yī)學人才培養(yǎng)基地和醫(yī)學科研機構,仁濟的歷史重合著西醫(yī)東傳的全過程,更展示著新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后中國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的巨大成就。與此同時,在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看來,仁濟所引領、實踐的西醫(yī)東傳,在近代中國,已經(jīng)超越了醫(yī)學本身,還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思想形成巨大的沖擊,對各種現(xiàn)代公共制度的形成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30年代的“高大洋”
各種史料表明,上世紀30年代,上海的西醫(yī)事業(yè)迅速崛起。以仁濟醫(yī)院為代表的教會醫(yī)院,都是在30年代規(guī)模上了檔次,并且基本上“定調”了隨后的一百年。
有記載表明,1932年,上海市注冊醫(yī)院為31家,其中西醫(yī)院為28家,總病床數(shù)1823張。而正是在這一年投入使用的仁濟西院大樓,已經(jīng)是一座擁有250張床位和綜合門診的六層現(xiàn)代化醫(yī)院,全年門、急診量達20萬人次。其實1922年時,仁濟就已經(jīng)擁有了上海乃至中國的第一架X光機。
事實上,到上世紀20年代,仁濟醫(yī)院已成為上海診治緊急病癥中心。透過那些留存下來已經(jīng)八九十歲“高齡”的門診記錄,上海街頭市井那幅喧囂混亂的畫卷似乎依稀再現(xiàn)眼前:黃包車夫飛快的腳步,有軌電車叮當作響的穿越,槍聲、哨聲、喊殺聲和慘叫聲此起彼伏,而工廠里剛剛購進的機器在轟鳴。彼時的中國,社會動蕩,機器作為龐然大物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在人們生產(chǎn)、生活中,由機器帶來的意外傷害也明顯增多。這些從地處上海鬧市中心的仁濟醫(yī)院門急診記錄中都可管窺一斑。據(jù)記載,1921年,仁濟醫(yī)院全年門診病人達9萬余人次,其中打架受傷者424人,刀傷84人,槍彈傷21人,跌傷317人;機器軋傷402人,電車傷54人,自行車傷117人;鴉片服毒自殺男37人、女29人,磷自殺男35人、女13人。1925年全年門診137152人次,其中車禍傷1837人,刀傷132人,槍彈傷22人,自殺1096人。
30年代上海西醫(yī)院的大發(fā)展,也與中國內科學大師黃銘新教授、中國外科第一刀蘭錫純教授等一大批醫(yī)學人才懷著“災難深重的祖國需要我”的信念從歐美等國學成歸來密切相關。他們懷揣的先進醫(yī)術、醫(yī)技和醫(yī)學理念,都在上海落地生根,創(chuàng)造出上海乃至中國的無數(shù)個第一,成為上海和中國現(xiàn)代醫(yī)學各個領域的奠基人,他們的名字及其創(chuàng)造的成就永遠鐫刻在了中國醫(yī)學史上。
中國人開辦的醫(yī)院陸續(xù)崛起
就在洋醫(yī)院大發(fā)展之際,中國人自己開辦的大中型醫(yī)院也在30年代陸續(xù)崛起。如今的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yī)院就是創(chuàng)始于1936年由國人自己創(chuàng)辦的一所規(guī)模較大的綜合性醫(yī)院,為紀念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而命名,1937年4月正式開業(yè)時建筑面積13597平方米,設有內科、外科、婦產(chǎn)科、兒科、泌尿科、眼科和耳鼻喉科等科室,開放病床有300張。
上海歷史最悠久的兒科專科醫(yī)院——上海交通大學醫(yī)學院附屬兒童醫(yī)院,其前身是由我國著名兒科專家富文壽及現(xiàn)代兒童營養(yǎng)學創(chuàng)始人蘇祖斐等前輩于1937年創(chuàng)辦的上海難童醫(yī)院。1954年更名為上海市兒童醫(yī)院,如今早就是集醫(yī)療、保健、教學、科研、康復于一體的三級甲等專科醫(yī)院。2010年位于普陀區(qū)長風生態(tài)商務區(qū)的新院動工,占地面積約39畝,核定床位550張。
1924年“本土”醫(yī)學博士盛才(原名盛清誠)決心在自己工作的楊樹浦一帶創(chuàng)辦醫(yī)院,因為當時的公立醫(yī)院、教會醫(yī)院、私人醫(yī)院都集中在上海市中心或富人區(qū),而滬東地區(qū)面積遼闊、工廠林立、勞工密集、貧民眾多,醫(yī)藥之需遠較市中心更為迫切,他把醫(yī)院命名為“滬東醫(yī)院”。
據(jù)盛才的兩個外孫女,如今旅居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徐瑾醫(yī)生和徐玨女士介紹,起初的滬東醫(yī)院經(jīng)費拮據(jù),設備簡陋,僅設了一張病床,但由于醫(yī)院服務周到,醫(yī)務日漸發(fā)展,病床也陸續(xù)增加,遠近有三十多家工廠職工來“團購”訂診。1934年,盛才傾其所有并向銀行貸款買地造樓,1935年滬東醫(yī)院主樓在眉州路34號落成。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上海淪陷,滬東醫(yī)院也處于岌岌可危之境,醫(yī)院業(yè)務也迫于停頓。一年后重起爐灶,再購大型X光機,添置手術室各項新式器械。盛才想盡辦法向國際紅十字會申請救濟物資,以應付戰(zhàn)時物資匱乏的狀態(tài)。
抗戰(zhàn)勝利后,滬東地區(qū)工廠相繼復工,人口激增,醫(yī)院又加建四樓,開辟新病房,添聘各科醫(yī)師,增設了多門專科,并在醫(yī)院后面購置了一幢宿舍樓。滬東醫(yī)院的業(yè)務蒸蒸日上,和滬東醫(yī)院簽約掛鉤的工廠多達97家。
在滬東醫(yī)院全盛時期,曾在醫(yī)院任職的外科醫(yī)師中,有剛從比利時回國的傅培彬醫(yī)生(后任上海廣慈醫(yī)院外科主任、二醫(yī)大一級教授和瑞金醫(yī)院院長)、上海醫(yī)學院畢業(yè)的黃偶麟(后任上海胸科醫(yī)院胸外科主任)、吳善芳、尢大鑣、董道鑄等;內科有上醫(yī)畢業(yè)的盛今純、史濟招等重量級名醫(yī)。1948年,盛才長子盛志勇從美國學成歸國后曾任滬東醫(yī)院醫(yī)務主任(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yī)院創(chuàng)燒傷外科主任、全軍燒傷研究所所長、教授,現(xiàn)為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
1956年盛才將其畢生經(jīng)營的上海滬東醫(yī)院,包括大樓兩幢、和各種醫(yī)療診斷、治療、康復的設備、圖書雜志等全部無償捐贈給國家,由政府改為公立醫(yī)院,盛才被任命為公立滬東醫(yī)院院長,并當選為多屆政協(xié)委員和人民代表。
1978年,在經(jīng)歷“文革”的各種磨難后,盛才病逝,1979年滬東醫(yī)院易名為楊浦區(qū)腫瘤防治院(后搬移到平?jīng)雎罚?5年滬東醫(yī)院史也畫上了句號。
去上海的老醫(yī)院懷舊吧,讓歷史就像一部舊電影在眼前播放。當你徘徊在山東中路上,也許會看到傳教士洛克哈脫夾著圣經(jīng)提著藥箱急匆匆地在拐進仁濟西院大門;當你沿著老樓梯尋找著新裝修的大病房,也許會與剛從五樓住院醫(yī)生的宿舍飛奔下樓的年輕蘭錫純不期而遇;當你在新加固的病房露臺上凝神發(fā)呆時,也許會聽見老克勒黃銘新放下小提琴,拿上stick,走出辦公室,微笑著與遇見的同事打著招呼,stick敲擊木質地板的“篤篤”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