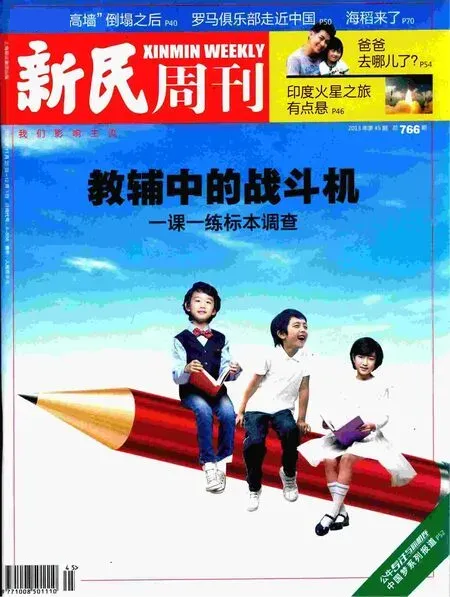重在解決“官官相護”形象
王若翰

作為一條獨立于司法體系之外的申訴途徑,多年來,信訪制度在民間的應用多少被賦予了一些“告御狀”的含義。在個別極端的案例中,信訪甚至成為了上訪戶不服法律判決,用來倒逼法院改變法律判決的一道殺手锏。
彼時,中央信訪局曾采取對各省份進行信訪排名通報的手段,希望使公民的上訪訴求在當地予以妥善解決,然而,出于地方政績等一系列原因考慮,各種形式的攔訪、截訪、勞動教養及黑監獄也由此而生。
一條本為確保群眾與中央之間信息通暢的道路,如今似乎荊棘叢生。縱有部分上訪人士穿越重重阻礙,最終到達首都,其中的大多數,也無非成為了中央信訪局方圓幾公里內長期駐扎的“滾地龍”。
一方面是信訪之路的崎嶇坎坷,另一方面是信訪之路上從來不缺少“后來人”,許多地方群眾在認為自身遭遇不公之時,甚至會選擇越過法律訴訟的途徑,直接上訪。
這樣的矛盾,其深層次的原因何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其中有關涉法涉訴信訪的改革,為以上問題提供了怎樣的解決途徑?
“上訪媽媽”成歷史
近年來公民信訪的極端案例,最典型的上訪代表莫過于湖南的“上訪媽媽”唐慧。唐慧從受害者家屬,到鍥而不舍的上訪戶;從當地政府眼中無理上訪的釘子戶,到被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區分局勞動教養。2013年7月15日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判唐慧訴永州勞教委一案勝訴,唐慧案中諸多情節翻云覆雨,備受關注。
在唐慧一次次的上訪過程中,我們先是看到了一位母親為了替女兒討回公道,而要求有關部門對此事進行立案的堅定與執著。隨后,在事態的進一步演變中,有關唐慧要求判處7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死刑的傳言,以及在死刑復核期間不顧司法程序,一再上訪催促死刑立即執行的行為,又似乎凸顯了一位普通婦女的盲目與無理。
網絡傳言中,唐慧上訪時采用了極端手段,對此,唐慧本人只承認曾在法院辦公樓大廳內以地鋪的形式夜宿,并滯留長達15天之久,對于其他不雅舉動的說法,她則予以否認。“我只是在那里跪著,沒有妨礙其他人。”這是唐慧對自己上訪方式的一句概括,當被問及為何不能正常反映情況,而一定要下跪,唐慧當時的回答是:“希望能感動領導。”
按照我國現有的信訪條例規定,信訪制度是指公民個人或群體以書信、電子郵件、走訪、電話、傳真等參與形式與國家的政黨、政府、社團、人大、司法、政協、社區、企事業單位負責信訪工作的機構或人員接觸,以反映情況,表達自身意見,吁請解決問題,有關信訪工作機構或人員采用一定的方式進行處理的一種制度。
由此可見,信訪制度中規定的信訪方式,主要強調公民表達意見的途徑,即通過何種途徑可以將問題順暢反映至相關部門并陳述清楚,反觀唐慧上訪過程中的舉動,不管其是否妨礙受訪機構的正常工作秩序,都已經超出了信訪制度中的正常方式。
勞教廢除,纏訪何解?
在唐慧案之后,記者也曾接到過許多上訪者打來的電話,其中大部分對自己如何被地方政府攔訪、截訪以及如何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進行勞教的情節加以重點描述,但對于自身的上訪訴求,以及該訴求的合理性卻一筆帶過。一些上訪者甚至無法為自己的訴求找出充分的理由,但仍舊堅信只要能上訪到中央,自己的訴求就會實現,他們認為,上訪期間,不管采取怎樣極端的上訪方式,有關部門都無權限制自己的人身自由。
毫無疑問,在唐慧訴永州勞教委一案中,唐慧的勝訴無疑為許多有過類似經歷的上訪者提供了參照樣本。盡管當時,勞動教養制度尚未被廢止,有關唐慧勝訴的判決,也是基于永州勞教委無法出示唐慧在上訪過程中,存在擾亂社會正常秩序的證據。但多數上訪者顯然只將這一判決結果,簡單地歸納為不管自己的上訪手段如何極端,只要尚未觸犯刑法,就不該受到處罰這一層面。
在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除有關涉法涉訟信訪制度改革外,“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成為廣受關注的一大亮點。自此,持續了50多年的勞動教養制度,終于壽終正寢。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部分公共治安管理部門對《決定》中的這一內容提出異議,一些具有公安背景的公職人員指出,勞教廢除后,對于一些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的纏訪、鬧訪者的處罰,將無從下手。
針對這樣的問題,華東政法大學刑法教研室主任沈亮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指出:對于上訪過程中的纏訪、鬧訪等行為,如果情節確實構成擾亂社會正常秩序,可直接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處理,如果上訪中采取暴力手段造成嚴重后果的,甚至可以依照刑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這些問題在正規的司法途徑里都有辦法解決,并不是一定要靠勞動教養約束的。因此,勞動教養的廢除,并不會使這些輕度擾亂社會治安的行為在處置上無法可依。
信訪也需依法終結
在信訪制度改革之前,多數訪民的上訪路線如出一轍:當地上訪沒效果,隨后越級上訪,繼而進京上訪。據有關數據顯示,2005年以來,直接進京上訪的訪民數量驟然增加。由于國家對各個省市、各個省市對各個地市、各個地市對各個縣區都實施“信訪排名”、“責任追究”等制度,因此,各地派專人進京攔訪截訪的事例屢見不鮮。
“除個別胡攪蠻纏為自己爭取不合理利益的上訪者外,大多數訪民一再上訪的原因,還是由于各地對于訪民的合理訴求沒有很好地解決,逐漸導致訪民對地方的信任度下降,最后大量的訪民進京訪。”沈亮指出,由于這種不信任,導致一些群眾在遇到問題時,選擇直接上訪,不試圖用法律手段解決。而事實上,按照我國一貫的信訪制度,即使是進京上訪,國家信訪局收到了上訪信件,也大多是層層批轉,由省一級批轉到地市,由地市批轉到縣區,相當于兜了一大圈,最后還是回到區縣解決問題。這就在客觀上造成了很多訪民信訪無結局的情況,導致他們一次次地進京上訪。
在沈亮看來,此次的《決定》中,中央政法委提出的有關涉法涉訟信訪的制度,規定把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解決,無疑是信訪改革中的一大亮點。“在當今的法治社會,我們的制度應該盡量引導公民去通過法律途徑進行訴訟,而不是引導公民上訪。一樁案件,經過兩級人民法院裁定,其最后判決結果,既被視為最終結果,當事人如果再不服判決進行上訪,即被視為非法上訪,有關部門應先予以勸告,如當事人再糾纏不休,則可依法處理。”
沈亮表示,這樣的改革必須是自上而下的,要讓公民相信法院,選擇通過司法途徑解決問題,中央層面必須在頂層設計上,對各地方法院和檢察院設立直屬管理,使其脫離地方政府,才能擺脫公民心中司法部門與地方政府官官相護的形象,使法院判決更具有可信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