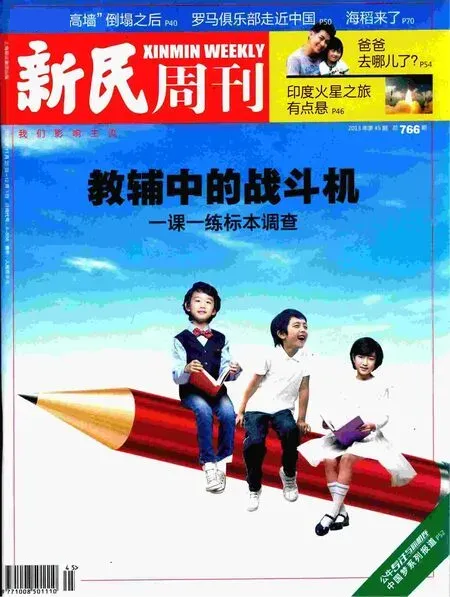曾經的大慶與今天的回望
沈嘉祿


西姚家弄是上海老城區內一條很不起眼的街道,在這個落葉遍地、空氣潮濕的秋天,被我傷感地重走一次。它深藏在歷史的磚縫中,名氣遠不如鄰近與徐光啟祖居有關的光啟路、與郁泰豐和王一亭有關的喬家弄、與任伯年有關的三牌樓路,但歷史向我們指出,在170年前的1843年秋天,剛剛被任命為首任英國駐滬領事的前印度馬德拉斯陸戰隊上尉巴富爾,從廣州登上“威克遜”號軍艦北上,到舟山再換乘“麥都思”號郵船,于11月8日抵達上海十六鋪碼頭。他帶著十幾個隨從以及笨重的行李,走進這條幽深的小街,租下一位顧姓商人的大宅子。這處大宅子叫敦春堂,典型的粉墻黛瓦中式建筑,52間屋子足夠領事館使用了。
今天,敦春堂已灰飛煙滅,小街上的房屋也換了幾茬,七老八十的“土著”對敦春堂的傳說一臉茫然,但有一棵胸徑超過60厘米的楓楊樹從一堵斑駁的圍墻后面伸出,最后的幾片樹葉在寒風中微微顫抖。它應該是敦春堂的見證者。
洋人落戶“城里”的消息不脛而走,許多上海市民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大搖大擺地進入敦春堂,像觀賞野生動物一樣來看洋人的西洋鏡,令巴富爾非常尷尬。窺得他者隱私的市民心滿意足地回家了,在菜油燈下當作聊齋故事來講給別人聽,但他們絕對預見不到異質文明的強行植入,將不可阻擋地改變上海人的生活以及觀念。
巴富爾的辦事效率相當高,11月14日領事館開張,11月17日即與上海道臺商議后劃定了外國人居留地界址,并宣布上海正式開埠。上海由此開始新的篇章。
接下來的故事可以用“峰回路轉”或“波瀾壯闊”來形容,當然,在主流歷史敘事之外,我們還可以通過觸摸西姚家弄的墻磚與門環來回望。比如影響市民生活與話語的細節非常龐雜,過去中國人對外來事物的話說總是居高臨下的,比如“胡床”、“胡麻”、“胡蘿卜”、“胡椒”等,還有“胡說八道”、“胡思亂想”、“胡作非為”,帶一個“胡”字的似乎就有原罪,至少不是好貨色。后來是“番”字,戲文中有“番邦”,食物中有“番薯”、“番茄”,最早在上海經營的西菜館叫“番菜館”,洋人被叫作“番鬼佬”,洋太太、洋小姐則被稱作“番婦”。再后來,隨著文化沖突的加深,稱異質文明為“夷”,租界為“夷場”,公園為“夷園”,在辦洋務時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是,實事求是地說,開埠后的半個世紀里,殖民者對租界的規劃設計與整治是卓有成效的,他們在第一時間引進了西方文明及工業化成果,也通過收稅理財、筑路修橋、駐軍設警、引進現代司法制度、開辦西式醫院和育嬰堂、傳播基督教、開辦教會學校等手段強化掌控城市的能力。特別是自來水、煤氣、電報、電話等新玩意兒對中國經濟及社會生活產生了直接影響,大大提升了上海的文明程度與生活質量。中國人只得放低身段,而且越來越低,在日常語境中也不知不覺易“夷”為“洋”了,即使是民族工商業開始艱難崛起的歲月,即使在抵制洋貨的呼聲中,“洋火”、“洋釘”、“洋油”、“洋皂”、“洋灰”等俗語仍以水銀瀉地之勢,昭示著當時的現實:中國經濟已土崩瓦解。
讓我們來個閃回吧。鏡頭切到1893年,上海迎來了開埠50周年之際。租界當局對這個時間節點極其重視,早在一年前就登報公告,征集納稅人對這一慶典的意見、建議。當年4月還專門成立了“上海租界50周年慶典委員會”,由工部局總董親自掛帥,另有11位名媛太太組成“女士輔助委員會”。西方列強來到上海,除了貿易,還希望在上海區域性克隆資本主義制度與國際商貿城市的模式,同時也為他們的代理人及中國民族工商業者創造了競爭的機會。所以,開埠50周年大慶也成了租界當局炫耀政績、強調價值觀的極佳機會。
于是租界當局忙著定制紀念章、發行紀念郵票、在外灘公園里安裝噴泉,連黃浦江上的兵艦也披紅戴綠。他們還上門聯絡租界內的華人會館,跳個舞吧,一起“華洋同慶”。1893年11月17、18日兩天,上海租界內的主要馬路張燈結彩、五光十色,除了軍事演習、演說、游園、焰火和燈會外,動員人數最多的還是慶祝游行。一百多年后,當我面對記錄這一慶典的照片和《點石齋畫報》、舊校場年畫時,足足驚愕了一小時。有圖有真相,這一盛況以及當年中國民眾所投入的熱情,以及媒體對此的積極報道,對我讀小學時就被植入的宏大觀念形成堅硬的沖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人民狂歡?
當然,事情也并非那么簡單。后來通過對史料的梳理與解讀,我終于明白,對開埠50周年大慶這檔事,上海“土著”的態度比較冷淡。洋鬼子來了,占地為王,吸金如魔,上海延續了數百年的農耕文明受到極大破壞,小農經濟空前凋敝,到處充斥著物欲、欺詐、貪婪與自私,士紳階層大扼腕長嘆今不如昔:“每作別有天地非人間之想”,“今人不能耐之,思欲求一心曠神怡之境界杳不可得。”而從慶祝游行隊伍中處于華人主體的兩大族群來看,是寧波幫與廣東幫,他們高舉寫著“絲業會館”、“通商大慶”、“廣肇公所”、“廣幫瑞獅”等字樣的旗幡、燈牌甚至極富戲劇色彩的萬民傘等中國風格道具,浩浩蕩蕩行進在外灘與大馬路之間,所到之處,萬眾喧騰。先富起來的寧波人和廣東人似乎都理直氣壯地認為:是租界這種模式給他們提供了大量的創業機會,使他們毅然走出地少人多的故鄉,登陸上海實現自己的夢想。歷史地看,這兩大族群的移民對上海之所以成為上海,是做出重大貢獻的,他們是上海開埠最勇敢的實踐者和最直接的受益者。而租界當局召集華人投身于這場慶典的另一層用意在于:讓公共租界的華洋雙方謀求合作發展的共同心愿得到宣泄與肯定。租界的成功辟建與后續發展,都在表明要處理好與華人商社的關系,在利益分割和城市管理時保持美妙的平衡。
于是,我們接下來就看到,工部局和公董局在慶典之后不久的1899年、1900年、1914年、1915年,多次通過越界筑路或強租等手段,使租界向西、向北擴張,“疆域”數倍于《上海土地章程》共同擬定的面積。
上海開埠有50周年“大慶”,但沒有100周年“大慶”——強加于中國的不平等條例被廢除,租界已收回。在改革開放后的1993年,在史學界和坊間卻幾乎沒人提及上海開埠150周年這檔事。而今年上海開埠170周年之際,卻被人經常提及。“華洋同慶”及萬民傘是沒有必要了,但審視與思考卻可以向著廣度與深度而去。經過35年的改革開放,大踏步行進在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的中國人民,已經獲得了足夠的自信,可以在歷史大事件、大動蕩、大變革面前多一份從容、大度與深刻。
西姚家弄的那棵楓楊樹,根深葉茂、飽經滄桑,但愿在舊區改造中能夠延續其頑強的生命,在新時代的和風細雨中,夜夜諦聽外灘海關的鐘聲。
老上海的水電煤
煤氣燈:19世紀60年代中期上海進入煤氣照明階段。1864年3月,上海第一家煤氣公司大英自來火房開張。次年制成煤氣燈,在多家洋行試用后于12月18日在南京路正式點燃第一盞煤氣燈。
電燈:1882年4月,上海電光公司創辦,7月26日,公司在英美租界裝成弧光燈15盞,在虹口招商碼頭、福利洋行、禮查飯店等處試燈,這是上海第一次亮起電燈。1897年,英美租界街道的煤氣燈全部換成電燈。
自來水:1860年旗昌洋行在外灘開鑿了第一口深水井,供內部使用。1872年租界建成第一座小型水廠。1875年,西商在楊樹浦建成第一座自來水廠。1880年,英商上海自來水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其他市政設施:灑水車、垃圾車、救火會、自鳴鐘等都在19世紀70年代前傳入上海。
生活用品方面:縫紉機、自來風扇、火柴、肥皂、洋傘、牙刷、牙粉等也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輸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