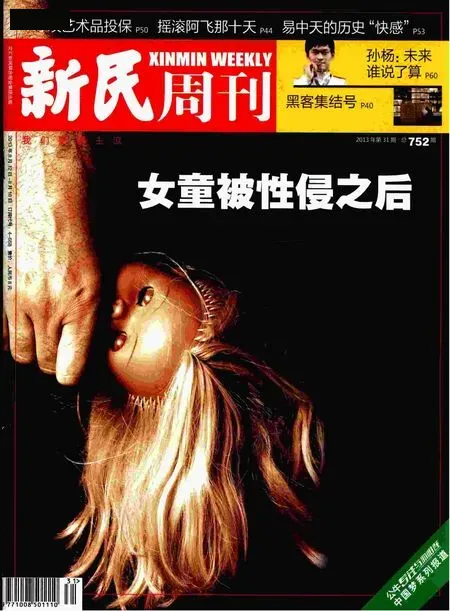提籃橋
沈嘉祿
在上海人的日常語匯中,提籃橋有兩個概念。一是指特定區域,也就是提籃橋這個上海歷史文化風貌區,涵蓋周邊的霍山路、舟山路、長陽路、昆明路等,其建筑特色為“特殊建筑和里弄住宅、宗教場所”,這里有三十多種西方建筑的樣本,至今保存基本完好。二是指素有“遠東第一監獄”之稱的提籃橋監獄。這座監獄建于1903年,在整個中國屬于使用歷史最悠久的監獄。由公共租界工部局設計建造,時稱華德路監獄,并由英國人管理。民國初年關押過章太炎、鄒容等反清志士,可以設想的是,如果沒有提籃橋監獄這一現代司法制度承載者的“蔽護”,他們將在清政府大牢里死得很難看。后來,這里還關押過革命者與民主人士。直到1943年收還租界后,才由中國人管理。抗戰勝利后曾關押過數百名日本戰犯,1946年初,盟軍在提籃橋監獄設軍事法庭,審判47名日本戰犯,這是抗戰勝利后中國境內最早的戰犯審判場所。汪精衛之妻陳璧君也在提籃橋監獄服刑。
前不久有消息見諸報端,立即引起坊間喧嘩:提籃橋監獄將關閉,百年老建筑將進行一番富有想象力的改造,或成時尚高地,或為高端寫字樓,高級賓館拔地而起也不是沒有可能,這一帶缺少五星級賓館已久矣!但是,提籃橋監獄的歷史文化價值,又豈是華館崇樓所能代替?
我打電話至監獄管理局的朋友,朋友告訴我:在整個上海已經找不到一塊可以另外建造大型監獄的地皮啦!即使上海方面同意置換,還得報請司法部批準,至少在近期,這個計劃難以實現。他還透露(因涉及國家機密,此處刪去200字)……,也許會搬遷到郊區某設施良好的監獄。朋友還表示,一旦大限將至,可讓我前往采訪。看來,搬遷已進入讀秒階段。
拜持續超過半月的39度高溫天所賜,我也在頭昏目眩中設想提籃橋華麗轉身后的面目,數年前探訪這座監獄的一幕幕情景漸次在眼前浮現,厚重的大門還是當年的遺物,推拉甚是輕巧,但監獄方面已在同一地點加設了一道電動移門。我去的那天,正好看到監獄方面安排一百多號犯人排好隊,依次在一堵寫有“向雷鋒同志學習”的照壁前拍照,照片沖洗后可寄回家里以慰娘親。還看到監獄所設的印刷廠正在熱火朝天地工作,所印之物有點像考卷。在監獄電視臺的錄播室里,一個眉清目秀的犯人主持人正在“很正規”地采訪監獄長。在一間不算很大的工作室里,有大約七八個犯人正埋頭翻譯外文資料,他們有意舉起書本遮蔽自己的臉。陪同警官告訴我,這些犯人為知識分子出身,多涉及經濟案件,監獄方面讓他們搞翻譯,以免荒廢術業。翻譯是有稿費的,所得可改善生活。
監房內的柵格狀走廊和鐵門也是當年的老古董,犯人動靜一目了然。順著一排監房走去,所到之所就會有領頭的高喊一聲:“首長好!”其他犯人馬上起立呼應,讓我很不習慣。監房很小,只有三個多點平方,當初設計是關一個犯人的,現在擠了三個,鋪位搭得像一個“上”字。順著一陣悠揚的單簧管,我們來到女犯監獄,那里有數名女犯是新岸藝術團成員,正在排練節目。其他女犯在監室里動作熟練地包裝濕紙巾,監室干凈敞亮,兩排雙層床上,每人的被子疊得像刀切豆腐一樣整齊。我還嗅到了一股淡淡的茉莉花香。新岸藝術團也偶爾去其他監獄及公共場所演出,所到之處大受歡迎。據說女犯人在上臺表演節目前允許抹口紅。
逢年過節,監獄里會組織犯人聯歡活動,地點就在廣場中央。監獄周邊已經建起了高十幾層的商品房,華燈初上,犯人載歌載舞時,居民們也會撲在陽臺上觀看并鼓掌喝彩。有犯人還會跟他們打招呼:“小心點!別一個跟斗翻進來,進來容易出去難啊!”
是啊,進來容易出去難!同樣的,拆毀容易保存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