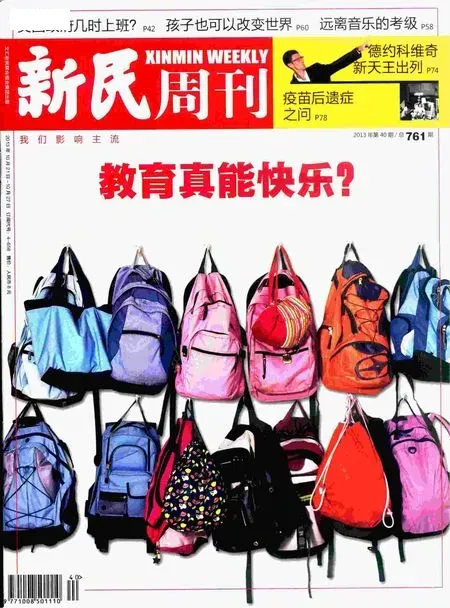減負,真的沒招了?
黃祺 謝璨燦


“戒煙最容易,我已經戒了好多次了。”如果把“減負”替換進剛才的這句笑話,歪邏輯依然成立:“減負最容易,我們已經減了好多年了。”
每年9月開學季,所有人都知道,又要談“減負”了。今年最引人矚目的“減負”消息有兩條。9月8日,教育部前發言人王旭明在自己的微博上呼吁:“取消小學英語課,取締社會少兒英語班,解放孩子,救救漢語!”即便已經不在教育部門工作,王旭明的言論還是引起了媒體的廣泛報道,顯然,他的話得到不少人的認同。
后一條新聞可以用“跌宕起伏”來形容,國家教育部就新的小學生減負規定向社會征求意見,其中一條看起來“大快人心”的規定——小學一至三年級不布置書面作業,竟然遭到最多的反對。
兩條新聞反映出中國社會對“減負”、對教育的矛盾心態,一方面我們希望孩子們能快樂,但面對社會競爭,我們又不得不要求孩子們接受更多的訓練,以便有能力去應付這個現實的社會。
教育是與社會環境聯系最為緊密的領域,因此,任何脫離社會需要來批評教育的意見,都不可取。如果用更加客觀的眼光看待今日的教育,中國的教育方式真的那么差嗎?這些年“減負”減到點子上了嗎?中國教育弊病只是教育的問題嗎?毫無負擔的教育真的是好的教育嗎?
作業困境
距離國慶長假結束還有兩天,初一學生曉禹(化名)開始有些心事重重——老師布置的假期作業只做完三分之一,還有6張試卷等著他完成。如果按照一張試卷2小時的速度,他需要12個小時,這意味著,接下來的2天除了吃飯睡覺,幾乎都要趴在桌子上了。
曉禹小學階段成績優秀,目前在中國內地三線城市的一所初中上學,這所學校在當地算得不錯,曉禹在新班級里也保持著學業上的優勢。但這名“好學生”不得不承認,自己長假的前幾天實在是有些“放縱”:跟著大人走親訪友,約上小學時的小伙伴玩滑板,一天的時間一眨眼就混過去了,哪里還想得起作業的事。
曉禹母親也“縱容”了兒子幾天,現在不得不在兒子頭上懸起“警鐘”:“明天7點起床,哪兒都不要去了。”其實,曉禹母親也有些矛盾,13歲正是精力旺盛、喜歡交友、喜歡運動的年紀,而現在的孩子卻要把絕大多數時間花在課堂、花在作業上。
曉禹的經歷,是長假中很多中小學生的縮影,據說,有的孩子隨父母旅游,只能在大巴上趕作業。作業,被視為中國基礎教育階段學業負擔承重的象征,因此,在中國教育界提出的各種“減負”措施中,減少作業量是必不可少的一環。
可是,不做作業就能讓怨聲載道的學生和家長滿意嗎?
教育部8月22日發布《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征求意見稿)》,其中第四條的內容是:“不留作業。小學不留書面式家庭作業,可布置一些適合小學生特點的體驗式作業。”
規定的制定者一定以為,這樣的規定會得到學生、家長以及社會各界的支持,因為過往在討論學業負擔過重時,學生和家長抱怨最多的,就是作業太多,學生休息和活動的時間太少。
但反饋意見卻充滿戲劇性。在收到的近6000條意見中,九成對陽光入學、均衡編班、“零起點”教學、規范考試、嚴禁違規補課、每天鍛煉一小時等規定表示支持。不同意見主要集中在小學階段留不留作業問題,大多建議還是傾向于小學高年級應該適當留些作業。
面對洶涌的民意,教育部第二次征求意見的“減負”規定中,關于作業的規定變成:“減少作業。一至三年級不留書面家庭作業,四至六年級要將每天書面家庭作業總量控制在1小時之內。要積極與家長互動,指導好學生的課外活動。”
作業多了大家抱怨學生太苦,作業少了大家又不同意——作業困境映射出中國教育的困境。教育部門主導的“減負”年年有新招,但學生的學業負擔卻越減越重;“零起點”、“素質教育”、“快樂教育”提倡多年,但學生卻沒見快樂起來。
很多家長因此對中國教育失望甚至絕望,送子女去海外讀書早已成為風尚,還有家長讓孩子“在家上學”,以逃避他們不能認同的學校教育方式。
什么是“減負”
2013新學年,上海市閘北區一所公辦小學的朱老師又迎來一批新學生。媒體上,上海將全面推行小學“零起點”教學的新聞鋪天蓋地,新聞中說,上海在小學一、二年級全面推行“基于課程標準的教學與評價”(即“零起點”教學和等第制評價),教師不能隨意拔高教學和評價要求,不能隨意加快教學進度。
聽記者講起這條措施,當小學教師已經十多年的朱老師反應平淡:“‘零起點我們一直在做啊,今年沒有什么特別的措施。”“減負”年年講,身處教育一線的老師有些“審美疲勞”,跟教師一樣“疲勞”的還有家長和學生,大家心里都明白,“減負”減它的,該補的課還得補,該做的習題一道都不能少。
難怪公眾對“減負”習以為常,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巡視員、著名教育專家尹后慶的統計,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歷代領導人都曾關注過“減負”問題,由國家下發的“減負政令”不下50件。早在上世紀50年代,教育部就曾發文要求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
“減負”60年,讓人尷尬的是,學生負擔越減越重,公眾因此對“減負”失去信心。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基礎教育處處長倪閩景在向《新民周刊》談起這個尷尬時,一點也沒有避諱,對于“減負”困境,他也從未停止過思考和探索。
倪閩景認為,“減負”這個詞本身就不夠準確。“讀書本身肯定就是有負擔的。我們反對的是對學習來說沒有意義的負擔。”采訪一開始,倪閩景就闡述了他對學業負擔含義的認識。“減負”多年后,學業負擔的概念變得模糊不清,一度,人們把毫無壓力的學習當作“減負”的目標。
學習都有壓力,這一點,其實不難理解。很多成功人士在回憶自己的成長經歷時,都喜歡談起兒時求學的辛苦或者嚴師的苛刻,但大多數人把這些“學業負擔”,視為自己成長過程中的正面動力。最近一篇名為《誰說死記硬背會扼殺創造力?》的文章在網絡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美國作者從他兒時的音樂老師談起,討論嚴師對于教育的意義。作者的結論是,批評、懲戒、壓力在學習的過程中有獨到的作用,而創造性與刻苦的訓練并不矛盾。
由此,學業負擔就不僅僅是一個“量”的問題,毫無負擔的學習本身就值得懷疑。倪閩景講起一個例子,在他做老師的時候,他曾指導學生做科技課題,攻關階段,一幫學生跟著他奮戰48小時,餓了吃面包,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一會兒。但學生們樂在其中,一點都沒有喊累。
這樣說來,快樂學習并不等于零負擔的學習,倪閩景認為,“減負”是要提高教育的效率,盡量減少那些對學習無意義的學業負擔。
不快樂從哪來?
但現實卻是,大量學生的確還在為無意義的學業負擔付出巨大的精力,“減負”為何越減越重?
一個最常見到的說法是,高考是學業負擔的罪魁禍首,看看那些“神一樣的學校”,你就會相信這一點。從經濟上看,衡水市是河北省比較落后的城市,但卻讓高中生們趨之若鶩,衡水中學,就是一所“神一樣的學校”。今年高考,考入北大清華的衡水中學畢業生有104名,進入港大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有77名。如此傲人的成績背后,是高中生們每天從早上5點半到晚上10點10分“無縫式”的學習節奏,這樣的強度,很難說有多少快樂。
曾經,改革高考被認為是“減負”的靈丹妙藥,但是,經過了高校擴招、部分高校自主招生、高考科目改革等種種改革后,學生學業負擔重的狀況并沒有多少改善,相反,全國各地像衡水中學一樣的“高考機器”風生水起,這些學校重壓出成績的應考方式,成為了其他中學效仿的目標。
今年,高考改革又傳出新的消息。有媒體報道,江蘇省正在醞釀的新高考方案中,有意嘗試探索英語科目的“一年兩考”,不再計入總分,而是以等級形式計入高考成績,高校在錄取時將對英語等級提出要求。
江蘇歷來是高考大省,由于考生眾多,要進入高質量大學,需要付出比其他地區學生更多的努力,學業負擔也要重得多。但是,江蘇的計劃很快被一些教育界人士認為不但不能為學生“減負”,反而會增加負擔。
上海也透露了一些新舉措。媒體報道,上海高中生的學業水平考試成績,今后將會用于大學自主招生選拔、作為目前高校自主招生的資格初試甚至代替筆試成績,新政將在未來幾年內開始實施。但也有一種說法認為,上海高中生為了應對學業水平考,整個高中三年都在應試,學業負擔更繁重了。
和上海的新措施類似,很多高考相關改革措施的初衷都是為了緩解“一考定終身”的壓力,但措施頻出,學業負擔卻沒有減輕多少。
在倪閩景看來,高考還有改革的空間。“一方面要提高命題的科學性,我們的考試題目一會兒難一會兒簡單,弄得孩子們沒有方向,命題應該基于課程標準,提高命題人員的專業化培訓,利用考試的指揮棒作用,讓學生們拋棄死記硬背、反復操練的模式。另一方面,高考報名要逐步走向社會化報名,避免區域和學校之間的比拼,逐步在社會上形成教育教學是學校的事,但考試是孩子自己的事。”
倪閩景還認為,從長遠來看,必須要提高學生對考試科目的高選擇度,這需要高校招生政策的調整。到了高中,有些孩子的優勢項目會慢慢凸顯出來,而考試就這么幾門,實際上是扼殺學生志趣和專長的。
近幾年部分高校推出花樣眾多的自主考試,宣稱是為了增加學生的選擇機會,但倪閩景卻對此并不樂觀。“現在的千分考、華約北約等考試,雖然對高校招生有一定價值,但從減負角度是起反作用的,因為考試的內容依然是高度一致的,高校依然是站在掐尖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的,沒有考慮招生對基礎教育的強烈導向作用。如果高校以專業平行志愿為主,學生可以在語文、數學必考的基礎上,自由選考與專業相匹配的科目,那么,學生在高中階段的個性發展將十分突出,而高校也能找到真正需要的人。這個模式叫做愛爾蘭模式。”
但高考改革不等于降低考試難度。“簡單地降低高考、中考難度,或減少考試科目,不可能減輕學生課業負擔。試想高考就考一門語文,語文就考一項內容寫字,寫字就考寫一個字“大”字,相信全國的孩子都會瘋狂地陷入對應的更無聊的應試訓練當中去,負擔一點兒都不會輕。這個判斷告訴我們,學生學習負擔本質上不是考試的難易問題。所謂的負擔重,不如說學習沒有意義,我們要思考與改進的是如何讓孩子們學得更有意義,也需要反思的是我們的高考、中考除了選拔,還有其他意義嗎?
教育需要啟蒙運動
倪閩景對“減負”越減越重的現象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就像在電影院看電影,如果第一排的觀眾站起來看,第二排也會跟著站起來,最后全場的人都站了起來。同樣看完一場電影,但大家都累死了。”顯然,高考并不是導致第一排觀眾站起來的唯一原因。
如果教育系統的“減負”措施都能夠實現,中國的學生們就真的能夠快樂起來嗎?現實中的事例證明,答案是否定的。
“學校規定說不讓學生把書包帶回家,家長就去學校偷書,或者買一套教材放在家里。” 倪閩景說到的不是笑話,而是真事。尹后慶把這種現象叫做“按下葫蘆起了瓢”:教育系統為學生減負,家長那邊卻帶著孩子補課、買習題書,自己給自己的孩子加碼。
可憐父母心,倪閩景說,家長的做法是現實的選擇,但社會對于教育需要一場啟蒙運動,家長也需要明白教育本身的規律。
“不是每個孩子都一樣,人是有差異的,人的智商也有差別。同樣的作業,有的學生覺得不多,有的做得慢,就感覺太多,壓力太大。”倪閩景的說法恐怕很難被一些家長接受,他們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比別人差,哪怕是“一般般”也不可以。
家長們的心態與這個時代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社會轉型期,家長對孩子的期待往往非常高。迪士尼經典動畫《藍色狂想曲》中有一個情節,一位媽媽拖著小姑娘上舞蹈課、鋼琴課、美術課、網球課,大街上穿梭著帶孩子“趕場子”的家長們。倪閩景認為,從社會發展程度看,現在的中國跟上世紀20年代的美國非常像,而如今中國的教育現象,也曾出現在那個時期的美國社會。
家長的心態表現出代際的變化。“我的父母,完全不知道教育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們小時候沒有來自父母的壓力。”中國的60后70后有著和倪閩景類似的感受,這些人成為家長后,由于對社會競爭有著深刻的體會,他們往往對孩子有更高的要求,而當80后90后逐漸成為家長,隨著經濟的發展,他們給子女的壓力,會小很多。
社會的焦慮需要時間化解,作為教育官員,倪閩景首先考慮怎樣通過改善教育行為來減輕學生學業負擔。倪閩景說,教師是專業人士,教師應該知道小學生需要9小時的睡眠,在布置作業的時候,就要考慮到學生的休息時間,不僅要考慮自己布置的作業量,其他科的老師還有作業。
要改變教師的教育行為,就必須改變對學校和教師的評價方法,從2010年開始,上海教育系統推出“綠色指標”,這個由眾多要素組成的復雜評價系統,試圖改變教師只關注成績的行為。倪閩景介紹,改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連續12次對課業負擔的監測中,直到2011年學生學業負擔才開始出現下降的趨勢,到目前已經連續兩年下降。
透過這個指標,倪閩景還發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比如,師生關系越好,學生成績越好;學生學習動力越強,成績越好。倪閩景認為,這些結論反饋到學校后,教師們會更加注意自己的行為——布置太多作業的老師,容易引起學生反感,師生關系自然不會好,如果老師發現師生關系融洽會提高成績,那么他又何必去布置那些過量而無意義的作業呢?
回到對學業負擔的定義,倪閩景認為,學業負擔一定伴隨著學習的過程,減輕不必要的學業負擔,需要遵循教育自身的規律。“學業負擔應該是有梯度的,年齡越小應該越輕,幼兒園小學階段應該非常輕松,隨著心智的成熟,承受壓力的能力越來越強,學業壓力也應該逐漸增加,按道理,大學階段應該是最重的,我們現在是反過來了。”
遵循這樣的規律,上海市很早就開始從小學入手,為低齡學生減負。2008年開始,上海開展“幼小銜接”,小學新生入學的前2個月用來適應新的環境和學習方法,不上新課。另外,前年開始小學每周有半天“快樂活動日”,小學生不上文化課,開展各種活動。今年,教育部門又對一年級“零起點”做了詳細的規定。
規定不少,但執行還取決于學校和教師,從更廣泛的范圍看,教師素質制約了“減負”政策的推行。“我們有些老師的教學水平急需提高,他只知道多布置作業。如果3道題能讓學生搞懂問題,為什么要做30道?但這些老師就是不知道挑哪3道題給學生做。”
現實的背景是,教師還不是一個太具吸引力的職業。“教師待遇是否高,標志是教師這個職業能否吸引社會上最優秀的那批人,但現在很多人不愿意做教師。”倪閩景提到廣受稱道的芬蘭教育,在這個國家,高素質的人才選擇成為中小學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