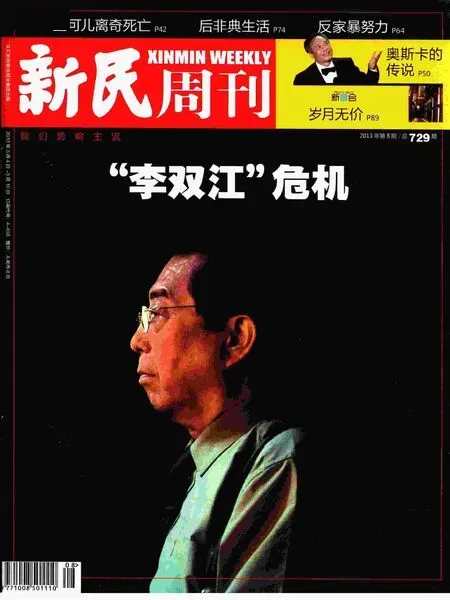在苛求細(xì)節(jié)中鑄就公信權(quán)威
禾刀
“盡管在最高法院成員中,魯思·金斯伯格和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是由克林頓提名任命的,但在1997年5月27日,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仍然對克林頓對葆拉·瓊斯性騷擾案作出了全體一致的判決,最終裁定維持上訴法院的判決結(jié)果”。接下來的一切大家都看到了,雖然貴為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卻不得不來到法庭,接受檢察官和法官的質(zhì)問,此案甚至還引發(fā)了后來的彈劾審判。
美國前總統(tǒng)布什在一次演講中曾說:“人類最偉大的進(jìn)步是實現(xiàn)了對統(tǒng)治者的馴服,實現(xiàn)了把他們關(guān)在籠子里的夢想。”這便是“把權(quán)力關(guān)進(jìn)籠子”的由來。權(quán)力如何關(guān)進(jìn)籠子?除了對權(quán)力的制衡設(shè)計,還必須仰仗法律底線的堅守。
在一般人看來,最高法院是堅守法律底線的地方,不過,2009年首度向電視敞開大門的美國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卻認(rèn)為:“我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解釋法律。我們只是履行職責(zé),告訴大家法律是什么,并不是要通過判決去支持其中一方或另一方。”持同一觀點的包括其他7位現(xiàn)任大法官(其中一位不愿公開采訪),還有本次一起接受采訪的另外3位退休大法官。《誰來守護(hù)公正》一書就是這次大法官的訪談錄,并且還附上了對美國最高法院現(xiàn)任書記官、前法官助理、前首席政府律師、出庭律師、資深記者和歷史學(xué)家等的訪談。
眾所周知,法律并非拜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由人們制訂,而只要與人有關(guān),都難以杜絕主觀性的一面。這意味著法律的形成本身難以解決制訂者的主觀認(rèn)識局限性,作為對法律最具權(quán)威的解釋者,學(xué)識淵博、資歷豐富的大法官們同樣可能面臨這樣的困惑。加強(qiáng)法律設(shè)計當(dāng)然很有必要,但再完善的法律也有鞭長莫及之處,法律在適用過程中總會面臨形形色色甚至是立法者難以想象的具體問題,于是努力踐行“法律下面人人平等”理念,這便是法庭包括法官存在的價值所在。
制度可以賦予大法官們合適的身份,但大法官公信力的樹立卻歷經(jīng)兩百多年的矢志堅守。本次大法官集體接受電視媒體采訪,在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還是頭一遭,而最高法院的庭審至今未能實現(xiàn)直播。州法院庭審電視直播早就司空見慣,公眾也習(xí)以為常,有趣的是,對于最高法院始終不愿引入直播,無論在大法官中,還是司法界、法學(xué)界包括媒體界等各行中,居然有極高的認(rèn)同。
如同不愿引入庭審直播一樣,美國最高法院對傳統(tǒng)的堅持讓人感到似乎有點過于守舊,甚至有些“老頑固”。比如有的法官至今仍舊習(xí)慣于用筆而不是電腦撰寫判決意見。就是本次接受媒體采訪,現(xiàn)任大法官戴維·蘇特仍然選擇拒絕公開出版他的訪談內(nèi)容。對于這些看似頑固的堅守,最高法院以及大法官們“理解保持連續(xù)性、恒定性的價值,而這是其他兩個政府分支無法做到的”。
一般情況下,很難想象,素以平等示人的美國,其最高法院卻是最講資歷的場所。無論是法庭上的坐序,還是大法官們在“密室”里的投票順序,辦公室的安排,甚至連換法袍房間也未能“幸免”,“資歷”二字如同美國最高法院的“內(nèi)部法”。不過,這種資歷傳統(tǒng)只是內(nèi)部基本工作秩序,并不影響到大法官們對案件的判斷,即便是大名鼎鼎的首席大法官,在內(nèi)部會議上,也只有一次發(fā)言機(jī)會,在投票時也僅有一票的權(quán)力。
那些久經(jīng)歷史淘洗的傳統(tǒng),如今早就顯現(xiàn)出其“光澤”魅力。美國最高法院的最近一次泄密事件發(fā)生在15年前。回避制度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程序,庭審和“密室”以外不談案件,這是最高法院延續(xù)的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的覆蓋面也不僅僅是大法官,還包括助理以及常駐媒記。回避制度之嚴(yán)甚至有草木皆兵之感,比如“三十秒規(guī)則”:如果有人看到法官助理與記者談話,助理三十秒后就得被開除。
細(xì)節(jié)不僅決定成敗,也是法律人士的基本素養(yǎng)。美國最高法院苛求的這些細(xì)節(jié),在千淘萬洗的歷史長河中,凝聚了任何力量均不足以動搖的公信力權(quán)威。在相當(dāng)一部分人看來,1937年羅斯福以推行“填塞法院”要挾贏得了最高法院的妥協(xié),因此,在這位美國人民并不否認(rèn)的偉大總統(tǒng)逝世時,人們沒有忘記在“偉大”二字下面留下這樣不太光彩的注腳——“羅斯福是個好總統(tǒng),但是,在最高法院那件事上,他做錯了。他不該那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