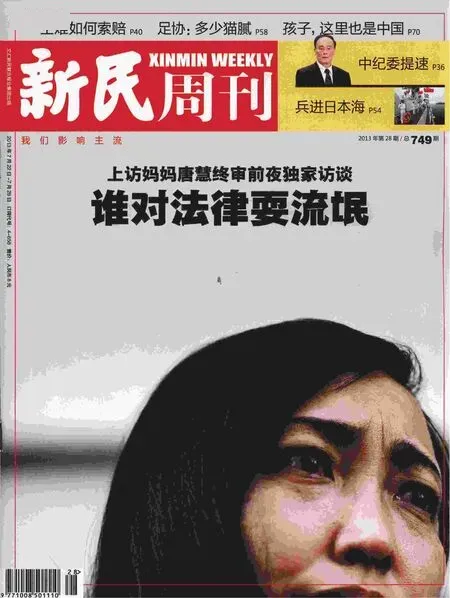“我為何最擔心85后、90后農民工”
王滬生


上學這條出路,斷了
《新民周刊》:你上學的時候,姐姐給你寫信:“只有上學才是我們的出路,只有上學才能讓我們過上好生活。”而你從中專到博士,從梁莊到北京,是什么讓你一直堅持到現在?
梁鴻:在我們那個年代,上世紀80年代,對我這樣一個農村貧困家庭的女孩來說,上學是唯一的出路,沒有別的路能夠變成城里戶口吃商品糧。當時,考上學不是考上本科,哪怕考上中專也行。變成城里人,吃飯有保障,這是最低的生存要求。
我不甘心在一個鄉村小學過一輩子,所以師范畢業,在鄉下教書三年后,我像打游戲關卡一樣,從縣里到市里再到北京,中專、大專、本科、碩士、博士,把中國的學歷體系都完整地上了一遍。
《新民周刊》:現在,農村孩子通過上學,還能夠改變命運嗎?
梁鴻:越來越難。原因很簡單,一個是農村的教學質量在下降,父親通常不在孩子身邊,二是學費越來越貴,即使大學畢業,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今天的農村孩子,想通過上學,高考,大學畢業,進入城市,找個好工作,成為社會精英,這樣的路越來越窄,越來越困難了,上學這條出路,斷了。
《新民周刊》:教育質量為什么下降?
梁鴻:我去年跟外甥女做升學調查,看了看現在的數據,真是太可怕了。在鄉村撤并學校后,小學統一撤到鄉鎮,中學并到縣城,一百多個學生一個班,有段時間四個孩子坐一個桌子。怎么教育?人太多了,老師根本忙不過來。為什么那么多孩子不上學?是因為教育環境太差了。
現在上學不掏錢,但生活成本非常大。很多農村的孩子,家遠要寄宿,在鎮上、縣里租個房子。父母不在身邊。孩子們的心理健康,身體健康,能否吃飽飯,吃得好不好,都是問題。
無法想象鄉村的破敗
《新民周刊》:過去的梁莊,你生長的梁莊,是什么樣子?
梁鴻:梁莊上世紀60年代,大煉鋼鐵,樹皮全部扒掉,經過20年的恢復,植被郁郁蔥蔥,也沒有什么工業項目,自然環境比較好。
小時候我們村的水塘,水質清澈,開滿荷花。村后的那條河流,培育了我對美的感覺,兩岸河岸上開滿野花。夏天的傍晚,全村人一吃完飯,都往那邊跑,洗衣服,洗澡,在那聊天,到夜里十來點鐘才回家。
在鄉村,小學是有象征作用的。學校的鈴聲,學生上課下課,讓農村的日常生活有了節奏感。每天早上,學生上學,農民下地,晚上放學,農民收工,每個人都有自身的位置,有一個村莊一個家的感覺。
《新民周刊》:今天的梁莊是什么樣?
梁鴻:今天的農村沒有了秩序。四處都是垃圾堆,許多房屋倒塌成廢墟,一些新建的房子高大,規劃混亂,一直鎖著門。河流污染,工廠排放的污水,滿是泡沫,都能點著。一些水塘被填,蓋滿了房子,孩子們沒有玩水的地方。僅存的兩個坑塘,填滿了垃圾,臭味也非常大。
我很意外,我生活的鄉村會以這樣的破敗形式體現出來。
《新民周刊》:為什么會走向破敗?
梁鴻:因為我們對這個村莊不愛了,只顧小家,不顧大家,自私自利,對集體的事物不管不問,對他人漠不關心,每人只盯著利益,導致公共空間沒有了。社會的變化,物欲的膨脹,城市的消費習慣,影響到農村,影響了農民,所以你看,我們村莊多么雜亂。
我小時候農村的資源都是反復利用,我們的糞便,牲口的糞便,直接灑到地田當肥料,現在我們全是用化肥。現在柴火沒有人用了,直接粉碎掉,用煤球和天然氣。以前小孩出生,用尿布反復地洗,現在用的全是尿不濕,垃圾遍地,原來農村沒有今天這么多的消費品。
農村的問題是“沒人”
《新民周刊》:你說,如今最大問題是“沒人了”?
梁鴻:現在的主要問題是人。人一旦沒有了,村莊沒有了精氣神。
梁莊有文化場館,有圖書室,也有電腦,有活動室,但青年人,中年人,有知識有文化的這幫人,都進城去了。15歲到50歲這個年齡的人,都在城市里。農村現在沒有人,都是老年人。國家對人員的流失,這種內部的坍塌,不管。
我們村蓋了多少房子,留在村里的,都是老弱病殘,就老太太和需要照顧的小孩,老無所依,就這個樣子。
《新民周刊》:鄉村的精英沒有了。
梁鴻:以前能干的村長、支書,道德完善,有威信的教書先生,到后來這些能人進城打工賺錢去了。在一切向錢看的社會里,你沒有掙到錢,就完蛋了,因為道德沒有說服力,也不會讓你有權威感。
我跟老家村官接觸過,任期只有五年,想升職一定要在短時間里出成績,怎么辦?種莊稼出不了成績,只有賣地,蓋工業園,引進工廠,馬上有效益。在發展建設中,官員的利益,企業的利益,小老板的利益,甚至一個村支書的利益,都可以挾持著村民,犧牲他們的利益。
有些地方,讓農民動遷,一開始量地,和政府測量人員一起出現的是房地產商,占地賠款是他發的,這片地升值的部分利益,被房產商和政府拿走了,跟農民沒關系。
《新民周刊》:鄉村基層直選、自治,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梁鴻:村主任、支書,是官僚系統的最低等級,他不對村里人負責,對鎮政府負責,跟村莊沒有關系,只跟上面打交道,跟上面要點錢,整天吃吃喝喝,心不在村里邊,只需要應付好上面,就可以坐穩位置。
老人覺得跟自己沒關系,誰都行,投誰的票都一樣,反正自己沾不到什么利益。年輕人在外面打工,跟村莊沒感情,一年四季在外,更不會管村里的事情,他們不會投票,即使選票上有他們的名字,但最后都是別人代簽的。這也是導致村莊集體公共的凝聚力渙散的原因。
農民工無處生根
《新民周刊》:你為什么說最擔心85后、90后這代打工者?
梁鴻:相比前兩代農民工,他們的理想和現實的差距更大,也更痛苦。這些年輕打工者,一部分沒有成家,一部分剛剛成家。父母在老家小城給他買好房子了,如果結婚成家,有了孩子,丟給爹媽養。
他們家里經濟條件都不錯,看的電視,玩的玩具、網絡游戲,吃的食物,和城里孩子都一樣。他們對工作和生活的期望值,跟大城市的同齡人一樣,工資要高,有休閑時間,能享受生活,想買車、出國旅游,希望得到公平的待遇。
他們不養孩子,因為他們小時候是被父母拋棄的孩子,和爺爺奶奶一起長大,到他們這一代,自然會放棄做父母的責任。他們不像第一代打工者那么痛苦,覺得自己對不起孩子,因為他們自己就是這樣長大的。
他們在城里打工,換工作極快,今天在鄭州,明天到廣州。為什么?工資不高,太累,你對我不好,我當然走,到哪里掙錢都一樣。他們到一個地方,都會換電話,只跟父母聯系,沒有穩固的朋友圈。將來怎么辦?不知道,根本沒去想。
他們的公平意識,自我的享樂意識,是時代發展社會進步,人的個性充分發展的體現。但這些又給他們帶來困境,他們很難實現理想,一年一年過去,最后他們灰心喪氣,只能聽天由命。
《新民周刊》:你在南都的鄉村建設論壇上,為什么和一個學者掐架?
梁鴻:論壇上一個搞農村研究的著名學者,發言說必須允許城市先富起來,然后才能夠管農村,隨著城市化發展,農村一定要消失,城中村影響城市市容,必須要拆遷。
當時我氣得站起來,為什么農民的溫飽問題解決了,農村就可以不管了?農民為什么不能享有和城市一樣的待遇?為什么都讓城市富起來,而不是農村先富起來?為什么我們今天說農民富,只說經濟的富裕,沒有人考慮到精神富裕?
我們讓農民背井離鄉、拋妻別女,到城市打工,干的都是城市人不愿意干的活,絕大部分都是賣體力,掙的血汗錢,省吃儉用,幸虧還有城中村,房租便宜,他們才能夠在城市落腳。
如果有一天,城中村全部拆掉,全變成高樓,超級商場,那些人到哪里去?離城市更遠,住地更偏,沒有公共設施,要跑更遠的路上班。城市的發展,從來沒有考慮到人的發展,尤其沒有考慮到普通貧民的存在,更沒有考慮到農民工的存在。
農民工和農村一樣,是這個國家社會階層的最低層,最容易被忽視、被歧視、被欺壓的群體。
《新民周刊》:你有一個判斷,如果農村人能在城市安家,能夠享受社會保障,孩子能夠上學,權益同等,中國會有更大的離鄉潮。為什么?
梁鴻:如果我們城市化的程度非常高,農村會更加敗落。如果農民工獲得城市戶口,得到保障,他當然愿意進城了,因為社會資源,目前全部集中在城市,肯定是更大的離鄉潮,這是毫無疑問的。
現在的問題是,所謂人口城市化率已達50%,城市戶籍人口卻只有33% ;這是虛假的城市化。梁莊幾個年輕人,考上大學變成城市戶口的,后來畢業分配沒留在鄭州,他們戶口也沒有回到農村,后來一問,留在鎮上的派出所集體戶口里。
《新民周刊》:你下一本書寫什么?
梁鴻:我最近做一個養老院的調查,想寫一個這方面的作品。
現在,農村老人老無所依的狀況非常嚴重,老人贍養是一個大問題,他們沒有社會保險,總是依靠子女,農村道德下降也非常厲害,兒女對老人感情淡漠,縣以下的地方,老人進養老院,絕不是自愿進的,一定是被遺棄的狀況。
我的妹妹一個朋友開養老院,我每次回來都去看。很多老人快死了,處于昏迷狀態,院方給她兒女打電話,在外地打工,好不容易聯系上,結果兒女問:“她到底會不會死?如果死了我就回去。”
現在道德淪喪,親情淡薄,一切變成利益的計算。大部分兒女是依靠自己出去打工掙的錢蓋的房子,憑什么養老人。哪怕你給他帶20年孫子了,帶不動了,癡呆了,他這個時候絕對不會管你。我覺得這個非常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