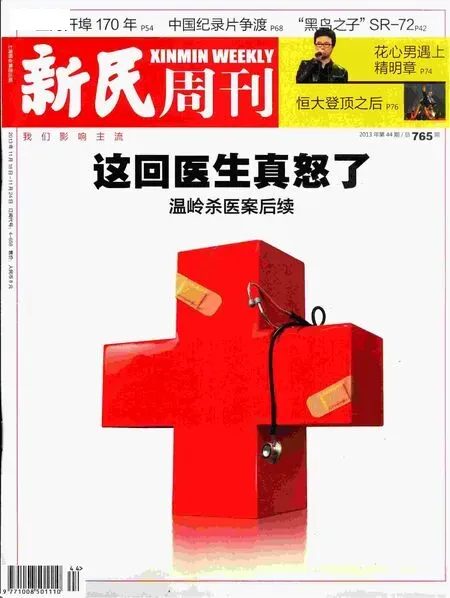市場公平等于公平嗎
劉洪波
沒有人會說不要公平,但要的是哪一種公平,很不相同。
近日看到一家大報上專家講全面深化改革,說“政府的作用就是要當看守人,守護公平正義,保護游戲規則,實現市場主體平等”。而聽一家央媒在說到“新一輪改革需破‘公平正義關”時,說的則是“讓發展成果更公平惠及人民”,談到的話題包括養老金改革、城鄉二元關系、財富分配不公等等。
前一種表述中,市場主體平等即使不是公平正義的全部,至少也被當成最緊要的問題;而后一種理解,將實現公平正義的重點放到共享發展成果。這是兩種差異很大的公平正義觀。
市場主體平等,輿論高度關切,從此來看,市場主體間不公平,應是大問題。現在市場主體多樣,但市場主體平等的說法是有特指的,那就是國有企業與其他企業之間不平等,而其他企業之間是否也不平等,沒有人關注。外資企業、股份制企業、私營企業,它們是否平等了,輿論上很少人關心,這就像是說它們之間已經平等了,或者即使不平等也不嚴重,又或者即使不平等而且嚴重但也不在意,而國企受到的優待則必須在意。
更重要的是,公平正義是否僅僅表現為市場主體平等,或者是否主要表現為市場主體平等。我知道,正經說起道理來,所有人都會表示并非如此,但事實上,一些人關切的公平正義,確實只意味著市場主體的平等,推廣一下,也僅僅是所有人在市場上平等。個人作為消費者平等了,個人創辦企業的權利、發財的機會、面臨的市場規則平等了,公平正義就實現了。
那些要求市場主體平等的人,那些義憤于市場主體不平等的人,并不見得同意勞動者與老板有什么平等,當然有時會說人格上平等,那只是客氣話,老板有那么多錢,還養活了勞動者,誰跟你平等,你怎么能跟老板談判報酬權、休息權、勞保權?
按照這種公平觀念,兩極分化根本不是問題,先富不僅無須帶著后富走,且不能富裕的人正是該被社會淘汰的對象;個人所得稅是向能力和智慧征稅,極不公平;貧富差距帶來的社會矛盾,只要用“你窮只怪自己無能”的教育,加上完備的安保措施去解決就行了。人在市場上公平了,就等于在社會上也公平了,或者說,公平就是市場公平,法律公平、政治公平、社會公平等,都只是市場公平在特殊場合的表現。
按照這種公平觀念,如果這個社會還要有一點救濟,那可不是為了體現公平,因為公平是早就在市場上實現了的,獲得救濟也不是貧困者的社會權利,而只是富裕者體現同情心。所以救濟必須謹防養懶漢,否則,同情心被濫用事小,同情者上了當事大,因為上當固然可以體現貧困者天性卑劣,但同時也有損于富裕者的智力優越感。
按照這種公平觀念,如果一個人發了財,那不僅是智力和道德的證明,而且社會必須為之開辟進一步發財的渠道,這才是公平的進一步擴大,市場主體平等的進一步拓展。與此同時,社會務須保證按財富榜排序分配社會尊重的份額。如果財富縮水,政府還應該去搭救,因為“救富人就是救窮人,救老板就是救工人”。
政府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守護公平正義”,具體而言就是“實現市場主體平等”。發展的意義是什么呢?GDP、稅收和出產富豪。一些地方說建設服務型政府,其實或者首要指的是服務資本、服務企業家,并以之作為服務社會和公眾,好像社會就是企業,公眾就是企業家一樣。資本認可投資環境優良,就代表政務環境改善了;企業家說營商環境好就是最高的夸獎,市場主體贊揚待遇公平就是社會公平。
“全面深化改革”,將會怎么改呢?會繼續模糊市場公平與社會公正,同意公平正義就是市場主體平等嗎?這也會改改的吧。